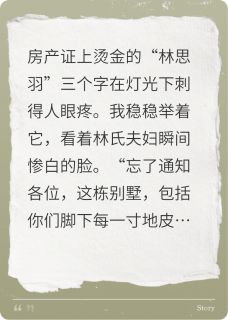房产证上烫金的“林思羽”三个字在灯光下刺得人眼疼。我稳稳举着它,
看着林氏夫妇瞬间惨白的脸。“忘了通知各位,这栋别墅,
包括你们脚下每一寸地皮——”“三年前就已经在我名下。”养母手中的骨瓷杯哐当坠地,
滚烫的茶水溅脏了林芳纭十万块的高定裙摆。那个他们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尖叫着跳开,
指尖几乎戳到我鼻梁:“你算什么东西!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我轻笑一声,
将驱逐通知书拍在价值连城的紫檀茶几上。“限你们三小时,带着真千金,滚出我的房子。
”1客厅水晶灯的光太亮了,亮得能看清林国栋鬓角新冒出的白发,
亮得能照见陈美娟眼底来不及藏好的嫌弃,
亮得让林芳纭脖子上那条钻石项链几乎要灼伤人眼。这条项链,
本该戴在我脖子上——林家所谓的“生日礼物”,在陈美娟得知林芳纭多看了一秒后,
便自然地滑进了亲生女儿的珠宝盒里。“思羽,芳纭刚回来,对环境还不熟悉,
”陈美娟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放软的疲惫,她保养得宜的手指揉着太阳穴,“你懂事,
先搬到公司那套小公寓过渡一下,好吗?那里离你上班也近。”她甚至扯出一个理由,
试图让这掠夺显得温情脉脉。我握着冰凉的茶杯,指尖感受着瓷釉细腻的纹理。
这杯子是我二十岁那年,用第一笔独立完成项目赚到的奖金,
特意从拍卖会上为陈美娟拍下的。她当时欢喜得不得了,逢人便夸“我们思羽眼光好,
贴心”。林国栋在一旁沉默地翻着财经杂志,仿佛眼前讨论的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家务事。
他的沉默,就是对这场驱逐最响亮的赞同。而林芳纭,
那个被找回来不到半年的林家“真凤凰”,此刻正慵懒地歪在昂贵的意大利沙发里,
新做的水晶指甲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屏幕,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胜利者的微笑。“妈,
”我放下茶杯,瓷器与玻璃茶几碰撞,发出清脆的“叮”一声,“我在这个家,
住了二十四年。”陈美娟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被更深的“为难”覆盖:“思羽,
妈妈知道你委屈。可芳纭……她流落在外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好不容易回家了,
我们总想把最好的都给她,补偿她……你是姐姐,让着点妹妹,好不好?
”她把“妹妹”两个字咬得很重,像一根针,精准地刺过来。让?这个字,在过去半年里,
我已经听得耳朵起了茧子。
芳纭故意打碎我母亲(那个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只留给我一枚廉价银戒的生母)唯一的遗像,
碎片划破我的掌心。陈美娟轻描淡写:“一个旧相框罢了,芳纭又不是故意的,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计较?”林芳纭在林氏重要的融资酒会上,将红酒“不小心”泼了我一身,
让我精心准备的汇报泡汤,导致林氏错失关键投资。
林国栋在书房里对我拍桌子:“她刚接触上流社会不懂规矩!你呢?你是林氏的项目总监!
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还指望你以后挑大梁?”他的怒火烧在我身上,
却对始作俑者连一句重话都没有。林芳纭甚至能把手伸进我的电脑,
将我呕心沥血三个月做的、关于挽救林氏旗下最大亏损子公司“晨曦”的方案,
改得面目全非后发给董事会。董事们震怒,质疑我的能力。
当技术部艰难恢复的数据日志清晰地指向林芳纭的IP地址时,
陈美娟只是搂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儿,对我叹息:“芳纭就是想帮你看看,她也是一片好心,
可能方式不对……你何必闹得这么大?家丑不可外扬啊!”每一次的“让”,
都像钝刀子割肉。每一次的“懂事”,都换来他们更得寸进尺的偏袒。他们忘了,
是谁在十年前林氏濒临破产、被高利贷堵门时,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
颤抖着却无比坚定地挡在吓瘫的陈美娟身前,对着凶神恶煞的债主头子说:“钱,我们会还!
给我三年!”他们忘了,是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像个永不停歇的陀螺,白天上课,
晚上钻研各种金融案例,抓住每一个微小的机会,用近乎自残的努力,在十六岁那年,
奇迹般地帮林氏拉到了第一笔救命投资。他们更忘了,是谁在之后的岁月里,
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为林氏拓展版图,巩固根基。那些觥筹交错背后的疲惫,
那些深夜伏案分析数据的灯火,那些在谈判桌上与人据理力争的锋芒……所有的付出,
在林芳纭出现后,都成了“你应该做的”。我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给真正的林家血脉铺路,
并在她需要时,随时让位。“最好的都给她……”我轻轻重复着陈美娟的话,
目光扫过这间奢华到极致的客厅。意大利定制的沙发,波斯的手工地毯,
墙上挂着价值连城的当代艺术名画……这里的每一分奢华,都浸透着我这些年的心血。
“包括我住了二十四年的房间?包括我为林氏赚回来的每一分钱支撑的这个家?
”林国栋终于放下了杂志,眉头紧锁,带着上位者惯有的不耐:“思羽!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搬出去是暂时的!等芳纭适应了,家里自然会给你安排更好的住处!林氏现在局面正好,
你作为高管,要以大局为重,别斤斤计较这些小事!
”他习惯性地给我扣上“不顾大局”的帽子,仿佛我的任何反抗,都是对林氏的背叛。大局?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沉入冰窖。原来我在他们眼里,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安排”的物件,
一个随时可以为了“大局”牺牲的棋子。那些所谓的养育之恩,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投资,
如今正主归来,我这枚棋子,就该识趣地退场了。“是啊,姐姐。
”林芳纭终于舍得从手机上抬起眼,那双与我毫无相似之处的眼睛里,
盛满了毫不掩饰的恶意和得意,“爸说得对,一家人嘛,分什么你的我的?
你的不就是林家的?林家的一切,不迟早都是我的?”她特意加重了“迟早”两个字,
像毒蛇吐信。最后一丝暖意,彻底熄灭。我看着眼前这三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林国栋的冷漠自私,陈美娟的虚伪偏心,林芳纭的贪婪恶毒。二十四年的滤镜轰然碎裂,
露出底下冰冷丑陋的真相。“分清楚?”我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胸腔里翻涌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暴烈的冰冷怒意,
以及……一种即将破笼而出的、久违的轻松。“好,是该分清楚了。
”我没有再看他们错愕的表情,转身走向楼梯下方那个不起眼的储藏室。
那里堆放着一些陈年的旧物,布满灰尘。林家三口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钉在我背上,
充满了疑惑和不屑——都这个时候了,难道还想翻找什么不值钱的“念想”带走?
我在积尘的旧画框和废弃健身器材后面,摸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金属物体。
那是一个嵌入墙壁的指纹保险箱,位置极其隐蔽。指尖按上去,蓝光扫描,
轻微的“咔哒”声,在寂静的客厅里清晰得刺耳。我捧出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不大,
却异常沉重。走回客厅中央,在三人惊疑不定的注视下,我打开了盒子。里面没有珠宝,
只有几份文件。我抽出最上面那份,轻轻一抖,纸张发出脆响。然后,我把它举了起来,
正对着那盏昂贵的水晶吊灯。烫金的国徽,清晰无比的“房屋所有权证”字样,下方,
权利人姓名栏里,“林思羽”三个字,力透纸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林国栋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冻结,化为难以置信的惊愕。陈美娟捂着嘴,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
身体晃了一下,手无意识地扫过茶几——那只她曾经无比珍爱的骨瓷杯,“哐当”一声脆响,
摔在地上,四分五裂!滚烫的茶水飞溅开来,
有几滴正落在林芳纭那条新买的、价值不菲的高定裙摆上。“啊——我的裙子!
”林芳纭像被烙铁烫到一样尖叫着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拍打着水渍,
精心打理过的头发都散乱了几缕。她猛地抬头,气急败坏,
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声音尖利刺耳:“林思羽!你发什么疯!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也敢拿假证在这里装神弄鬼!
”她的尖叫打破了死寂。林国栋猛地回过神,脸色由惊愕转为铁青,他一步上前,
试图看清我手中的证件,声音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不可能!
这房子……这房子当年是我亲自……”“亲自买下的,没错。”我平静地接口,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盖过了林芳纭的噪音,也压下了林国栋强装的镇定,“时间是二十一年前,
林氏地产开发的‘云顶’系列一号别墅,户主登记的是你,林国栋。
”我看着他那双开始慌乱的眼睛,一字一句地,缓慢地,扔下炸弹,“但是,三年前,
林氏遭遇那场最大的财务危机,银行冻结了所有主要资产准备拍卖抵债,包括这栋别墅。
你忘了?”林国栋的脸色“唰”地一下惨白如纸,身体几不可查地晃了晃。
陈美娟也想起了什么,血色迅速从她脸上褪去,只剩下惊恐的灰白。“是我。
”我晃了晃手中的产权证,金色的字在灯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是我用‘晨曦资本’的名义,在法拍最后一刻,以高于市价三成的价格,拍下了这栋房子,
以及,”我从盒子里抽出另外几份文件,“林氏集团总部大楼的产权,
还有林氏持有的‘晨曦科技’15%的核心股权。”这些文件像沉重的砖块,被我一份一份,
轻描淡写地拍在光可鉴人的紫檀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份文件的权利人栏里,
都只有同一个名字——林思羽。“你……你哪来那么多钱?”陈美娟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晨曦资本……那个神秘的资本方……是你?”这些年,
除了为林氏明面上的业务殚精竭虑,
我从未停止过用另一个身份——“晨曦资本”的幕后掌舵人,在资本市场开疆拓土。
那些在谈判桌上积累的人脉,那些在危机中洞察的先机,
那些被林国栋嗤之以鼻却精准无比的市场预判,都成了“晨曦”崛起的基石。
这个身份隐藏得极深,连林家夫妇也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只当是某个背景深厚的海外财团。
“这不重要。”我扯了扯嘴角,
目光扫过他们三人精彩纷呈的脸——震惊、恐惧、贪婪、怨毒,种种情绪混杂,扭曲而丑陋。
“重要的是,你们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你们林氏集团赖以生存的核心资产,
捏在我的手里。”“你……你想怎么样?”林国栋的声音干涩嘶哑,
强撑着最后一点家主的威严,但眼神里的恐慌出卖了他。“我想怎么样?
”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从丝绒盒子的最底层,抽出三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
白色的A4纸,黑色的打印字体,标题醒目而冰冷——《房屋腾退通知书》。“啪!啪!啪!
”三声轻响。三份通知书,被**脆利落地甩在那一堆价值亿万的产权证上。“三小时。
”我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带着你们林家尊贵的真千金,
收拾好你们所有的私人物品,滚出我的房子。三小时后,
如果我还在这里看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或者人,”我顿了顿,目光如同冰锥,
刺向脸色煞白的林芳纭,再缓缓移向摇摇欲坠的林氏夫妇,“我会通知我的律师和安保团队,
按非法侵占处理。相信我,明天的财经版和社会版头条,一定会非常精彩。”死寂。
令人窒息的死寂。只有林芳纭粗重的、带着哭腔的喘息声。她似乎终于意识到,
这不是一场她可以靠着撒泼打滚、父母偏袒就能赢的游戏。
她的目光死死盯着茶几上那堆文件,尤其是那本深红色的房产证,像是要用目光把它烧穿。
陈美娟最先崩溃,她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被林国栋下意识地扶住。她抓住丈夫的胳膊,
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眼泪汹涌而出,却不是对着我,而是朝着林国栋哭喊:“国栋!
这……这不可能!她是思羽啊!是我们养大的孩子啊!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一定是搞错了!
你快告诉她,这房子是我们的家啊!”她的哭声凄厉,充满了被背叛的控诉。
多么熟悉的姿态,每一次林芳纭犯错,她总是这样,用眼泪和“亲情”作为武器,
逼迫别人让步。可惜,这一次,她的武器失效了。林国栋扶着妻子,脸色灰败,他看着我,
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恐惧,有难以置信,
甚至还有一丝……被蝼蚁咬伤的荒谬感?他张了张嘴,试图拿出父亲的威严,
或者商人的谈判技巧:“思羽……我们……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关起门来商量?
你这样做,让外人怎么看?让林氏的股价怎么……”“一家人?”我打断他,
笑声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讽,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林董,
血缘可以是亲情的基础,却从不是亲情的证明。你们用二十四年的时间教会我这个道理,
现在,该我交答卷了。
”我不再理会身后陈美娟崩溃的哭嚎和林芳纭歇斯底里的咒骂(“林思羽!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不得好死!”),
也忽略掉林国栋那瞬间颓败下去、仿佛老了十岁的背影。转过身,脊背挺得笔直,一步一步,
踏过脚下光洁如镜、映照着他们狼狈倒影的地板,
走向那扇象征着这个家权力中心、此刻却显得无比讽刺的厚重雕花大门。门外,
初夏傍晚的风带着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屏幕上,
一个标注为“深蓝拍卖行-李经理”的来电正在闪烁。按下接听键,
一个恭敬热情的声音传来:“林**,您之前特别关注的‘蔚蓝之泪’钻石项链,
已经确定将作为压轴拍品出现在下周苏富比的慈善夜。另外,按照您的吩咐,
给林氏集团的邀请函已经发出,特别标注了林芳纭**的名字。”“很好。
”我望着远处天边最后一抹瑰丽的晚霞,声音平静无波,“替我预留最好的位置。这场戏,
我要亲自到场。”2一周后,
由苏富比联合本地顶级豪门苏氏举办的“深蓝之心”慈善拍卖晚宴,
在市中心最负盛名的半岛酒店宴会厅举行。这是名利场最顶级的盛宴,
政商名流、各界巨擘云集,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空气中浮动着高级香槟的气味和名贵香水交织的气息。我选了一条极简的吊带黑色丝绒长裙,
没有繁复的装饰,流畅的剪裁完美勾勒出线条。乌黑的长发松松挽起,露出修长的脖颈,
上面没有任何项链点缀。唯一的亮色,是耳垂上两颗小巧却光芒四射的水滴形粉钻。
这身装扮在满场珠光宝气中显得低调至极,却又因为那份极致的简约和自信,
反而透出一种不容忽视的气场。
我挽着“晨曦资本”明面上的合伙人、也是我多年好友兼得力助手秦铮的手臂,
从容步入会场。“九点钟方向,你的‘家人们’来了。”秦铮微微倾身,在我耳边低语,
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不用回头,
我也能感受到那几道混合着怨毒、惊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的视线,如同芒刺在背。
林氏夫妇带着盛装打扮的林芳纭出现了。林芳纭显然下了血本,
一身当季最新款的桃粉色抹胸蓬蓬裙,脖子上戴着一条目测分量不小的钻石项链,
手上也戴满了闪亮的戒指,整个人像是移动的圣诞树,极力想融入这个顶级圈子,
却透着一股用力过猛的艳俗。她一眼就看到了我,
尤其是在看到我身边气度不凡、英俊挺拔的秦铮时,眼中的嫉妒几乎要喷出火来。“姐姐!
”一个甜得发腻的声音响起,林芳纭端着酒杯,像只花蝴蝶一样“飘”了过来,
脸上堆着假笑,刻意放大的音量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真巧啊!你也收到邀请函了?
是跟着哪位老板来的呀?”她那双眼睛滴溜溜地在秦铮身上打转,
毫不掩饰地评估着他腕表的价值和西装的品牌,话语里的暗示性十足——一个养女,
怎么可能有资格独立进入这种场合?必然是作为“女伴”依附男人而来。
周围的私语声隐隐传来,不少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林氏真假千金的风波,
在这个圈子里并非秘密。秦铮眉头微蹙,刚要开口,我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臂。“林**。
”我晃了晃手中香槟杯,澄澈的酒液在金碧辉煌的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
唇角勾起一抹毫无温度的弧度,声音清晰而平稳,足以让附近几桌的人都听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