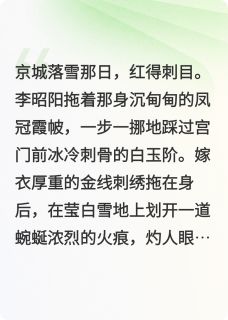京城落雪那日,红得刺目。李昭阳拖着那身沉甸甸的凤冠霞帔,
一步一挪地踩过宫门前冰冷刺骨的白玉阶。嫁衣厚重的金线刺绣拖在身后,
在莹白雪地上划开一道蜿蜒浓烈的火痕,灼人眼目。她爹,当今天子,
顶着一张涕泪横流的老脸,死死攥着她的手腕不肯松开,
哭腔浓得化不开:“闺女啊……爹这心里头,跟被剜去一块肉似的疼!真舍不得你啊!
”李昭阳垂着眼睫,看着老爹龙袍袖口上沾着的几点可疑水渍,
心里翻腾的嫌弃几乎要冲口而出——舍不得?舍不得还把我往那三千里外的草原狼窝里推?
天家的父女情谊,果然比纸糊的窗户还薄。可话到嘴边,硬生生被她咽了回去,舌尖一转,
吐出的只剩温软熨帖:“爹,放宽心。女儿……去去就回。”去去就回?这话轻飘飘的,
连她自己都不信。车轮碾过宫门高高的门槛,发出沉闷的声响,
将天子最后一声哽咽和身后巍峨的宫阙一并甩开。李昭阳靠在颠簸摇晃的马车壁上,
撩起猩红车帘一角,最后望了一眼风雪中渐渐模糊的朱红宫墙。红墙白雪,
是她记忆里京城最后的色彩。此一去,山高水长,归期渺茫。送亲的队伍像一条疲惫的长蛇,
在官道上缓缓蠕动。车轮吱呀,马蹄嘚嘚,单调枯燥,日复一日。离京时还是早春,
枝头刚刚冒出嫩芽,空气里浮动着若有似无的杏花微雨气息。待车窗外景致彻底变了模样,
已是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辽阔无边的绿意泼洒开来,天高地远,风吹草低,
露出远处星星点点的白色毡房轮廓。草原,到了。近两个月的长途颠簸,
五脏六腑都似移了位。马车停稳的刹那,李昭阳只觉得一股酸水猛地冲上喉咙口。
她强撑着发软的双腿,掀开厚重的车帘,脚刚踏上松软的草地,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
胃里翻江倒海,早上勉强咽下的几块干硬点心再也按捺不住,“哇”的一声,尽数喷溅而出。
好巧不巧,前方一双沾着泥土草屑、一看就属于男人的、样式粗犷的牛皮马靴,
正稳稳地立在那里。秽物温热,带着令人作呕的酸腐气味,瞬间糊满了那深棕色的靴面,
滴滴答答往下淌。李昭阳捂着绞痛的胃,冷汗涔涔地抬起头。逆着草原午后过分耀眼的阳光,
她撞进了一双眼睛里。那眸色奇异,如同凝固的、澄澈的琥珀,镶嵌在深邃的眉骨之下。
鼻梁高挺得近乎嶙峋,薄唇紧抿,唇线像被最锋利的弯刀精心削刻过。他身形极高,
站在那里,像一堵沉默的山壁,投下的阴影几乎将她整个笼罩。空气凝滞了一瞬。
周围原本嘈杂的人声、马匹的响鼻声,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掐断。
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微微眯起,锐利的目光在她惨白的脸上刮过,
随即落在自己那惨不忍睹的靴子上。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
带着草原风沙打磨过的粗粝质感,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鼓面上:“啧。中原送来的,
就这?一只碰不得、摔不得的……瓷花瓶?”那轻蔑的尾音像带着倒刺的钩子,
狠狠扎进李昭阳的耳朵。胃部的翻搅和长途跋涉的委屈、对未知命运的惶恐瞬间被点燃,
烧成一股不管不顾的怒火,直冲头顶。她猛地挺直了几乎佝偻下去的腰背,
仿佛要将这两个月被马车颠散的骨头重新一根根拼凑硬朗。下巴抬得高高的,
迎上那双审视的琥珀眸子,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凝固的空气:“花瓶又如何?
至少还能插花,装点门面,瞧着也舒心。总比某些外强中干、只会空占地方的草包强!
”话音落下,死寂。风声都停了。侍立在不远处的几个草原壮汉,眼珠子瞪得溜圆,
嘴巴微张,活像白日里见了鬼。敢这么顶撞他们可汗?这中原公主怕是嫌命太长!
赫连灼的眉骨几不可察地跳动了一下。
他锋利的视线牢牢锁住眼前这个面色苍白、却倔强地挺直脊梁的少女。
她身上那身繁复华丽的中原嫁衣,在这广袤粗犷的草原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又异常扎眼,
像一团强行塞进来的、格格不入的火。片刻的死寂后,赫连灼的嘴角,
竟极其缓慢地向上牵起了一个微小的弧度。不是笑,更像一头猛兽发现了某种新奇猎物时,
带着玩味和探究的兴味。“呵。”一声短促的气音从他鼻腔里哼出,意味不明。
他没有再看那双被弄脏的靴子,也没有再看李昭阳,只是利落地转身,
丢下一句:“带她进去。”声音依旧低沉,却没了方才那刺骨的寒意。
高大的身影裹挟着一股风沙和皮革混合的气息,
大步流星地走向营地中央那顶最为巨大、装饰着雄鹰图腾的王帐。李昭阳站在原地,
草原上强劲的风吹得她嫁衣的广袖猎猎作响。她深吸了一口带着青草和泥土腥气的空气,
压下喉咙口残余的恶心感。第一步,似乎……没被生吞活剥?她攥紧了袖中冰凉的手指。
夜幕低垂,草原的寒意无声地渗透进王帐的每一个角落。
巨大的空间里只点着几盏昏暗的牛油灯,光影在帐壁上跳跃晃动,
映出毡毯上繁复的暗色花纹。李昭阳穿着一身素白的中衣,像个受惊的小兽,
死死抱着那床厚实的羊毛锦被,将自己蜷缩在宽大毡床的最里侧角落,
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赫连灼就坐在床对面的矮几旁。他换下了白日沾了秽物的外袍,
只着一件深色的单衣,领口微敞,露出线条硬朗的脖颈和小片结实的胸膛。他坐姿大开大合,
一条腿随意地屈起,手肘撑在膝盖上,
正慢条斯理地用一块磨刀石打磨他腰间那柄镶着宝石的弯刀。
“嚓…嚓…”磨刀石刮过金属的声响,在过分安静的帐篷里被无限放大,听得人头皮发麻。
琥珀色的眸子抬了起来,精准地捕捉到角落里那团瑟瑟发抖的白色。他停下动作,
刀锋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出一点幽冷的寒芒。“怕我?”他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低沉,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像夜风吹过枯草的沙沙声。李昭阳抱紧被子的手臂又收紧了些,
指尖掐进被面柔软的羊毛里。她强迫自己迎上那道目光,声音努力平稳,
却泄露出一点不易察觉的微颤:“怕?我…我怕你半夜磨牙!”“磨牙?
”赫连灼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笑话,喉咙里滚出一阵低沉的笑。他放下磨刀石,
将那柄寒光闪闪的弯刀随意地搁在矮几上,身体微微前倾,
那张刀削斧凿般的脸孔在跳跃的灯火下半明半暗,嘴角勾起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弧度。
“我不磨牙。”他慢悠悠地说,目光像带着钩子,在她脸上逡巡,“我咬人。
”“……”李昭阳所有强装的镇定瞬间土崩瓦解。她猛地将头埋进厚厚的羊毛被子里,
把自己裹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茧,只留下几缕乌黑的发丝散落在外面,
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微微起伏。黑暗中,她似乎听见男人又发出一声极轻的、意味不明的哼笑,
然后是脚步声,朝着毡床的方向。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碎肋骨。然而,
那脚步声并未靠近床边,而是走向了帐篷的另一侧。接着是窸窸窣窣的声响,
似乎是摊开了另一张铺在地上的厚毡毯。李昭阳紧绷的神经这才敢稍稍松懈一丝。
她悄悄将被子拉开一条缝隙,借着昏暗的光线,
看到赫连灼高大的身影已经和衣躺在了那张临时铺就的地毡上,背对着她,呼吸均匀绵长。
他……没过来?她缩回被子里,身体依旧僵硬,但狂跳的心却一点点落回实处。帐外,
草原的夜风呼啸着掠过,卷起阵阵呜咽般的声响。帐内,只剩下两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在寂静中交织。草原的日子,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撒开蹄子狂奔,
将李昭阳过去十六年养成的所有精细习惯碾得粉碎。清晨,
一碗浓稠腥膻、浮着奶皮的羊奶被端到面前,那股子直冲天灵盖的腥气让她胃里一阵翻腾。
中午,巨大的木盘里盛着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四溢的整羊,刀子割下去,
肉块间还渗着淡淡的血丝。晚上,围着篝火,听着苍凉悠远的马头琴声,
入嘴的依旧是油乎乎的手抓羊肉。第三天,李昭阳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从头发丝到脚趾尖,
都浸透了那股挥之不去的羊膻味。她看着面前又是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烤羊排,胃里一阵痉挛,
脸色发白地推开了盘子。“中原的娇花,这就蔫了?”赫连灼的声音带着惯常的嘲弄,
从主位传来。他正用锋利的小刀娴熟地剔着骨头上的肉,动作带着草原特有的豪迈。
李昭阳没力气跟他斗嘴,只虚弱地摇摇头,摸出自己藏在袖袋里的最后一块干硬饼子,
小口小口地啃着,味同嚼蜡。赫连灼的目光在她苍白的脸上停留片刻,
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随手将自己盘中一块烤得半生不熟、还带着血筋的羊排,
“啪”地一声扔进李昭阳面前那只描金画凤、与草原粗犷格格不入的细瓷盘里。“吃!
”命令式的口吻,不容置疑。人在屋檐下。李昭阳闭了闭眼,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
用银箸夹起那块羊排,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瞬间,
浓烈原始的膻味混合着生肉的铁锈腥气在口腔里爆炸开来,直冲鼻腔!眼泪完全不受控制,
唰地一下就涌了上来,在眼眶里打转。她死死咬住下唇,强忍着没吐出来,憋得脸颊通红。
赫连灼看着她这副泫然欲泣、强忍痛苦的模样,握着银刀的手顿住了。
琥珀色的眸子里飞快地掠过一丝……近乎茫然的不解和极淡的烦躁。这中原女人,
怎么比刚出生的小羊羔还难养?夜半,万籁俱寂,只有风声在帐篷外呜咽。
李昭阳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火烧火燎。她悄无声息地爬起来,
借着帐壁缝隙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摸到了自己陪嫁箱笼里小心藏匿的一个巴掌大的小铜锅,
一小袋金贵的小米,还有一只小皮囊装的清水。她像个偷油的小老鼠,
蹑手蹑脚地溜到王帐后面背风的角落里。这里堆着些杂物,正好能挡住火光。
她飞快地架起小锅,倒入清水和小米,又摸出火折子,费了好大劲才点燃一小堆捡来的枯草。
橘黄的小火苗跳跃着,舔舐着锅底。小米在清水中翻滚,
渐渐散发出一种朴素却无比诱人的谷物清香。这熟悉的味道,
让李昭阳紧绷的神经和空荡的肠胃都得到了些许慰藉。她蹲在地上,
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翻滚的米粥,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就在她拿起木勺,准备搅动一下时,
一个高大的黑影无声无息地笼罩下来,将她和小锅完全罩住。“你在干什么?
”赫连灼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低沉得像草原深处滚动的闷雷,带着被惊扰的冰冷怒意。
李昭阳吓得手一抖,木勺差点掉进火堆里。她猛地抬头,
对上那双在夜色中依旧锐利如鹰隼的琥珀色眸子。心提到了嗓子眼,
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各种借口。“我……”她深吸一口气,索性破罐子破摔,
指着那锅翻滚着白沫、寡淡得能照见人影的清粥,声音带着豁出去的倔强,
“给自己留条活路!再吃你们的肉,我怕活不到明年开春!
”赫连灼的目光从她因紧张而绷紧的小脸,慢慢移到那口可怜巴巴的小铜锅上。锅里的东西,
稀汤寡水,几粒米沉浮着,与他平日见到的浓稠奶粥、油亮肉食相比,简直寒酸得可怜。
他沉默着,高大的身影在夜风中像一尊凝固的石像。一股莫名的情绪,
混杂着烦躁和一种从未有过的、极其陌生的……心虚感?悄然漫上心头。这女人,
弱得像草芽,却又硬得像石头。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用脚踢了踢旁边一小块未燃尽的枯草,
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回了王帐,厚重的毡帘在他身后落下。李昭阳愣在原地,
手里还攥着那只木勺,后背惊出一层冷汗。这就完了?不没收她的锅?不训斥她?
第二天清晨,当侍女端来早餐时,李昭阳惊讶地发现,除了惯常的羊奶和奶疙瘩,
她的矮几上竟然多了一碗热气腾腾、熬得恰到好处的白米粥!米粒软烂,
散发着纯粹的谷物香气。她疑惑地看向赫连灼的方向。赫连灼正大口撕扯着一块烤羊腿肉,
头也没抬,仿佛那碗粥的出现与他毫无关系。只是在她端起粥碗时,
才状似随意地冷哼了一声,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她听见:“你们中原人,啧,就是娇气。
”李昭阳捧着温热的粥碗,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喝着。那暖意从喉咙一直熨帖到胃里,
驱散了草原清晨的寒意。她悄悄抬眼,
瞟了一眼那个埋头大嚼、仿佛刚才那声冷哼不是他发出的男人,
嘴角忍不住向上弯起一个极小的弧度。
嘴硬心软……跟她宫里养的那只总爱挠人、却又偷偷把小鱼干叼到她窗台上的大花猫,
简直一模一样。草原的脾气,向来暴烈。盛夏刚铺开它滚烫的绿毯没多久,
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雪,如同天神震怒时掀翻了巨大的白色口袋,在短短一夜之间,
将整个王庭及周边几个小部落彻底吞没。狂风卷着雪沫子,像无数冰冷的鞭子抽打着大地。
厚厚的积雪压垮了不少老旧的毡帐,牲畜冻毙的哀鸣夹杂在风雪的咆哮中,令人心头发紧。
营地里一片混乱,哭喊声、吆喝声、牲畜的惊叫混作一团。李昭阳裹着厚厚的羊毛斗篷,
从王帐里冲出来时,正撞见赫连灼翻身上马,他脸色沉得能拧出水,
对着集结的部属厉声下令:“能动的都给我出去!救人!清雪!把帐篷给我撑起来!快!
”吼完,一夹马腹,黑马如离弦之箭般冲进了茫茫雪幕。寒风裹着雪粒子扑在脸上,
刀割似的疼。李昭阳顾不得许多,
立刻转身对身边几个同样惊慌的陪嫁侍女和几个王帐里的年轻女奴喊道:“别愣着!
去把所有能找到的生姜都拿来!再支起几口大锅,烧热水!”侍女们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立刻分头行动。很快,几口大铁锅在王帐前相对避风的空地上支了起来,
积雪被清扫开,燃起了熊熊篝火。锅里的水翻滚着,李昭阳挽起袖子,
亲自将大块大块的生姜拍碎,投入沸水中。辛辣的气息很快随着蒸汽弥漫开来。
她又指挥人将王庭储备的干粮——炒米、肉干、奶疙瘩,尽可能多地分装出来。“阿吉嫂!
你家帐篷塌了?别慌,先带孩子过来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她认出一个抱着孩子、满脸惶急的妇人,正是平日负责给王帐送鲜奶的。“巴图大叔!
您腿脚不好,先坐下歇会儿,这里有热的!”她端着一碗滚烫的姜汤,
快步走向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牧人。她穿梭在混乱的人群和倒塌的帐篷间,
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发髻也散乱了,几缕发丝贴在额角。她指挥着侍女们分发姜汤和干粮,
声音在风雪中拔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镇定。“小心烫!”“慢点喝,还有!
”“孩子抱过来,先暖暖!”一碗碗滚烫辛辣的姜汤递到冻得嘴唇发紫的牧民手中,
一块块干粮塞进他们冰冷僵硬的手里。
那抹在雪地里奔忙的、穿着中原式样厚斗篷的纤细身影,像投入冰湖的一颗石子,
渐渐驱散了恐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暖意。几个被安顿好的老牧民捧着热腾腾的碗,
看着那个在风雪中穿梭忙碌的身影,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湿意,用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草原话,
喃喃地念叨:“中原的小太阳……是长生天赐给我们的小太阳啊……”远处,
赫连灼正带着人奋力撑起一座被压塌大半的毡帐。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下意识地回头,
望向王帐的方向。风雪迷眼,但他依旧清晰地看到了那个身影。
她正蹲在一个冻得直哭的小女孩面前,小心地吹凉手中的姜汤,柔声说着什么。
通红的脸上沾着雪粒,乌黑的发丝被风吹乱,狼狈不堪。可那双眼睛,在漫天风雪中,
却亮得惊人,像两颗坠落在草原上的星星,穿透了寒冷的帷幕,直直地撞进他心里。
母亲临终前虚弱的话语,毫无预兆地在他耳边响起,
清晰得如同昨日:“灼儿……记住……能真正温暖这片草原的女人,
才是……才是你命中注定的王后……”赫连灼握着支撑毡帐木杆的手,猛地收紧了。
冰冷的木头硌着掌心,一股滚烫的洪流却从心底最深处汹涌而出,瞬间席卷四肢百骸。
他定定地望着风雪中那抹亮色,琥珀色的眼底,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融化,碎裂,重组。
七月半,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赛马节。辽阔的草场被无数马蹄踏平,
彩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喧闹的人声和骏马的嘶鸣交织在一起,
空气里弥漫着青草、汗水与尘土混合的蓬勃气息。赫连灼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骑装。
纯黑的衣料紧束着他挺拔的身躯,勾勒出宽肩窄腰的利落线条,
外面罩着象征可汗身份的雪白狼裘坎肩,黑与白的强烈对比,
让他如同一簇在烈日下熊熊燃烧的火焰,耀眼夺目,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
李昭阳也换上了骑装。不过她的装束是精心改良过的,窄袖束腰,便于骑乘,
衣料是上好的湖蓝色锦缎,袖口和衣襟处用银线细细绣着中原特有的缠枝莲纹,
在阳光下流淌着内敛的光华。乌黑的长发高高束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
少了几分公主的柔婉,多了几分飒爽英气。号角长鸣,声震四野!数十匹骏马如同离弦之箭,
在号角声落下的刹那猛地冲了出去!马蹄翻飞,踏起草屑泥块,大地为之震动。
赫连灼一马当先,黑马如一道闪电,瞬间将其他人甩开几个身位,
白色的狼裘坎肩在风中飞扬,气势惊人。李昭阳紧抿着唇,伏低身体,双腿紧紧夹住马腹,
手中的缰绳控制得极稳。她胯下的枣红马也是精心挑选的良驹,虽不及赫连灼那匹神骏,
却也奋力追赶,始终咬在赫连灼斜后方不远处,竟是女子中最快的一个!风在耳边呼啸,
将她的马尾高高扬起。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血液在血管中奔涌。
她感受着身下骏马每一次肌肉的爆发,感受着速度带来的极致快意,
目光紧紧锁住前方那道如火焰般跃动的黑色背影。一圈,两圈……终点在望!
就在这最后冲刺的关头,李昭阳左侧一个急于争抢位置的骑手猛地一夹马腹,坐骑受惊,
狠狠撞向她的枣红马!枣红马一声惊嘶,前蹄高高扬起,瞬间失控,
竟斜斜朝着赛道旁边一根粗壮的拴马桩猛冲过去!“啊——!”惊呼声四起。
电光火石之间,前方那道黑色的闪电猛地勒紧缰绳!高速奔驰的黑马发出一声痛苦的长嘶,
前蹄几乎直立而起,硬生生钉在原地!就在李昭阳连人带马即将撞上木桩的千钧一发之际,
一只强健有力的手臂如同铁钳般猛地探出,精准无比地揽住了她的腰!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李昭阳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瞬间脱离了马鞍!下一秒,她便落入一个坚硬滚烫的怀抱,
后背重重撞上坚实的胸膛,鼻尖充斥着浓烈的男性气息——风沙、皮革、汗水,
还有一丝淡淡的血腥气。赫连灼一手控缰,一手紧紧箍着她的腰,将她牢牢按在自己身前。
黑马因为骤然承受了两个人的重量而暴躁地原地踏了几步。“你疯了?!不要命了?!
”赫连灼的怒吼在她头顶炸开,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怒和后怕,灼热的呼吸喷在她的耳廓。
李昭阳惊魂未定,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腰被他勒得生疼。她急促地喘息着,
隔着薄薄的衣料,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腔里同样剧烈的心跳,一下下撞击着她的后背。
这感觉奇异又陌生。她猛地抬头,正对上他低垂下来的、燃烧着怒火的琥珀色眸子。
那里面翻涌的情绪太过复杂,有愤怒,有后怕,还有一种她看不懂的、深沉的悸动。
就在这四目相对的瞬间,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窜入李昭阳脑海。她压下狂跳的心,
喘息着,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穿透了赫连灼的怒吼和周围的嘈杂:“我要是赢了……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赫连灼的怒吼戛然而止。他像是没听清,又像是难以置信,
琥珀色的瞳孔骤然收缩:“什么?”“我说!”李昭阳提高了声音,
眼中闪烁着孤注一掷的亮光,直直地望进他眼底,“如果我赢了这场赛马,可汗大人,
你就得应我一个条件!”条件?在这种时候?
赫连灼简直要被这女人的胆大包天和异想天开气笑了。他箍在她腰间的手臂又收紧了几分,
几乎要将她揉进自己骨血里。“哈!好!好得很!”他怒极反笑,胸膛剧烈起伏,
盯着她因激动而格外明亮的眼睛,几乎是咬着牙吼道,“你若真能赢我,别说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天上的星星,老子也亲自给你搭梯子摘下来!开一条通天大道都行!现在,
给我坐稳了!”话音未落,他猛地一抖缰绳!黑马再次如离弦之箭般冲出!
李昭阳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她非但没有坐稳,反而在赫连灼的怀中猛地扭身,
一手反抓住他环在自己腰间的手臂借力,另一只手闪电般探出,
狠狠一鞭子抽在赫连灼那匹黑马的臀后!“驾!”黑马吃痛,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嘶,
速度再次飙升!这突如其来的加速让赫连灼措手不及,身体猛地后仰!就在这瞬间,
李昭阳借着这股冲力,像一条滑溜的鱼,竟从他怀中挣脱出来,以一个极其惊险的姿势,
重新扑向旁边那匹因受惊而稍稍落后、此刻正被一个侍卫死死拽住的枣红马!
她精准地抓住鞍鞯,翻身而上!“驾——!”清越的娇叱响彻赛场。
枣红马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破釜沉舟的决心,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四蹄腾空,
如同燃烧的流星,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竟真的在最后几十步的距离,
一点点、一点点地追上了那匹因负重和方才骤停而稍显迟滞的黑马!终点线近在咫尺!
李昭阳伏在马背上,身体压到最低,拼尽全力!在越过终点线的那一刹那,她猛地回头,
对着身后仅差半个马头的赫连灼,扬起一个混合着汗水、尘土和极致得意的笑容,
甚至挑衅地做了个极其幼稚的鬼脸:“可汗!说话——算话!”赫连灼勒住马,
胸膛剧烈起伏,
的眼眸死死盯着前方那个勒住马缰、在终点处兴奋地调转马头、脸上洋溢着胜利红晕的身影。
她鬓发散乱,额角沾着汗湿的尘土,那身精致的湖蓝色骑装也沾满了草屑泥点,狼狈不堪。
可那双眼睛,亮得如同淬了火的星辰,带着一种燃烧生命般的灼热光芒,穿透了赛场的喧嚣,
直直地撞进他眼底,撞得他心口一阵发麻。刚才她在怀中扭动挣脱时那惊人的柔韧和爆发力,
那不顾一切的疯狂,
那越过终点线时回头甩来的、带着汗水和尘土味道的鬼脸……无数画面在他脑中炸开。
一股从未有过的、极其陌生的热流,混杂着被挑衅的恼怒、棋逢对手的激赏,
以及一种更深沉、更汹涌的悸动,如同地下奔突的熔岩,轰然冲垮了他心头的堤坝。
他看着她,看着她那双比草原天空还要明亮的眼睛,只觉得喉咙发干,心跳如擂鼓,
擂得他耳膜嗡嗡作响。草原的夜,仿佛被水洗过一般。墨蓝的天穹低垂,
缀满了碎钻般的星辰,璀璨得触手可及。远处篝火的余烬明明灭灭,
映照着归巢的牛羊模糊的轮廓。赫连灼牵着两匹马,沉默地走在前面。
李昭阳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靴子踩在松软的草地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赛马场上那股近乎燃烧的亢奋早已褪去,只留下疲惫和一种奇异的、心照不宣的沉默。
晚风带着青草和露水的凉意,拂过两人汗湿的鬓角。“喂,”赫连灼忽然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地融进夜色里,“你要开的那条路……到底想做什么?”李昭阳也停下,
抬头看着前方他高大挺拔的背影,在星光下像一座沉默的山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