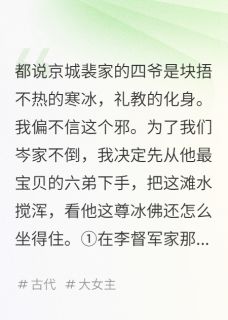都说京城裴家的四爷是块捂不热的寒冰,礼教的化身。我偏不信这个邪。为了我们岑家不倒,
我决定先从他最宝贝的六弟下手,把这滩水搅浑,看他这尊冰佛还怎么坐得住。
①在李督军家那场能把人活活无聊死的赏花宴上,我端着笑脸周旋了一整天,
感觉自己的脸皮都要僵硬得掉渣了。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让丫鬟卸掉头上沉甸甸的珠钗,
贴身的崔嬷嬷就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脸上血色尽失。她压着嗓子,声音都在发抖:「**,
出事了!外面……外面都在传您的闲话!」我对着西洋镜,慢条斯理地摘下耳坠子,
眼皮都没抬一下:「传我什么?如今这京城里,关于我的闲话还少吗?」
自打我们岑家生意一落千丈,从京城顶流的望族跌下来之后,
我岑霜晚就成了各家太太**们茶余饭后最好的谈资。不过,
靠着这张脸和父亲教的几分手段,我在交际场上依然混得风生水起,甚至比从前更甚。
她们越是嫉妒我,我就越是要活得光鲜亮丽。想到这,我没忍住,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勾了勾嘴角。崔嬷嬷急得直跺脚:「**您还笑!这次不一样!
他们说您和……和裴家的六少爷,行为不端!」哦?我这才来了点兴趣。「裴景卓?」
我转过身,捏起一颗葡萄送进嘴里,「我当是谁呢。」三天前,
我确实和裴家那个刚从西洋回来的六少爷在“思茗”茶楼喝了杯咖啡。
那小子大约是觉得被狗仔队跟踪很**,浑然不觉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
他紧张得一杯咖啡洒了半杯,话都没说完就落荒而逃。我以为拍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几张远景照片,掀不起什么风浪。崔嬷嬷的下一句话,却让我知道,事情比我想的更热闹。
「何止是喝咖啡!现在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你们在茶楼的包厢里……举止亲昵,
拉拉扯扯,就差没说你们……」后面的话,她没敢说出口。啧,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沉吟片刻,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忽然问崔嬷嬷:「这流言,
现在传得多厉害?」「已经……已经传进裴家老太太的耳朵里了!裴家最重门风,
这下可怎么收场啊!」崔嬷嬷的声音都带上了哭腔。我非但没慌,反而坐直了身子,
快速算了一下日子。「嬷嬷,裴家那位四爷,后天是不是要在‘知闲’山庄办一场清谈会,
遍邀京城名流?」崔嬷嬷被我问得一愣,不明所以:「是啊,**,您别扯开话题……」
「那就别澄清。」我打断她,对着镜中那个眉眼妩媚的自己,绽开一个艳丽到极致的笑,
「嬷嬷,你再去找几个嘴碎的,给我添柴加火。要闹,就闹得整个京城都知道,我岑霜晚,
看上裴六少了。」镜中的我,一身藕荷色的旗袍勾勒出纤秾合度的身段。
为了应付白天的场合,头发盘得一丝不苟,但现在几缕碎发垂落颊边,
平添了几分慵懒的风情。这张脸,眉眼深邃,鼻梁挺直,偏厚的嘴唇像是饱满的樱桃,
诱人采撷。左边眉峰上那颗小小的朱砂痣,更是点睛之笔,让这张本该是性感尤物的脸,
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娇俏。这张脸,就是我岑霜晚最后的,也是最强的本钱。而我,
恰巧是个最懂得如何利用自己本钱的女人。不理会崔嬷嬷满脸的惊恐和不解,
我径直走向妆台,拿起眉笔,细细描摹。「**,您……您这是要去哪儿?」
「去宠幸我这张脸啊。」我冲镜子里的她眨了眨眼,声音娇媚,「姐姐我赶时间,
要去杀出一条血路了。」我这辈子,有三大宏愿:重振岑家门楣。手握泼天富贵。
入主裴家宗祠。一个都不能少,全都要搞到手。而这一切的起点,就从今晚这个流言开始。
2崔嬷嬷办事向来靠谱。等我敷完一张贵得能换二两黄金的面膜,整个京城的上流圈子,
已经彻底被我和裴景卓的“风流韵事”给炸开了锅。那些平日里和我塑料姐妹情的名媛们,
一边在电话里假惺惺地问候我,一边在背后编排得比戏文还精彩。
我听着崔嬷嬷转述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词,笑得花枝乱颤。正乐着,
裴家六少爷的帖子就递了进来,措辞急得都快烧着纸了。「岑姐姐!
你为何不让府上的人出面辟谣?如今流言愈演愈烈,我……我都要被我四哥的眼神冻死了!」
那孩子的声音听着又委屈又郁闷。我坐在新铺的波斯地毯上,一边舒展着身体,
一边用最温柔的语气回信:「景卓弟弟,姐姐这天大的名声免费给你贴上来,你不说句谢谢,
还来质问我?」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字迹都透着抓狂:「我不要这种名声!
我四哥已经禁了我的足!姐姐,再这样下去,我怕是……怕是要跟那位**解释不清了!」
那位**?我挑了挑眉,心里升起一丝好奇。这才多久,这傻小子就有心上人了?「哦?
哪家的**,快说给姐姐听听。」裴景卓在信里支支吾吾,只反复强调:「您快些澄清便是!
别的不要问!」「啧。」我换了个姿势,慢悠悠地蘸墨写道:「可是姐姐我,
偏偏就不想澄清呢。」「岑、霜、晚!」隔着纸,
我都能想象到他气急败坏、连姐姐都不叫了的样子。我笑着回了最后一句:「我不猜。
姐姐我的脑子,要用在更重要的地方。」果然,之后再没收到他的信。
大概是真的被我气到了。我放下笔,一点也不恼,嘴角反而不受控制地向上翘起。
我从一个上了锁的红木匣子里,拿出一样东西。那不是相册,
而是一张小小的、巴掌大的素描。是我花重金,请了京城最有名的西洋画师,
躲在暗处偷着画的。画上只有一个男人。裴晏之。他正盘腿坐在书房的窗边看书,
身上穿着一件烟灰色的长衫。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他身上,他一手持卷,
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搭在旁边一只肥硕的波斯猫身上,
整个人就像一幅静止却充满张力的水墨画。那只猫,曾经是我的。名叫“白团子”。
我曾借口家里闹鼠疫,硬塞给他养了整整半年。为了接近他,
我真是把脸皮和计谋都用到了极致。可他就像块捂不热的万年寒冰。看着这张偷画来的肖像,
我没忍住,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画上那张清冷禁欲的脸。「裴晏之,
马上……就要见面了呢。」这时,裴景卓又让人递了张小纸条进来,上面只有一行字,
写得歪歪扭扭:「你们到底准备何时和好?我再不走,真要被我哥的冷气冻成冰雕了!」
和好?我倒是想啊。可惜,我和他,压根就没好过。3裴晏之,
如今京城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他不是官,却能影响内阁的决策;他不是帅,
手下却没有一兵一卒,却让各路军阀都给他三分薄面。裴家是百年望族,书香门第,
到了他这一代,更是将家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政、商、军各个领域。而他,
就是这一切幕后的操盘手。四年前,他一篇《论时局策》,精准预判了三省联军的溃败,
一举将摇摇欲坠的裴家重新推回了权力的牌桌上,
也让他自己成了无数人想要拉拢或除掉的对象。但他这个人,孤高自许,极难相处。
据说当年总统府亲自设宴,想请他出山,他连面都没露,
只托人带了一句话:「裴某只是一介书生,于国无用。」自那以后,
他“恃才傲物”的名声就传遍了京城。我最初,也是这么看他的。毕竟,
当年他那篇让他一战封神的《论时局策》,几乎是踩着我们岑家的尸骨上去的。若不是他,
我父亲的生意也不会败得那么惨。但偏偏,我岑霜晚什么都能抵抗,
就是扛不住一个男人的才华和那张祸国殃民的脸。于是,我收起了恨,换上了笑脸,
用尽各种方法去接近他,纠缠他……甚至,还用过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明确的回应。单纯的裴景卓,以为我早把他哥拿下了,
有段时间还偷偷叫我“四嫂”。我对这种美丽的误会乐见其成,也从没纠正过。
直到三个月前。我抱着我的“白团子”,怒气冲冲地从裴家大宅里冲出来,正好撞见裴景卓。
那小子小心翼翼地问我:「四嫂,你跟我哥吵架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
口不择言:「别叫我四嫂!我跟你哥,完了!彻底决裂!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这傻弟弟,
就真当我和他哥“分手”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和裴晏之,从头到尾,就没在一起过。
而那次争吵之后我才幡然醒悟,如果我不主动,裴晏之是真的可以一辈子都不找我。
整整三个月,我们之间连一张字条的往来都没有。想到这,我心里一阵阵地泛酸。
还没等我伤感完,裴景卓的求救信又像雪片一样飞来。
他连着让人送了十几张画着各种小人求饶的简笔画,幼稚得可爱。
我去冰窖里拿了瓶冰镇的酸梅汤,喝了两口,才慢悠悠地回他:「你哥怎么说?」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裴景卓秒回,「他什么都没说。」
我都能想象到他抓耳挠腮的样子。不等我回复,他又递来一张:「但姐姐你信我!
我哥他绝对生气了!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我当然知道裴晏之会生气。
但绝不是因为我吃醋。他那样一个把家族声誉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自己的亲弟弟,
竟然跟我这种“声名狼藉”的交际花纠缠不清,他不气炸了才怪。
于是我隔岸观火地回信:「那弟弟你好自为之,多哄哄他。」然后便将笔墨纸砚丢到一边,
安心睡我的美容觉去了。因为后天的清谈会,才是我真正的战场。要见到他了。这个认知,
让我的心提前好几天就开始不听话地乱跳。虽然,这流言本就是我为他一手策划的。最起码,
我们见面时,有话可说。哪怕是吵架。4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岑霜晚在任何社交场合,
都是暖场子的好手。但我从没想过,只是即将再次见到裴晏之这件事,
就让我提前两天开始手心冒汗。裴晏之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我从他那些流传出来的文章和诗稿里琢磨过。他笔下的理想世界,秩序井然,规矩森严。
他赞美的女性,也大多是贞静娴雅、端庄识大体的大家闺秀。而我,恰恰是这一切的反面。
可越是这样,我越是要反着来。清谈会这天,我特意挑了一件酒红色的改良旗袍。
料子是西洋传来的丝绒,紧紧包裹着身体,腰开得极低,一双腿在开衩处若隐若现。
头发松松地用一根碧玉簪子挽起,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和旗袍的颜色一衬,更是艳光四射。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许久,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勾引”二字。
我就是要让他看到,我就是这么一个离经叛道、上不了台面的女人。然后,我还要让他,
为我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发疯。到了“知闲”山庄,刚下汽车,
就冤家路窄地碰上了主人李督军和并肩而行的裴晏之。我立刻调整表情,摘下墨镜,
扭着腰肢走上前,笑得百媚横生:「李都督,裴四爷,这么巧。」
李督军眼中的惊艳毫不掩饰,笑呵呵地对裴晏之道:「晏之啊,你看,
我就说霜晚**是我们京城第一美人吧!这身段,这气韵,啧啧。」
我顺势将目光黏在裴晏之身上。他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那目光像一片冰凉的羽毛,
从我脸上刮过,没留下任何痕迹。随即,他抬手看了看腕上的金表,
对李督军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先进去吧。」说完,连个正眼都没再给我,
径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他走过时带起的风,都像是夹着冰碴子。李督军见状,
赶紧打着哈哈:「霜晚啊,你别介意,晏之这个脾气……你也知道……他这个人,
就是个活古董……」我看着裴晏之那冷硬的背影,非但没退缩,反而故意拔高了声音,
确保他能听得一清二楚:「李都督您多虑了,我怎么会跟四爷一般见识呢?
他老人家脾气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啊,习惯了。」走在前面的裴晏之,
背脊似乎僵硬了一瞬,但脚步未停。看来,他是真的气狠了,连场面上的风度都懒得维持了。
这样最好。5清谈会冗长又乏味。一群老头子引经据典,说的都是些陈词滥调。
我强撑着听完,被几个相熟的太太拉着说了半天话,等我再抬头,
整个厅里早就没了裴晏之的影子。说不失落是假的。我拦住一个正在收拾残局的侍者,
装作不经意地问:「裴四爷走了吗?」那侍者恭敬地回答:「回**,
刚才见四爷在后院的湖心亭里看书,现在还在不在,小的就不知了。」都这个时辰了,
他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书?可真有他的雅兴。我问清楚方位,提着裙摆就快步往后院走。果然,
在湖心亭那影影绰绰的灯笼光下,我一眼就瞧见了他孤高清冷的背影。我停下脚步,
对着光线昏暗的水面,借着倒影快速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襟,然后放慢了脚步,
一步三摇地走到他跟前。他正凝神看书,听到脚步声,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才抬起眼。
不等他开口,我直接在他对面的石凳上坐下,笑吟"「裴四爷真是好雅兴。
不过您刚才在会上的那番见解,可真是字字珠玑,振聋发聩。这新出的法案,
若是按您的意思改,必定能造福万民。」我先把他捧上天。裴晏之「啪」地一声合上书,
往后靠了靠,整个身子都陷在阴影里,只留一双眼睛,锐利得像鹰。「岑**也听得懂那些?
」他声音里那股子不加掩饰的嘲讽,比直接骂我还让我不爽。但我今天就是来让他不爽的。
我笑得愈发温婉动人:「跟在四爷身边死缠烂打了那么久,就算是块石头,
也该被四爷的墨水味给熏出几分文气了。」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上上下下地将我打量了一遍,最后目光落在我那过分暴露的旗袍开衩上。接着,他冷笑一声。
那笑声,像冰块砸在玉盘上。「岑霜晚,游戏人间是你的本事,但别把我弟弟拖下水!」
又是这句话。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不等我反驳,他又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更冷,
像是腊月里的寒风,刮得人骨头疼:「你就这么想进我裴家的门?」这句话,
成功地把我给气笑了。我花了足足三秒,才调整出一个堪称完美的、营业式的笑容:「是啊。
」我清晰地看到,裴晏之的脸色,黑了。我心底升起一股报复般的**,
继续用最甜最软的语气,说着最诛心的话:「能做您的妻,是霜晚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可既然您瞧不上我,那我努努力,做您的弟媳,似乎也不错?」「你!」
他像是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喉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里面风暴凝聚。他想骂我,可他那引以为傲的教养,让他骂不出一句脏话。
我欣赏着他隐忍到极致的表情,心里默默数到三十。见他依然没有开口的意思,
我便施施然站起身,理了理根本没乱的裙摆,
继续往他心口上捅刀子:「我知道四爷您瞧不上我,但没办法,景卓单纯,喜欢我这款的。
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说不得,我还要跟着景卓,喊您一声‘四哥’呢。」「所以,
为了景卓,也为了裴家的颜面,咱们以后……还是尽量,好生相处吧。」
裴晏之嘴唇瞬间绷成一条冷硬的直线。我知道,这是他怒气值积攒到顶峰的表现。
我大功告成,不再看他,拎着裙摆,踩着胜利的鼓点,快步离开。让他一个人,
在风里慢慢消化我的“宣战”吧。6我以为裴晏之就算再生气,也得顾及身份,
顶多是背地里给我使绊子。我万万没想到,他的报复来得那么快,那么狠,那么不留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