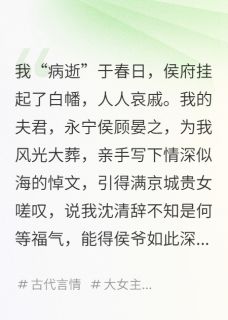我“病逝”于春日,侯府挂起了白幡,人人哀戚。我的夫君,永宁侯顾晏之,为我风光大葬,
亲手写下情深似海的悼文,引得满京城贵女嗟叹,说我沈清辞不知是何等福气,
能得侯爷如此深情。可无人知晓,我的灵堂前,他与那新宠柳云裳眉来眼去。
我“病重”时灌下的汤药,每一碗都带着慢性毒的苦涩。如今,距离我“下葬”已一年有余。
侯府的白幡早已撤下,换上了喜庆的红绸。我站在侯府侧门,一身青布长衫,面容蜡黄,
贴着一道浅浅的疤,以一个落魄书生的身份,前来应聘我儿子的夫子。透过半开的门缝,
我看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儿子景明。他瘦了,小小的身子裹在锦缎里,显得空空荡荡。他身旁,
站着一位珠翠环绕的女子,正是如今的侯府女主人,柳云裳。她正不耐烦地训斥着景明,
而我的儿子,只是低着头,沉默地绞着衣角。顾晏之,你以为我死了,
便可与你的心上人高枕无忧,尽享荣华?我回来了。以一个死人的身份,
回来教我的儿子读书。顺便,看一出你们如何作死的,好戏。1“下一位,苏文。
”管事尖细的嗓音传来,我整了整衣冠,压下心头翻涌的恨意,步履平稳地走入花厅。
厅内檀香袅袅,主位上坐着的,便是我阔别一年的夫君,永宁侯顾晏之。
他还是那副清隽矜贵的模样,眉眼深邃,只是眼底多了几分不耐。想来也是,
为了给景明寻个夫子,他已在此耗费了半日。他身旁,柳云裳正娇声细语地为他奉茶,
一身流光溢彩的云锦,衬得她愈发貌美。她见我进来,眼神轻飘飘地一扫,
掠过我蜡黄的脸和那道伪装的疤痕时,毫不掩饰地露出一丝嫌恶。“你就是苏文?
”顾晏之呷了口茶,淡淡开口,声音里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回侯爷,草民正是。
”我躬身行礼,嗓音刻意压得有些沙哑粗粝。这是我精心准备的身份。苏文,
一个家道中落的江南书生,学识尚可,却时运不济,流落京城。简单,干净,不起眼。
“抬起头来。”我依言抬头,目光坦然地迎上他的。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看到他持杯的手微微一顿,眉头不自觉地蹙起。我知道,这双眼睛。
这双曾盛满星光与爱意,后来又被冷漠与不耐填满的眼睛,是他最熟悉的。即便我换了容貌,
改了声音,但这眼神深处的东西,却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柳云裳立刻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她娇滴滴地靠过去,声音甜得发腻:“侯爷,怎么了?
可是这位先生的相貌……有些惊扰到您了?”她意有所指地看着我脸上的疤,
话语里满是恶意。顾晏之回过神,眼中的探究一闪而逝,恢复了惯有的冷漠:“无事。
苏先生,既是来教导世子的,学问想必不差。本侯考你一考。”接下来的半个时辰,
他从经史子集问到策论时务。这些,曾是我们闺房夜话的一部分。他考校我的学问,
我为他剖析朝堂局势。那时,他总爱揽着我的肩,赞我“有不输男儿之才智”。如今,
我将昔日的论点娓娓道来,只字不提过往,却字字都带着过往的影子。“……故草民以为,
治河之道,堵不如疏,当因势利导,方为长久之计。”我话音落下,厅内一片寂静。半晌,
顾晏之才沉声道:“先生大才。”柳云裳的脸色有些难看。她不过是个小官之女,
仗着有几分姿色,哪里听得懂这些。见顾晏之对我另眼相看,她心里早已不快。“侯爷,
光有学问有什么用?为人师表,品性才是最重要的。”她酸溜溜地开口,
“这位苏先生看起来……有些寒酸,别是冲着我们侯府的富贵来的吧?景明还小,
可不能被带坏了。”我心中冷笑。柳云裳,你才是那个为了富贵不择手段的人。
顾晏之瞥了她一眼,似乎有些不悦她的插话,但终究没说什么。他看向我,问道:“苏先生,
你对我儿景明,有何看法?”终于问到点子上了。我垂下眼帘,沉声道:“草民方才在门外,
有幸见过小世子一面。”“小世子天资聪颖,眉宇间自有贵气。只是……”我顿了顿,
抬眼直视着他,“只是似乎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孩童天性烂漫,小世子这般模样,
恐非心性使然,而是外物所扰。教书之前,需先育人。若要小世子成才,必先解其心结,
复其本性。”这番话,如同一根针,精准地刺向了顾晏之的心。
我看到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景明是他的嫡长子,是他唯一的血脉。自我“死”后,
他或许一时被柳云裳迷了眼,但对这个儿子,他不可能全然不在意。
柳云裳的脸色更是“刷”地一下白了。我这番话,无疑是在暗指她这个继母苛待了孩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她尖声叫了起来,“景明好好的,哪里郁郁寡欢了?你一个外人,
懂什么!我看你就是妖言惑众,想攀附侯府!”“够了!”顾晏之猛地一拍扶手,
厉声喝止了她。柳云裳吓得一哆嗦,眼圈瞬间就红了,
委屈地看着他:“侯爷……”顾晏之却看也没看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中风云变幻。
“苏文,”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从明日起,你便入府,为世子之师。月俸五十两,
府内自有院落供你居住。”柳云裳的表情瞬间僵住,满脸的不可置信。我心中一片冰冷,
面上却不露分毫,只是恭敬地长揖及地:“草民,谢侯爷赏识。”很好,顾晏之。这第一步,
我踏进来了。2我被安排在侯府东侧一处名为“听竹轩”的小院。这里偏僻清静,
离景明的“观云阁”不远,倒是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为我引路的是府里的老人福伯。
他自我嫁入侯府时便在,为人忠厚。见我时,他只是低着头,恭敬地称我“苏先生”,
眼中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苏先生,院子都收拾妥当了。您若还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老奴。”福伯的声音有些苍老。“有劳福伯。”我点点头,
目光扫过院中那几竿翠竹,“此处甚好。”福伯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我知道他的心思。我方才在花厅的那番话,定然让他想起了曾经的女主人。我推门入屋,
屋内的陈设简单雅洁,一应俱全。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正好能看到观云阁的一角飞檐。
景明……我的孩子,母亲回来了。这一夜,我几乎未眠。
脑海中反复回想着景明那瘦小的身影,和他眼底深藏的怯懦。一年前,我假死脱身时,
景明尚在我母亲家中。我派人送去信,只说自己得了急症,要去南方静养,归期未定。
我不敢告诉他真相,怕他年幼,承受不住这等变故。我原以为,顾晏之再薄情,
总归是景明的亲生父亲,虎毒不食子。可今日一见,我才知我错得有多离谱。柳云裳的出现,
让景明在自己家里,活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次日清晨,我梳洗已毕,
换上一身干净的青衫,前往观云阁。还未走近,便听见柳云裳尖利的声音。“哭哭哭!
就知道哭!一大早的晦不晦气!不就是打碎了一个杯子吗?你母亲留下的东西就那么金贵?
我是短你吃了还是短你穿了,让你天天抱着那些死人的东西!”我心头一紧,加快了脚步。
只见院中,景明跪在冰冷的石板上,面前是一地碎瓷。那是我最爱的一套雨过天青色的茶具,
景明知道,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柳云裳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满脸刻薄。
她身边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丫鬟,正是我从前的二等丫鬟,后来背叛我投靠了柳云裳的春桃。
“夫人,您消消气,为个小孩子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春桃谄媚地笑着,“世子爷也是,
夫人给您新买的玉瓷杯不用,非要用这些旧东西,这不是存心惹夫人生气吗?
”“一个没娘的野孩子,也配跟我置气?”柳云裳冷哼一声,抬脚就要去踹景明。“住手!
”我一声厉喝,快步上前,将景明一把拉起,护在身后。景明小小的身子还在发抖,
他抬起头,一双酷似我的眼睛红通通的,带着泪水和惊恐,
怔怔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苏先生”。那一刻,我的心像被刀剜一样疼。
柳云裳没料到我敢出声,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你是谁?好大的胆子,
敢管本夫人的事!”“草民苏文,是侯爷昨日亲聘的世子之师。”我冷冷地看着她,
“为人师表,见学生受辱,不能不管。”“夫子?”柳云裳上下打量着我,嗤笑一声,
“原来就是你这个穷酸书生。怎么?第一天来就想给我个下马威?你以为你是谁?
侯爷请你来是教书的,不是让你多管闲事的!”“世子为何跪在此处?
”我没有理会她的叫嚣,只是沉声问道。“他打碎了东西,手脚笨,就该罚!
”柳云裳理直气壮。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碎瓷,又看了看景明微微泛红的手背,
心中已然明了。“哦?是吗?”我弯下腰,仔细查看那些碎片,“这套雨过天青,釉色纯净,
乃是前朝官窑所出,价值不菲。更重要的是,这碎裂的截面……光滑平整,不似失手摔落,
倒像是被人从旁撞击所致。”我一边说,一边抬眼看向一旁的春桃。春桃的脸色瞬间白了。
柳云裳一滞,随即恼羞成怒:“你胡说什么!一个破杯子而已,就算是我撞的又怎么样?
我是主母,教训一个孩子,难道还要跟你一个外人交代不成?”她这是不打自招了。
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平静:“夫人自然是主母。只是,世子乃侯府嫡长子,
未来的继承人。如今他跪在这里,伤的是身,损的却是侯府的颜面。若传出去,
外人会如何议论侯爷与夫人?是说侯爷治家不严,还是说夫人……德不配位?”“你!
”柳云裳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你竟敢诅咒我!”“草民不敢。”我直起身,
将景明护得更紧,“草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世子殿下该上课了,请夫人行个方便。
”我的态度不卑不亢,语气却字字诛心。柳云裳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张俏脸涨成了猪肝色。
她想发作,却又找不到由头。毕竟,“德不配位”这四个字,对她这种继室来说,
是最大的忌讳。正在这时,一个沉稳的脚步声传来。“一大早的,吵什么?
”顾晏之走了进来。3顾晏之的出现,让僵持的气氛瞬间凝固。柳云裳一看到他,
立刻像换了个人,脸上的刻薄瞬间化为满腹委屈,眼泪说来就来,扑到他身边哭诉:“侯爷,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这个新来的苏先生,一上来就顶撞妾身,还、还咒我德不配位!
”她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正是顾晏之最吃的那一套。我心中冷笑,面上却毫无惧色,
只是对着顾晏之躬身行礼:“侯爷。”顾晏之的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景明,
又看了看满地碎瓷,最后落在我脸上,眼神幽深。“苏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不等我开口,
柳云裳就抢着说:“侯爷,是景明!他打碎了您最喜欢的那套茶具,我不过是说了他两句,
他就又哭又闹。苏先生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我,还说我苛待景明……”她避重就轻,
颠倒黑白,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了委屈的好继母。顾晏之听完,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看向我,
似乎在等我的解释。我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平静地问景明:“景明,你告诉为师,
杯子是怎么碎的?”我特意用了“为师”二字,提醒顾晏之我的身份。
景明怯生生地看了柳云裳一眼,又看了看顾晏之,嘴唇嗫嚅着,不敢说话。他的恐惧,
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柳云裳见状,心中得意,又假惺惺地劝道:“景明,别怕,
有爹爹在这儿呢。快告诉爹爹,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的?没关系,爹爹不会怪你的。
”她这是在威逼利诱。我心中怒火翻腾,但知道此刻不能硬来。我蹲下身,与景明平视,
放柔了声音:“景明,看着我。为师只问你一句话,是与不是,你点头或摇头即可。这杯子,
是你自己失手打碎的吗?”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景明怔怔地看着我,
从我这双陌生的眼睛里,他似乎看到了一丝熟悉的温暖和坚定。他犹豫了片刻,终于,
缓缓地、却无比坚定地摇了摇头。这一个摇头,让柳云裳的脸色瞬间煞白。
顾晏之的瞳孔也是一缩。“你……你这个小畜生!”柳云裳气急败坏,口不择言,
“我白疼你了!你竟敢联合一个外人来污蔑我!”“够了!”顾晏之再次厉声喝止她,
“当着孩子的面,像什么样子!”他扶起景明,亲**了拍他膝盖上的灰尘,
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压抑的怒火:“景明,你先跟苏先生去书房。”然后,他转向我,
语气复杂:“苏先生,今日之事,让你见笑了。犬子顽劣,以后……劳你费心了。
”他没有追究,也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没有像往常一样,
无条件地相信柳云裳的眼泪。我心中了然,牵起景明冰冷的小手,领着他向书房走去。
自始至终,没有再看柳云裳一眼。身后,传来柳云裳不甘的哭泣声,和顾晏之隐忍的安抚声。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在我亲手播撒下,在顾晏之的心里,
悄然发了芽。4观云阁的书房,曾是我亲手布置的。一排排紫檀木书架,
上面摆满了我为景明精挑细选的启蒙读物。窗边的大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可如今,
书房里却蒙上了一层灰。原本摆在架子上的几本珍贵古籍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做工粗糙的玩物。我牵着景明走进去,他的情绪依旧很低落。“景明,
从今日起,我便是你的夫子。”我让他坐在书案前,自己则在他对面坐下,
“我们先从认字开始,好不好?”他低着头,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害怕,也不逼他。
我取过一本《千字文》,用温和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他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的声音平稳而舒缓,渐渐地,景明紧绷的小身子放松了下来。
他抬起头,偷偷地看我,眼神里带着好奇。“苏先生……你的声音,
有点像……”他小声地嘟囔了一句,又很快低下头去。像你娘亲,是不是?我的心尖一颤,
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深吸一口气,装作没听清的样子,问道:“像什么?
”“没什么。”他摇摇头,拿起笔,开始笨拙地模仿我写的字。看着他认真的侧脸,
我的鼻子一阵发酸。一连几日,我都待在听竹轩和观云阁两点一线。白日里教景明读书习字,
晚上则在灯下整理思绪,谋划下一步。景明很聪明,许多东西一点就透,学得很快。
在我的引导下,他也渐渐开朗了一些,不再像最初那般胆怯。但柳云裳显然没打算就此罢休。
她无法直接对我下手,便把气都撒在了景明身上。观云阁的下人被她换了一大半,
剩下几个老人也战战兢兢,不敢与我们亲近。景明的饮食被克扣,送来的饭菜常常是冷的,
衣物也久久无人浆洗。我没有声张,只是默默记在心里。
我让福伯暗中帮我联系上了我曾经的陪嫁嬷嬷,张嬷嬷。张嬷嬷自我“病逝”后,
便被柳云裳寻了个由头打发到庄子上去了。接到我的信,她连夜赶回京城,
在城外一处茶寮与我见了面。看到我如今的模样,年过半百的张嬷嬷老泪纵横,
抱着我哭得说不出话。“**……您受苦了!老奴就知道,您不会就这么去了的!”“嬷嬷,
别哭。”我为她拭去眼泪,将这一年来的事情简略说了一遍,“我回来,一为景明,
二为复仇。我需要你在府外帮我。”张嬷嬷抹了把泪,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您吩咐!
老奴这条命都是您给的,万死不辞!”我将我的计划告诉了她。柳云裳出身小官之家,
根基浅薄。她嫁入侯府,最大的靠山就是顾晏之的宠爱。但她贪婪愚蠢,最大的软肋,
便是她那吸血鬼一般的娘家。“嬷嬷,你帮我盯紧柳家。柳云裳当了侯府主母,
她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还有她那对贪得无厌的父母,绝不会安分。”“老奴明白!
”有了张嬷嬷在外面接应,我便如虎添翼。很快,机会就来了。这日,我正在教景明画画,
春桃走了进来,趾高气扬地说道:“苏先生,夫人请您过去一趟。”我放下笔,
对景明道:“你先自己练习。”跟着春桃来到柳云裳的院子,只见她正歪在贵妃榻上,
一边吃着西域进贡的葡萄,一边翻看一本册子。“苏先生来了。”她眼皮都未抬一下,
“听说你画技不错?”“略懂一二。”我平静地回答。“正好。”她将手中的册子丢给我,
“我娘家新盖了座园子,正缺一幅镇宅的《松鹤延年图》。这事就交给你了,十日之内画好,
不得有误。”我接过册子,那是一本画谱,但她言语间的颐指气使,
仿佛我不是侯府请来的夫子,而是她可以随意使唤的画师。“夫人,”我翻开画谱,
淡淡开口,“草民是世子的夫子,职责是教导世子。画画之事,恐怕有违侯爷所托。
”“让你画你就画,哪来那么多废话!”柳云裳不耐烦地坐起身,“怎么?瞧不起我娘家?
别忘了,你的月俸可是侯府发的,让你做点事是看得起你!”我心中冷笑。她果然按捺不住,
开始利用侯府的资源为娘家谋利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夫人言重了。”我合上画谱,
微微躬身,“只是,这《松鹤延年图》气势恢宏,需要上好的徽墨、宣纸和颜料。
尤其是那画中仙鹤顶上的一点朱红,需用上等的赤金朱砂方能显其神韵。
这些……”“行了行了,不就是要钱吗?”柳云裳鄙夷地打断我,
从手边的匣子里取出一张银票,随手丢在桌上,“这是一百两,够不够?别跟我耍花样,
画不好,仔细你的皮!”我走上前,拿起那张银票,收入袖中。“草民,遵命。
”5我拿着这一百两银子,并没有立刻去买什么上好的笔墨纸砚。
我让福伯帮我寻了京城最好的装裱师傅,
将我陪嫁单子里一幅前朝大家郑思公的《墨兰图》取了出来。这幅画,自我“死”后,
便一直被封存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然后,我用最普通的纸笔,
画了一幅形似神不似的《松鹤延年图》。画工粗糙,用色俗气,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敷衍之作。
十日后,我带着这幅“大作”去见柳云裳。她展开画卷一看,柳眉倒竖,勃然大怒:“苏文!
你这是画的什么东西!这仙鹤跟只病鸡似的,松树也歪歪扭扭,你是在糊弄我吗?
”“回夫人,草民画技鄙陋,实在有负所托。”我一脸“诚惶恐恐”,“而且,
夫人给的一百两银子,也实在买不到上等的赤金朱砂。草民尽力了。”“废物!
”柳云裳气得将画揉成一团,狠狠砸在我身上,“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侯府养你何用!滚!
给我滚出去!”我“狼狈”地退了出去,心中却是一片平静。鱼儿,已经开始咬钩了。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顾晏之便来了听竹轩。他来时,我正在灯下教景明写字。见他进来,
景明有些害怕地往我身后缩了缩。“爹爹。”他小声地喊了一句。顾晏之“嗯”了一声,
目光复杂地看着我们父子二人其乐融融的场景。他挥手让景明先下去休息,
书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苏先生。”他走到书案前,目光落在我刚刚画的一幅竹上,
“先生的画,清雅风骨,颇有大家之风。
为何给夫人画的《松天鹤寿图》却……”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府里的下人嘴杂,
今天柳云裳发怒的事情,想必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我放下笔,叹了口气,
一脸为难:“侯爷明鉴。非是草民不尽心,实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哦?
”“夫人所要的《松鹤延年图》,对笔墨颜料要求极高。尤其是那点睛的朱砂,
需用上等贡品。夫人所给的一百两,在京城最好的墨斋‘集雅轩’,
连半两赤金朱砂都买不到。”我半真半假地说道,“草民不敢擅动侯府公中财物,
只能用普通颜料替代,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惹得夫人生气,是草民的不是。
”我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解释了画作粗糙的原因,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还顺便点出了柳云裳的小气和外行。顾晏之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不是蠢人,
自然听得出我的言外之意。柳家要办喜事,却反过来让侯府的夫子出人出力,
甚至连材料钱都想克扣,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些。“集雅轩的赤金朱砂,一两需三百金。
”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侯爷博闻。”我躬身道,“草民不敢欺瞒。
”空气中一片沉默。顾晏之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这张平平无奇的脸上看出什么端倪。“苏文,
”他忽然开口,换了个话题,“你似乎……很了解我那位亡妻。”我的心猛地一跳,
面上却不动声色:“侯爷何出此言?”“你教景明的画法,你对书房陈设的看法,
甚至你方才说的‘堵不如疏’的治河之策……”他一步步逼近,眼中带着锐利的审视,
“都和她,如出一辙。”我的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我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他对沈清辞的“了解”,竟到了如此细致入微的地步。这究竟是深情,还是多疑?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垂下眼帘,用一种带着几分追忆和伤感的语气说道:“回侯爷,
草民的恩师,曾与前侯夫人沈氏有过数面之缘。恩师常赞夫人聪慧通达,才情卓绝,
并将夫人的一些见解说与草民听。草民耳濡目染,深受其益,不想竟在侯爷面前班门弄斧了。
”我临时捏造了一个“恩师”,将一切都推了过去。这个理由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