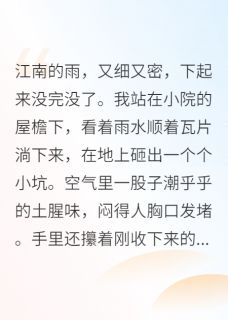“哟,小婉,这就是你家那口子吧?可算回来了!”张大婶嗓门洪亮,
隔着篱笆好奇地打量正在笨拙地修补篱笆的李承(他把篱笆弄得更歪了),
“小伙子长得可真精神!就是……看着身子骨有点虚?得好好补补啊!
”李承听到“你家那口子”几个字时,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修补篱笆的手也停住了。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带着一丝隐秘的期待和……忐忑。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张大婶自顾自地说开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小婉一个人不容易!
小伙子,好好对你媳妇儿!这年头,能守着家等男人回来的女人,可不多喽!
”李承沉默地听着,握着锤子的手,指节微微发白。他低着头,继续敲打着歪歪扭扭的篱笆,
动作缓慢而沉重。那天之后,他干活更卖力了。劈柴挑水,抢着干。
甚至真的跑去镇上的码头,想找扛包的活。结果人家看他虽然高大,但脸色苍白,
动作也不够利索,又不像常年干苦力的,只当他是个落魄书生,挥挥手就把他打发走了。
他有些沮丧地回来,坐在院子的石阶上发呆。我看着他失落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晚上,我在灯下绣花。他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借着昏暗的光,笨拙地拿着一根针,
试图帮我分线。那骨节分明、曾执掌朱批、挥斥方遒的手,此刻捏着一根小小的绣花针,
显得无比笨拙和滑稽。线被他搅成了一团乱麻。“别添乱了。”我忍不住开口,
语气带着一丝无奈。他讪讪地放下针线,像个做错事被大人训斥的孩子。沉默了一会儿,
他低声说:“我……我想帮你。”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我没理他,
继续绣我的花。又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的声音再次响起,低沉而沙哑,
带着一种沉痛的自省,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小婉……我知道……我以前……很混账。
”“我以为……给你身份,给你体面,
……错得离谱……”“那些女人……那些争斗……我总以为我能掌控……以为只要不闹出格,
就无伤大雅……是我太自负……太蠢……”“孩子……”他的声音哽咽了一下,
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他……每次想起……这里……”他用手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心口,
发出沉闷的响声,“就像刀子在绞……”他抬起头,眼眶通红,泪水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光,
却倔强地没有落下。他看着我的眼睛,
怕……你永远只是喻小婉……永远不想记起李承这个人……也没关系……”他的声音颤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