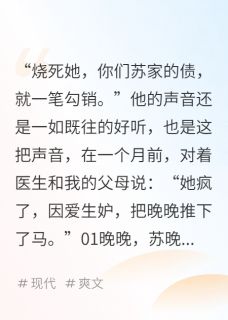“烧死她,你们苏家的债,就一笔勾销。”他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也是这把声音,
在一个月前,对着医生和我的父母说:“她疯了,因爱生妒,把晚晚推下了马。”01晚晚,
苏晚晚,他养在心尖上、碰不得、说不得的白月光。而我,林舒,他明媒正娶的未婚妻,
就因为在他策划的派对上,苏晚晚“意外”坠马成了植物人,
便被他亲手送进了这家全市最昂贵的私人精神病院。我的辩解,我的眼泪,我的证据,
在他一句“我只相信我看到的”面前,都成了因嫉妒而狡辩的疯话。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强制的药物注射让我的神经日夜在亢奋与迟钝间撕扯,
手腕和脚踝上满是挣扎时被束缚带勒出的淤青。我的父母被他拦在门外,
散尽家财也请不来一个能为我说话的律师。我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鸟,
被困在这金丝笼铸就的地狱里,日夜盼着他能良心发现。直到今天。门外,
苏晚晚的哥哥苏浩,声音里带着贪婪的确认:“顾少,您说真的?
只要这个疯女人死了……”“我顾景渊说话,一言九鼎。”顾景渊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波澜,
仿佛在谈论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垃圾,
“一场意外的疗养室线路老化引发的火灾,合情合理。你们拿到钱,我拿到安宁,
晚晚也能得到告慰。”我的血,一寸寸凉了下去。原来,把我关在这里,折磨我,
只是第一步。他真正想要的,是我的命。用我的命,去填补苏家的债务窟窿,
去告慰他那生死不知的白月光。我蜷缩在冰冷的墙角,浑身抑制不住地发抖。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一种从骨髓深处蔓延开来的,极致的恨意。我死死咬住嘴唇,
直到口腔里弥漫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好,顾景渊,真好。你不是要我死吗?我死给你看。
但不是像你设计的那样,屈辱地、无声地,化为一捧骨灰。
我要让这场你为我准备的死亡盛宴,成为我逃离地狱的门票。铁门外,脚步声远了。
我扶着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那扇小小的、焊着铁栏杆的窗前。窗外,
是精神病院里修剪得过分整齐的草坪,再远一点,是两米高的电网。我曾以为,
这里是我的坟墓。现在我才知道,这里,是我的起点。夜,很快就来了。今晚的镇静剂,
我没有吞下去,而是藏在了舌下。等护士走后,我悉数吐了出来。我需要最清醒的头脑,
来迎接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豪赌。凌晨两点,万籁俱寂。我能闻到空气中,
开始弥漫起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它来了,顾景渊为我准备的“意外”。我走到门边,
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下地撞着那扇厚重的铁门,发出声嘶力竭的嘶吼:“来人!救命!
着火了!救命啊!”我的喊声在空寂的走廊里回荡,带着绝望的颤音,像一只垂死的困兽。
浓烟开始从门缝里争先恐后地涌进来,呛得我不住地咳嗽,眼泪直流。
火势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还要猛烈。苏家的人,还真是拿钱办事,一点都不含糊。很快,
走廊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惊慌的叫喊声。“快!307室着火了!”“病人还在里面!
”有人在外面疯狂地砸门,但不知道顾景渊做了什么手脚,这扇门被从外面反锁了,
钥匙根本打不开。火舌已经舔上了门板,发出“噼啪”的爆裂声。高温灼烧着空气,
我感觉自己的皮肤都在刺痛。“不行!门打不开!”“快拿灭火器!来不及了!”混乱中,
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那个一直对我心存善意的护工张阿姨,她带着哭腔喊:“小舒!
林舒!你听得到吗?”我缩在离门最远的墙角,用湿透的病号服捂住口鼻,眼中没有恐惧,
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我要让所有人都相信,我被困死在了里面。
就在浓烟几乎要将我吞噬殆尽时,我头顶的天花板通风口,那块铁网栅栏,
突然被人从外面撬动了。“快!抓住绳子!”一个刻意压低的、陌生的男声传来。
一根粗壮的绳索垂了下来。我毫不犹豫地抓住它,双脚用力蹬在墙上,在那人的拉拽下,
艰难地爬进了狭窄的通风管道。02通风管道里一片漆黑,充满了灰尘和铁锈味。
我被那人拉着,在狭窄的空间里匍匐前进,膝盖和手肘很快就被粗糙的铁皮磨破,
**辣地疼。但这点疼,和我心里的恨比起来,什么都算不上。身后,
火场的喧嚣声越来越远,最终被沉闷的爬行声取代。不知过了多久,前面终于透进一丝微光。
那人撬开另一个通风口,我们落在一间无人的储物室里。月光从高窗照进来,
我这才看清救我的人。他很高,穿着一身黑色的作战服,戴着兜帽和口罩,
只露出一双深邃得不见底的眼睛。那双眼睛,锐利、冷静,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漠然。
“你是谁?”我哑声问,喉咙被烟熏得像要裂开。“救你的人。”他言简意赅,
递给我一个背包,“换上衣服,我们有十分钟。”我没有多问,迅速脱下肮脏的病号服,
换上背包里干净的T恤和长裤。陌生的触感包裹住身体,像一层新的皮肤,隔绝了过去。
“为什么要救我?”我一边整理衣服,一边盯着他。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善意,
尤其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他终于摘下口罩,
露出一张俊美却冰冷的脸。这张脸,我认识。沈司,沈氏集团的继承人,
在京圈是唯一能和顾景渊分庭抗礼的存在。他们两家是商场上斗了几十年的死对头。
我瞬间明白了。救我,不是善心,是投资。我是他用来对付顾景渊的一把刀。
“我凭什么相信你?”我问。“凭这个。”沈司将一部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段视频。
视频里,是精神病院的监控室。顾景渊赫然坐在里面,平静地看着监控屏幕上,
我所在的307室燃起熊熊大火。他身边站着院长,谄媚地笑着:“顾少放心,
一切都处理好了,绝对是一场意外。”顾景渊没有说话,只是端起桌上的咖啡,
轻轻抿了一口。那双我曾痴迷过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仿佛在欣赏一场与他无关的烟火。我的心,被这无声的画面,凌迟得鲜血淋漓。
“他想让你死得无声无息,而我想让他死得人尽皆知。”沈司收回手机,声音冰冷,
“我提供平台和资源,你负责执行。事成之后,顾家的一切,我拿七成,你拿三成,
包括顾景渊的命。”他的话里,没有半分感情,像是在谈一桩最寻常的生意。我看着他,
这个男人和顾景渊一样,都是站在权力顶端的捕食者。唯一的区别是,顾景渊想让我死,
而他,给了我一个复仇的机会。“我不要钱。”我摇了摇头,一字一句地说,
“我只要顾景渊,还有苏晚晚,亲身体验一遍我所受过的所有痛苦。我要他们身败名裂,
众叛亲离,最后,被全世界当成疯子。”我要的不是他的钱,不是他的命。我要诛他的心。
沈司看着我,那双深潭般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波澜,那是一种近似于欣赏的审视。
“可以。”他点头,“你的要求,比钱有趣多了。”他递给我一张新的身份证和一本护照,
上面的名字是“林鸢”,照片是我,但眉眼间经过了巧妙的微调,既有我的影子,
又判若两人。“从今天起,林舒已经死在了那场大火里。”沈司说,“你是林鸢,去瑞士,
我会安排你进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你需要的一切,我都会提供。
”“心理学?”我皱眉。“对付疯子,最好的武器,就是成为比他们更懂操纵人心的专家。
”沈司的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顾景渊最在乎什么?苏晚晚。等她醒来,你,
就是治愈她的最后一张王牌。也是亲手把他拖进地狱的,催命符。”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漫长而精密的计划。他要的不是一时的胜利,而是釜底抽薪的毁灭。这正合我意。
“好。”我接过证件,紧紧攥在手里,“成交。”那天晚上,我跟着沈司,像一个影子,
无声无息地离开了那座城市。第二天,我“死亡”的消息,登上了本地新闻的社会版。
标题是:《豪门订婚宴悲剧后续,女主角意外葬身火海》。报道里,
顾景渊在镜头前“悲痛欲绝”,他说他对我心存愧疚,没想到一场意外,竟让我们天人永隔。
他演得那么好,深情款款,无数不知情的网友在评论区为他点蜡,
咒骂我这个“蛇蝎女人”死有余辜。我坐在飞往苏黎世的航班上,
看着手机屏幕上他虚伪的脸,笑了。03苏黎世的冬天很长,雪很大。
我把自己埋进了知识的雪堆里,像一株在极寒中汲取养分的植物。沈司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顶级的导师,独立的实验室,以及源源不断的研究经费。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以最快的速度,
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警校第一的底子还在,我学东西很快。
逻辑分析、犯罪心理、行为侧写,这些我曾经引以为傲的技能,
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领域里,找到了新的共鸣。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
以为爱情就是全世界的林舒。我是林鸢,一个冷静、偏执,以复仇为唯一信仰的机器。
我剪掉了长发,换上了最简单的白大褂和黑框眼镜。我不再化妆,
任由苍白的脸色和眼底的青黑成为我的保护色。我疯狂地阅读、做实验、写论文,三年时间,
我拿下了别人需要八年才能完成的双博士学位。我的导师,一位诺贝尔奖提名者,
称我是他见过最“纯粹”的天才。他不知道,驱动我的不是对科学的热爱,
而是对地狱的仇恨。这三年,我没有主动联系过沈司一次,
但他会定期将顾景渊和苏晚晚的消息,像投喂饲料一样,发到我的加密邮箱里。
苏晚晚还躺在VIP病房里,是个植物人。顾景渊对她“不离不弃”,
每天都会去病房陪她说话,为她擦洗身体。这段“京圈情圣”的佳话,被媒体大肆宣扬,
为顾氏集团赚足了声誉和好感。他甚至以我和苏晚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专门救助因意外事故受伤的女性。多可笑。一个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了救世主。
每次看到这些消息,我心里的恨意,就像被喂了养料的藤蔓,疯狂地滋长,盘根错节,
几乎要撑破我的胸膛。我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了学业上。我专攻的方向,
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记忆植入。我要的,不只是让苏晚晚醒来。
我要在她的大脑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颗只有我能引爆,
能将他们所有人炸得粉身碎骨的炸弹。第三年的秋天,我正在实验室分析一组脑电波数据,
沈司的加密电话打了过来。“她醒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我握着鼠标的手,
倏然收紧。“苏晚晚醒了。但情况很不好。”沈司继续说道,“三年的植物人状态,
让她的大脑部分功能受损。她醒来后,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有严重的应激障碍和被害妄想,
除了顾景渊,攻击所有靠近她的人。”我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向上扬起。“时机到了。”我说。“没错。”沈司说,
“顾景渊已经为她找遍了全世界的名医,都没用。现在,轮到你登场了。”“他会信我吗?
”“会的。”沈司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嘲弄,
“我已经把你包装成了瑞士归来的神秘心理干预专家‘Dr.Lin’,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并且,我高调宣布,聘请你做我的私人心理顾问。以顾景渊多疑的性格,
他不会用我的‘人’。所以,我会安排一场‘意外’,让你和他最信任的世交叔叔,李教授,
‘偶遇’。”这个局,他已经布了三年。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一周后,
我以“Dr.Lin”的身份,回到了那座让我涅槃的城市。
在沈司安排的一场学术论坛上,我见到了李教授。他是我国神经科学领域的泰斗,
也是看着顾景渊长大的长辈。我在茶歇时,
“不经意”地和他探讨了一个关于“长期昏迷患者苏醒后记忆重塑”的课题。
我抛出的观点和理论,都是这个领域最前沿,甚至有些是超前的。李教授从最初的惊讶,
到后来的凝重,最后,变成了全然的欣赏和激动。“林博士,你……你简直是……个天才!
”他握着我的手,像发现了一块稀世珍宝,“景渊那孩子为了晚晚的事,都快愁白了头。你,
你愿不愿意……去看看她?”鱼,上钩了。我故作为难地蹙了蹙眉:“李教授,我很抱歉。
我刚回国,已经接受了沈氏集团的聘约,恐怕……”“沈司那个混小子!”李教授一听,
果然急了,“他能给你什么,顾家双倍,不,三倍给你!林博士,这不仅是救一个病人,
更是救一个家庭啊!”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在李教授几乎是恳求的目光中,
我“勉强”地点了点头。“既然是您开口,我愿意尝试一下。但事先说好,
我的治疗方法很特殊,需要病人家属,尤其是顾先生的,百分之百的配合。”“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李教授大喜过望,立刻就去给顾景渊打电话。04再次见到顾景渊,
是在那间我曾住了三年的VIP病房里。只是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换成了苏晚晚。
我跟在李教授身后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他。他坐在床边,正低头为苏晚晚削苹果,
侧脸的线条依旧英挺得像一尊雕塑。岁月似乎格外厚待他,三年过去,
他身上那股高高在上的矜贵气,只增不减。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我清晰地看到,他握着水果刀的手,微微一顿。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足足三秒,
那双深邃的黑眸里,闪过一丝不易察ANO的困惑与探究,仿佛想从我这张陌生的脸上,
找出什么熟悉的痕迹。我的心跳,在那一刻漏跳了半拍,
但随即被我用强大的自制力压了下去。我朝他礼貌地、疏离地,微微颔首。“顾先生,你好,
我是林鸢。”我的声音,经过三年的刻意训练,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它更低,更平,
带着一种学者的沉稳,不带任何感**彩。他眼中的那一丝困惑,很快就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审视和挑剔。“林博士,”他放下水果刀,站起身,
颀长的身影带着一股迫人的压力,“李叔叔把你夸上了天,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我会尽力而为。”我平静地回答,目光转向病床上的苏晚晚。她很瘦,瘦得脱了相,
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睁得大大的,却空洞无神,像个精致的坏掉的娃娃。
一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她立刻蜷缩起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威胁声,像一只受惊的小兽。
顾景渊立刻回到床边,柔声安抚她:“晚晚,别怕,这是林博士,是来帮你的。”他的温柔,
刺得我眼睛生疼。我走上前,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开口道:“顾先生,从现在开始,
请你不要用‘帮’或者‘治’这样的词。对于一个有严重被害妄想的病人来说,
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让她觉得我们是要‘处理’她。”顾景渊的眉头皱了起来,
显然不习惯被人这样当面指正。我没理会他的不悦,
继续以专业的口吻说道:“根据李教授给我的病历,苏**的应激反应,
主要来源于对陌生环境和人的不信任。所以,我的第一步治疗,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你。
”“针对我?”顾景渊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危险。“没错。”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毫不退缩,
“你是她目前唯一信任的人,是她的‘安全岛’。但你的过度保护和紧张,
会把你的焦虑情绪,成倍地传递给她,加重她的病情。所以,在治疗苏**之前,
我需要先教会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安全岛’,而不是一个移动的‘焦虑源’。”我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李教授,都愣住了。从来没有人,
敢用这种近乎教训的口吻和顾景渊说话。他的脸色沉了下去,周身的气压低得骇人。
“林博士,你是在质疑我?”“我是在陈述事实。”我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镜片反射的冷光,让我看起来更加不近人情,“顾先生,我的治疗方案,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如果你不能完全配合,那我只能说抱歉,请另请高明。”我这是在赌。赌他对苏晚晚的在乎,
会压过他那高高在上的自尊。空气仿佛凝固了。半晌,他紧绷的下颌线,终于松动了一分。
“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需要我怎么做?”我赢了。“很简单。
”我拿出一个录音笔,按下开关,“从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把它戴在身上。
我要记录你和苏**所有的对话,分析你的语言模式和情绪波动。另外,从明天起,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是我们的单独会谈时间,地点就在这里。记住,是单独。
”我刻意加重了“单独”两个字。我要的,就是和他独处的机会。我要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开他那坚硬的外壳,看到里面最脆弱、最不堪的内核。他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要将我看穿。我坦然地回视着他,目光平静如水。猎人与猎物的第一次交锋,我,
占了上风。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这间顶级病房的常客。我没有急着去接触苏晚晚,
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治疗”顾景渊上。
我让他一遍遍地回忆苏晚晚坠马那天的细节,回忆我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他一开始很不耐烦,觉得这些都是无用功。“这些有什么好谈的?事实很清楚,
林舒嫉妒晚晚,在马鞍上动了手脚。”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嫉妒?
”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AI,捕捉到关键词,“她嫉妒苏**什么?
嫉妒苏**可以让你抛下你们的订婚宴,冒着大雨去为她送一份生日礼物?还是嫉妒苏**,
能让你在送我的订婚戒指上,刻上她的英文名‘Evelyn’?”我的话音刚落,
顾景渊猛地抬起头,眼中迸发出骇人的厉芒。“你怎么知道?!”戒指的事,
是他心底最隐秘的秘密。除了他和我,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那枚戒指,
在我“死”后,就和他一起,沉入了海底。我看着他震惊的脸,心中涌起一阵报复的**。
但我脸上,却是一片茫然。“什么?”我故作不解地眨了眨眼,“我不知道什么。
这些……不是从你给我的,林舒**的日记里看到的吗?”“日记?”他愣住了。“是啊。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粉色的日记本,递给他,“这是警方在她‘遗物’中发现的,
李教授转交给了我,说是能帮助了解她的作案动机。”那个日记本,是我伪造的。
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我模仿着林舒当年的笔迹,含着血泪写下的。
我将我们之间那些甜蜜的、痛苦的、隐秘的细节,全都写了进去。
那些他以为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如今,却通过一个“陌生人”的口,
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顾景渊一把夺过日记本,快速地翻阅着。他的脸色,随着书页的翻动,
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难看。我看到他握着日记本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根根泛白。“顾先生,
”我恰到好处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一个女人,如果不是爱到了极致,
又怎么会恨到极致呢?也许,林舒**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嫉妒,
而是一种绝望下的……报复。”我把“报复”两个字,咬得极轻,却又像一颗钉子,
狠狠地钉进了他的心里。05对顾景渊的心理防线进行初步的松动后,
我开始正式“治疗”苏晚晚。我的方法很简单,催眠。在顾景渊的注视下,我用一支笔,
一个平缓的语调,轻易就将精神高度紧张的苏晚晚带入了深度催眠状态。“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