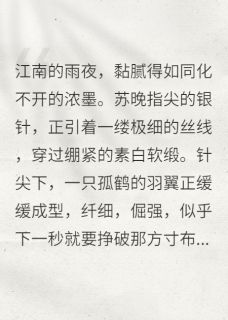江南的雨夜,黏腻得如同化不开的浓墨。苏晚指尖的银针,正引着一缕极细的丝线,
穿过绷紧的素白软缎。针尖下,一只孤鹤的羽翼正缓缓成型,纤细,倔强,
似乎下一秒就要挣破那方寸布帛,没入无垠的天际。砰!巨大的爆裂声撕裂了夜的寂静。
木屑如同黑色的雪片,裹挟着冰冷的雨水,疯狂地扑进小小的绣坊。一股蛮横至极的力量,
狠狠撞碎了那扇单薄的木门。苏晚猛地一颤。指尖的绣针,猝不及防地深深扎进食指指腹。
一点殷红,迅速在洁白的鹤羽上洇开,像一滴刺目的血泪。她甚至来不及感到疼痛。
冰冷刺骨的雨气,混杂着铁锈、皮革和某种久违的、令人窒息的沉水香,如同无形的巨浪,
瞬间淹没了这方小小的、温暖的天地。沉重的、覆着玄铁的靴底,踏着破碎的门板,
碾过她刚染好晾干的鹅黄色衣料,一步,一步,踏入屋内。靴底粘着的泥泞和门板的碎屑,
在那抹鲜嫩的鹅黄上,践踏出肮脏污浊的印记。雨水顺着他漆黑的玄甲往下淌,
砸在潮湿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嗒、嗒”声。空气骤然冻结。烛火在他身后狂乱地跳动,
将一道巨大、扭曲、如狱底魔神般的影子,铺满了整个墙壁,也沉沉地压向苏晚单薄的身影。
苏晚浑身冰凉,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凝固,又在下一瞬疯狂倒流,冲撞得耳膜嗡嗡作响。
她僵在原地,连指尖那点细微的刺痛都彻底麻木。是他。萧烬。那个她耗费七年心血,
用一场焚尽王府的大火和一句刻骨铭心的诅咒,才终于埋葬掉的噩梦。
那个名字像淬了寒冰的针,狠狠扎进她的脑海。他怎么会找到这里?
雨水顺着他线条冷硬的下颌滴落,砸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萧烬的目光,
像毒蛇冰冷的信子,缓慢地、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味,舔过苏晚煞白的脸,最终,
黏在了她指尖那点刺目的猩红上。那点血,落在他眼底,仿佛点燃了某种深不见底的疯狂。
他薄削的唇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勾起。一个毫无温度、却足以让苏晚肝胆俱裂的笑容。
“抓到你了,晚晚。”低沉沙哑的嗓音,裹挟着雨夜的湿冷,
轻易穿透了苏晚摇摇欲坠的防线。冰冷的恐惧瞬间攥紧了她的心脏,几乎让她窒息。
她猛地后退一步,脊背重重撞在身后堆满各色丝线的木架上。竹架一阵剧烈的摇晃。哗啦!
五颜六色的丝线卷轴,如同坍塌的彩虹瀑布,纷纷滚落在地,沾满了地上的泥水和碎木屑。
一片狼藉。她精心构筑了三年的、属于苏晚的平凡安稳的世界,
在这玄铁重靴踏碎门扉的一刻,彻底分崩离析。萧烬的视线,掠过她惊惶的眼,
掠过她沾血的指尖,最终,死死锁在她纤细脖颈上——一道颜色尚新的、浅浅的疤痕,
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那是逃离时留下的印记,一道她以为已经彻底摆脱的烙印。
他向前迈了一步。沉重的甲胄摩擦声,在死寂的室内格外刺耳。带着玄铁手套的冰冷手指,
毫无预兆地抬起,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猛地攫住了苏晚的下巴。
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强迫她仰起脸,
迎向他那双深不见底、翻涌着血色暗流的眼眸。“这疤,”他的指腹,
带着金属的粗糙和寒意,极其缓慢地、近乎痴迷地摩挲过那道新生的疤痕,
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稀世珍宝,却又带着一种令人骨髓发冷的占有欲,“谁弄的?
”他指间的寒意,顺着那道疤痕,蛇一样钻入她的血脉,瞬间冻结了她的四肢百骸。
苏晚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窟里艰难地挤出来:“摔…摔的…”“呵…”一声短促的冷笑,
从他喉间溢出,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和毫不掩饰的嘲弄。他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
刺穿她拙劣的谎言,钉在她眼底最深的恐惧上。“晚晚,”他俯下身,
冰冷的气息喷在她的耳廓,激起一层细密的战栗,“三年不见,你撒谎的本事,倒是退步了。
”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病态的温柔,却比刀锋更利。“不过没关系,”他的手指,
从她下巴的钳制,缓缓滑落到她脆弱的颈侧,感受着那里脉搏疯狂的跳动,
如同濒死鸟雀的挣扎,“很快…你就再也没必要,对任何人撒谎了。”话语落下的瞬间,
一股巨大的、完全无法抗衡的力道猛地传来!苏晚只觉得天旋地转,
整个人被一股野蛮的力量狠狠掼倒在地。潮湿冰冷的地面,混杂着木屑和泥水的污浊,
瞬间浸透了她的后背。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打在她的脸上、颈间,刺骨的寒意直透骨髓。
她挣扎着想要爬起。然而,视线所及,是那双覆着玄铁的重靴,踏着令人心悸的节奏,
一步步逼近。最终,停在她眼前。靴尖上冰冷的金属,几乎要贴上她的鼻尖。
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绝对的压迫。紧接着,是金属碰撞的、冰冷的、锁链拖曳的声响。
哗啦…哗啦…那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瞬间唤醒了苏晚灵魂深处最恐怖的记忆。
三年前,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那金链摩擦地面的、永无止境的回响。她瞳孔骤然收缩,
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冻结。不!不能回去!她猛地蜷缩起身体,手脚并用,
不顾一切地向后蹭去,徒劳地想要逃离那步步紧逼的玄铁重靴和越来越近的锁链声。
破碎的木屑深深扎进她撑在地上的掌心,留下细密的血痕。冰冷的泥水浸透了单薄的衣衫。
狼狈不堪。一只覆着冰冷玄铁手套的大手,带着千钧之力,猛地攫住了她纤细的脚踝!
那力道,像是钢铁的捕兽夹,瞬间锁死。骨头被挤压的痛楚尖锐地传来。“啊——!
”苏晚发出一声短促的痛呼,身体被那铁钳般的手硬生生拖拽回去。
粗糙的地面摩擦着她的肌肤,留下**辣的痛感。她被拖行着,
再次回到了那双玄铁重靴的阴影之下。哗啦!沉重的、比记忆中更加粗粝冰冷的玄铁锁链,
带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和铁锈味,精准地绕上了她的脚踝。然后,是手腕。锁链扣死的瞬间,
那熟悉的、令人绝望的沉重感,伴随着金属特有的冰冷,瞬间将她钉在了原地。
如同再次被打上了无法挣脱的烙印。萧烬单膝蹲下,沉重的甲胄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伸出带着玄铁手套的手指,动作竟带着一种诡异的轻柔,
拂开她脚踝处散落的、沾满泥水的裙裾。
露出那截被粗粝锁链禁锢的、在昏暗烛火下显得异常苍白的肌肤。他冰冷的指尖,
顺着锁链冰冷的弧度,缓缓滑过,
最终停留在她脚踝内侧一个几乎淡不可见的、旧日链环留下的浅色印记上。“还是这里好。
”他低语,声音沙哑,如同梦呓,带着一种病态的满足和怀念,“我的晚晚,
终究要回到这里。”他的指尖,带着金属的冰冷触感,在那旧日的印记上反复摩挲。
动作轻柔得近乎爱抚,却让苏晚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恐惧和恶心交织着汹涌而上。
她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浓重的血腥味,才勉强压下喉间的尖叫。
身体却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带动着沉重的锁链,发出细碎而绝望的“哗啦”声。
这声响,似乎取悦了他。萧烬低低地笑了起来,胸腔震动,笑声在空旷潮湿的绣坊里回荡,
阴森诡异。他抬起眼,那双深不见底、翻涌着血色暗流的眸子,
牢牢锁住她因恐惧而失焦的瞳孔。“晚晚,”他轻轻唤着,语气温柔得令人心胆俱裂,
“你说,这次,我该锁你哪里好?”他的目光,如同带着倒刺的钩子,
缓慢地、极具侵略性地扫过她颤抖的身体。从被锁链磨红的脚踝,
到被雨水打湿而紧贴肌肤显出脆弱线条的腰肢,再到剧烈起伏、如同受惊小鹿的胸口。最终,
停驻在她纤细脆弱的脖颈上。那道浅浅的疤痕,在摇曳的烛光下,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这里?”他冰冷的指尖,带着玄铁的坚硬触感,轻轻点在那道疤痕上,激得苏晚猛地一颤,
几乎窒息,“用最细的金链子,嵌上南海的珠子…衬你。”他的指尖继续向下,
滑过她剧烈起伏的锁骨,如同在丈量一件即将被永久珍藏的器物。“还是…这里?
”指尖点在她的心口处,感受着她心脏在肋骨下疯狂擂动,“锁住这里,晚晚的心,
是不是就再也不会乱跑了?”那冰冷的触感,透过湿透的薄衫,直刺入她的心脏。
苏晚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牙齿磕碰的声音清晰可闻。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
瞬间淹没了头顶。不!她不要再做那个被锁在暗室里,
只能仰他鼻息、连呼吸都需他施舍的玩物!绝不!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骤然劈下的闪电,
带着同归于尽的决绝,狠狠攫住了她!簪子!她发髻上,那支沉甸甸的银簪!
那里面…藏着东西。她用了整整三年,才一点点收集齐,淬炼成膏,
小心翼翼封存在银簪中空的芯管里。那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条路。当所有的路都被堵死,
当绝望彻底降临…至少,她可以选择如何结束这炼狱般的折磨!带走他!或者,被他撕碎!
苏晚猛地屏住呼吸,强行压下几乎冲破喉咙的恐惧战栗。被锁链束缚的右手,
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僵硬,一点点向上抬起。动作细微得如同濒死前的抽搐。
指尖,颤抖着,带着冰凉的汗意,一点点,艰难地,探向自己脑后松散的发髻。
指尖终于触碰到了一抹冰冷坚硬的银质。是簪尾!她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死死地、小心翼翼地捏住了那截冰凉的簪尾。只要拔下来!
只要狠狠刺下去!刺向他毫无防备的颈侧!刺向那跳动着的、滚烫的脉搏!或者…刺向自己!
带着他一起,坠入永恒的黑暗!这疯狂的念头,如同燎原的野火,
瞬间烧尽了她最后一丝恐惧,只剩下玉石俱焚的决绝!她的指尖猛地发力,
就要将那淬毒的银簪狠狠拔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噗通!一声沉闷的巨响,
毫无预兆地在她身前炸开!冰冷的水花和泥点,猛地溅了她一脸!苏晚的动作,
如同被无形的冰锥瞬间冻结。拔簪的指尖,僵在半空,微微颤抖。她惊愕地睁大了双眼。
眼前,那个如魔神般恐怖的男人,那个刚刚还掌控着她生死的萧烬,
竟然…直挺挺地、以一种近乎卑微的姿态,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她面前!
跪在这冰冷、泥泞、满是木屑污秽的地上!沉重的玄甲砸在地面,发出令人心悸的闷响。
膝盖陷入泥泞之中。这突如其来的、完全违背常理的举动,像一道狂暴的雷霆,
狠狠劈在苏晚混乱的脑海。巨大的冲击让她思维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他…在做什么?
疯了?他一定是彻底疯了!萧烬低着头,湿漉漉的黑发垂落,遮住了他大半张脸,
只露出线条紧绷、毫无血色的下颌。雨水顺着他高挺的鼻梁滑落,滴在冰冷的玄甲上。
他伸出手。那双沾满泥污、戴着冰冷玄铁手套的手,
此刻却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小心翼翼的颤抖。他缓缓地、极其轻柔地,
捧起了苏晚沾满泥水、被雨水浸得冰凉的右脚。那只脚,纤瘦,苍白,
脚踝处被粗粝的玄铁锁链磨出了刺目的红痕。那只刚刚被他用锁链粗暴禁锢的脚。此刻,
却被他如同捧着易碎的稀世珍宝,小心翼翼地托在掌心。冰冷的玄铁触感,
混合着他掌心透过手套传来的、一丝诡异的灼热温度,让苏晚浑身汗毛倒竖,胃里一阵翻搅。
她下意识地想缩回脚,却被他的力道牢牢固定,动弹不得。萧烬低着头,
专注地看着掌中那只泥泞不堪的绣鞋。雨水冲刷着鞋面,
露出底下褪色的、沾满污泥的刺绣——一只残破的、几乎看不出原貌的孤鹤。
他伸出另一只手,覆着玄铁手套的指尖,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温柔和专注,
轻轻地、一点一点,拂去鞋面上冰冷的泥浆。动作轻柔得不可思议,
如同在擦拭一件失而复得的圣物。绣鞋湿透了,冰冷刺骨。他掌心那点透过玄铁传来的热度,
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滚烫,带着一种不正常的灼烧感,烫得苏晚脚心发麻。
一种比锁链加身更甚的恐惧,毒蛇般缠绕上她的心脏。他到底想做什么?这反常的举动,
比直接的暴虐更让她毛骨悚然!终于,他拂开了大部分污泥,
露出了那只残破孤鹤模糊的轮廓。他停下了动作。捧着那只冰冷湿透的绣鞋,
如同捧着某种祭品。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只有屋外哗哗的雨声,
屋内烛火噼啪的爆响,以及苏晚自己疯狂擂动的心跳,在死寂中无限放大。然后,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湿透的黑发黏在他苍白的额角,
雨水顺着他的鬓角蜿蜒而下。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此刻清晰地映入苏晚惊恐的瞳孔。
没有暴怒,没有疯狂。只有一片死水般的空洞。空洞之下,
却燃烧着一种令人灵魂颤栗的、偏执到极致的幽火。那眼神,不再是看一个人。
而是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绝不容许再丢失的…所有物。他薄唇微启,声音低沉沙哑,
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非人的平静,
却蕴含着比刀锋更凌厉的疯狂:“晚晚…”他唤她的名字,语气温柔得诡异。
“你逃一次…”他捧着她脚的手,不易察觉地收紧,冰冷的玄铁几乎要嵌入她的肌肤。
“我就杀一百人…”空洞死寂的眼底,骤然掠过一丝猩红暴戾的寒芒,如同地狱之门洞开!
“这次…”他微微歪了歪头,沾着雨水的唇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勾起一个弧度。那笑容,
冰冷,扭曲,带着一种灭世般的疯狂。清晰地,一字一句,如同诅咒,
砸进苏晚的耳膜:“我屠了整座城,可好?”轰——!苏晚的脑子像是被一柄巨锤狠狠砸中!
眼前瞬间一片漆黑,耳边只剩下尖锐的、足以撕裂灵魂的嗡鸣!屠城?整座城?
那些清晨递给她新鲜瓜果的李婶,那些围着她绣架叽叽喳喳讨教针线的邻家姑娘,
那些傍晚在桥头下棋、总爱笑呵呵招呼她的老人……那些她用了三年时间,
小心翼翼融入、试图在其中汲取一丝人间暖意的面孔……一张张,鲜活地、带着笑意地,
在她因极度恐惧而混乱的脑海里飞速闪过。紧接着,被一片无边无际的、粘稠猩红的血海,
瞬间吞噬!窒息!冰冷的绝望如同万载玄冰,瞬间冻结了她的血液,她的骨髓,她的灵魂!
她张着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只有空气被强行挤压出的、破碎的“嗬嗬”声。
身体抖得如同狂风中的残叶,带动着沉重的锁链发出绝望的哀鸣。
眼前那张苍白、俊美、此刻却如同地狱修罗般的脸,在摇曳的烛光中扭曲变形。
他唇角那抹疯狂的笑意,如同烙印,深深烙进她濒临崩溃的眼底。“不…”一个破碎的音节,
终于从她痉挛的喉咙深处挤了出来,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和濒死的哀鸣。微弱得如同蚊蚋。
“不?”萧烬眉梢微挑,空洞的眼底,那点猩红骤然放大,如同滴入清水的墨汁,
迅速晕染开一片妖异的血色!“晚晚说不?”他低低地笑了起来,胸腔震动,
笑声在空旷的绣坊里回荡,阴森得如同夜枭啼鸣。他猛地凑近!冰冷的呼吸,
带着沉水香和浓重的血腥气,狠狠喷在苏晚惨白如纸的脸上。两人鼻尖几乎相抵。
他深不见底的瞳孔里,清晰地映出她因极致恐惧而扭曲的面容。“晚了。
”他轻轻吐出两个字,如同宣判。下一刻,他捧着苏晚右脚的手,猛地向上抬起!
冰冷的玄铁手套边缘,狠狠擦过她脚踝被锁链磨破的肌肤,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苏晚痛得闷哼一声,身体下意识地后缩。然而,预想中更可怕的折磨并未降临。
萧烬只是将她的脚抬到了一个极其屈辱的高度。然后,他低下头。冰冷的、带着雨水的唇,
带着一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占有姿态,重重地、烙印般吻在了她冰冷肮脏的绣鞋鞋尖!
吻在那只残破的、沾满泥污的孤鹤图案上!这个动作,带着极致的亵渎与极致的占有,
如同滚烫的烙铁,狠狠烫在苏晚早已崩断的神经上!“呃啊——!
”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终于冲破了她被恐惧扼住的喉咙!
她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逆流,冲上头顶!眼前骤然一片血红!所有的理智,
所有的算计,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被这疯狂的、灭顶的屈辱和绝望彻底碾碎!
只剩下最原始、最狂暴的本能!杀了他!或者…杀了我自己!僵在半空的右手,
积蓄了所有残存的力量和滔天的恨意,猛地发力!嗤!那支沉甸甸的、淬了剧毒的银簪,
终于被她从发髻中狠狠拔出!冰冷的簪身,带着她指尖的汗水和最后一丝体温。
簪尖在昏暗的光线下,闪过一点幽蓝的、不祥的寒芒!没有丝毫犹豫!
苏晚眼中燃烧着同归于尽的疯狂火焰,手腕用尽全身力气,带动着沉重的锁链,
将簪尖对准萧烬毫无防备、低垂着的颈侧!狠狠刺下!去死!带着我的恨!带着这座城的怨!
一起下地狱吧!簪尖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破空声,直刺目标!
一点幽蓝即将触碰到他苍白的皮肤、感受到那皮下温热血液搏动的瞬间——跪在地上的萧烬,
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又或者,他早已洞悉了她所有的挣扎与绝望。他猛地抬起头!
那双翻涌着无边血色与疯狂的眼眸,直直地撞入苏晚因恨意而猩红的瞳孔!没有惊愕。
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狂喜的、病态的期待!他甚至…主动地、微微侧了一下脖颈!
将那段最致命、跳动着大动脉的脆弱部位,更清晰地暴露在苏晚染血的簪尖之下!同时,
他那双覆着玄铁手套的手,依旧死死地、如同铁钳般禁锢着她的右脚脚踝,
不让她有丝毫挣脱的可能!簪尖,带着苏晚全身的力量和玉石俱焚的决绝,狠狠刺入!嗤!
一声轻微的、皮肉被刺破的闷响。预想中鲜血喷溅的场景并未出现。簪尖,
仅仅刺入了他颈侧皮肤不到半寸!一股难以想象的、磐石般的阻力,从簪身传来!
仿佛刺中的不是血肉,而是千锤百炼的精钢!苏晚惊愕地瞪大双眼。这…怎么可能?!
她用了全力!簪尖淬毒,见血封喉!萧烬的身体,只是极其轻微地震颤了一下。
颈侧被刺破的皮肤,渗出一点细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血珠。顺着苍白的皮肤缓缓滑落。
他那双翻涌着血色的眼眸,却骤然亮起!如同地狱业火被点燃,
爆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极致愉悦的光芒!他喉间发出一声满足的、近乎叹息的喟叹。
“呵…”仿佛等待已久的猎物,终于露出了它最锋利的爪牙。而他,享受这反抗的刺痛。
下一秒!他禁锢着苏晚脚踝的手猛地一松!以快得超越视觉的速度,那只覆着玄铁的手掌,
如同捕食的毒蛇,闪电般向上探出!精准无比地,一把攫住了苏晚握着毒簪的右手手腕!
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响起!剧痛瞬间席卷了苏晚的右臂!“呃——!
”她痛得眼前发黑,几乎晕厥。手腕的骨头,像是被冰冷的铁钳瞬间捏碎!五指无力地张开。
那支淬着幽蓝寒芒的毒簪,脱手而出。叮当!一声脆响,银簪跌落在地,滚入泥泞之中,
沾染上污秽的泥浆,那点幽蓝的光芒瞬间黯淡,如同熄灭的毒火。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
绝望的黑暗,如同粘稠的墨汁,瞬间淹没了苏晚所有的意识。
“我的晚晚…”萧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
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兴奋和灼热的喘息,“果然…还是这么烈!”他捏着她碎裂手腕的手,
力道大得要将她的骨头碾成齑粉。剧痛让苏晚浑身痉挛,冷汗瞬间浸透了冰冷的衣衫。
他猛地用力,将她整个人粗暴地从泥泞地上拖拽起来!如同拖拽一件没有生命的破布娃娃。
苏晚痛得蜷缩,沉重的锁链哗啦作响,拖曳在泥水里。萧烬另一只手臂如同铁箍般,
狠狠勒住她纤细的腰肢,将她死死禁锢在胸前。冰冷坚硬的玄甲硌得她生疼。
浓重的沉水香混合着他身上传来的、如同烈焰焚烧后的焦糊气息,
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将她紧紧包裹,令人窒息。他低下头,灼热滚烫的呼吸,
带着一种毁灭性的疯狂,狠狠喷在她的耳廓。“这样才好…”他低语,
牙齿轻轻啃噬着她冰凉的耳垂,留下细微的刺痛和湿热的触感,“这样烈的晚晚…烧起来,
才最耀眼…”他猛地收紧手臂,勒得苏晚几乎断气。然后,他拖抱着她,
如同拖着一件战利品,转身,大步走向绣坊那破碎的、如同巨兽獠牙般洞开的门洞。门外,
是无边无际的、冰冷的、吞噬一切的雨夜。狂风卷着冰冷的雨水,狠狠抽打在苏晚的脸上。
她最后一丝力气也耗尽了,如同断线的木偶,任由他拖拽着,踏入那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沉重的玄铁锁链,在泥泞的地面上拖曳,发出单调而绝望的“哗啦…哗啦…”声。
如同通往地狱的丧钟。萧烬的脚步,沉重而稳定,踏在青石板路上,溅起浑浊的水花。
他抱着她,或者说,拖着她,穿过死寂无人的长街。冰冷的雨水无情地冲刷着苏晚的脸颊,
试图唤醒她麻木的神经,却只带来更深的寒意。不知走了多久。
久到苏晚以为自己会在冰冷的雨水中彻底冻僵、死去。前方,浓稠的黑暗中,
突兀地出现了一团模糊的、橙黄色的光晕。像一只悬浮在黑暗里的巨兽独眼。随着靠近,
那光晕渐渐清晰。是两盏巨大的、在风雨中剧烈摇晃的气死风灯。昏黄的光,
艰难地撕开雨幕,照亮了灯下沉默矗立的、如同蛰伏巨兽般的——镇国将军府邸。
那熟悉的、象征着权势与禁锢的朱红大门,此刻洞开着。如同一张择人而噬的血盆大口。
门内,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比外面的雨夜,更黑,更冷。
门楣上悬挂的、象征着他赫赫战功的玄铁牌匾,在风雨中沉默着,
透着一股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威压。苏晚的心,彻底沉入了无底深渊。又回到了这里。
这个她曾用生命和一场焚天大火逃离的囚笼。萧烬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他抱着她,或者说,
拖着她冰冷的身体,径直踏过了那高高的、象征着不可逾越权势的门槛。沉重的脚步声,
在空旷死寂的府邸前院回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苏晚早已碎裂的心脏上。门内,
并非空无一人。两排身着漆黑甲胄、如同石雕般沉默肃立的亲卫,
无声地分列在通往深处的甬道两旁。他们脸上覆着冰冷的面甲,
只露出一双双毫无感情、如同深渊的眼睛。雨水顺着他们冰冷的甲胄往下淌。
当萧烬抱着苏晚经过时,所有亲卫如同被无形的线操控,动作整齐划一地单膝跪地。
甲胄摩擦,发出沉闷而肃杀的金属撞击声。头颅深深低下。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丝声响。
只有绝对的服从,和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仿佛他们跪拜的,不是一个活人,
而是一尊来自地狱的魔神。这诡异的静默,比任何喧嚣都更令人恐惧。
苏晚被这森然的气氛压迫得几乎无法呼吸。她闭上眼,不愿再看这如同墓穴般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