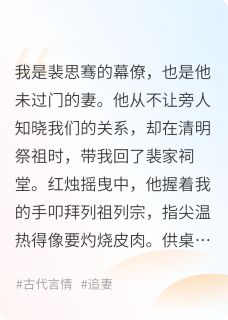我是裴思骞的幕僚,也是他未过门的妻。他从不让旁人知晓我们的关系,却在清明祭祖时,
带我回了裴家祠堂。红烛摇曳中,他握着我的手叩拜列祖列宗,指尖温热得像要灼烧皮肉。
供桌上的香炉泛着幽光,他低声说:“温姝,待我平定北境,便以十里红妆迎你。
”那时我以为,这烛火、这誓言,便是相守的凭证。直到那夜,我撞见他攥着苏婉的手腕,
红着眼问:“婉婉,你当真要嫁人?你若摇头,我这就去退了温家的亲事。
”01军营里除了他的副将秦风,没人知道我与裴思骞的渊源。我爹原是边关守将,
三年前为护裴思骞,硬生生替他挡了敌军的冷箭。那支淬了毒的箭穿透他的护心镜时,
他还回头对裴思骞吼:“护住粮草!别管我!”他战死沙场的消息传回时,
家里的梁上还挂着他刚给我做的秋千。乱兵抄家那日,我躲在柴房。
就在我被拖拽着往外走时,裴思骞带着亲兵赶到了。他身披染血的银甲,
玄色披风上还凝着未干的血渍,一脚踹开抓着我的乱兵,伸手将我从泥地里捞起来。
他的手掌宽厚有力,攥着我的手腕时,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颤抖。后来才知道,
那是因为我爹临终前攥着他的战袍,断断续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闺女…就托付给你了”。
“别怕。”他低头看我,眼里翻涌着我读不懂的情绪,“以后有我在。”后来我剪去长发,
换上皂色长衫,以“温舒”之名混入军营。没人知晓这清瘦的“少年郎”原是女儿身,
更没人料到,我能在半年内从小小的杂役,坐到参军之位。我爹生前总爱摸着我的头笑,
说:“姝儿这脑子,若投个男儿胎,定是块做幕僚的好料。不说决胜千里,
至少能在军帐里替主帅分三分忧。”他去世后,那些被我翻得起毛边的兵书成了唯一念想,
夜里就着月光研读时,总能想起他捏着我的小手,在图上画箭头的模样。02暮春时节,
秦风递来一张字条:“先生,将军明日归来。”我回了个“嗯”字,指尖却泛了白。
裴家老太太去年冬日出了场大病,夜里咳得喘不上气。她总来信念叨着要亲眼见孙媳妇,
裴思骞便在去年清明祭祖时节带着我回了裴府,在祠堂许下十里红妆的诺言,
当时的我满心只有甜蜜。我翻出箱底那件月白长衫,在营外候了一个时辰,雾气渐浓,
才见裴思骞的马队归来。他翻身下马时,玄色披风扫过地上的枯草,
却没像往常那样先问军务,反而转身朝身后的马车轻轻一扬鞭。车帘被一只纤细的手掀开,
月白裙角先落下来,苏婉踩着他伸过来的掌心下车,鬓边银钗上的流苏晃了晃,
沾了点边关的沙。“阿骞,关外的风果然比江南烈。”她仰头笑时,
指尖轻轻搭在裴思骞臂弯上,像是在撒娇。我站在三步外,
看着裴思骞屈指替她掸去肩头的尘,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早说过让你开春再来,
偏不听。”话里带着嗔怪,眼底却漾着我从未见过的软意。我曾在裴家书房见过画像,
正是苏家那位**,他已经去世哥哥的未婚妻,也是他的远房表妹。“阿骞,
这位就是你信中常说的温先生?”苏婉的声音软得像江南春水,目光落在我身上时,
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打量。她腕间的檀木珠串随着动作轻响,我的手猛地收紧,
我本不该多想的。但三个月前替他整理书房暗格时,曾见过同款檀木锦盒,
盒里垫着红色的绒布,当时只当是他孝顺,给老祖母备的礼,许是事务繁忙耽搁了,
便没往深处想。裴思骞淡淡颔首:“温姝,这是苏婉,特意从江南来看我。
”他没提她是已故兄长的未婚妻,只淡淡补了句,“在营中住些时日,你多照看。
”我们相识五年,他从未对我如此,此刻却对另一个女子体贴入微。苏婉仰头笑时,
鬓边的珍珠耳坠晃了晃,恰好落在裴思骞手背上,他竟没有像往常般避开。
去年我替他研墨时,衣袖不慎扫过他的手背,他当即皱了眉,说“男女授受不亲”。
03军帐内的木桌摆得简单,粗陶碗里盛着炖羊肉,膻气混着炭火味飘在帐内。
我刚用匕首把烤得焦脆的羊排切成小块,就见裴思骞掀帘进来,身后跟着苏婉。
苏婉捏着帕子捂了捂鼻子,
眉尖微蹙:“这味道……”裴思骞当即把自己面前那碗没动过的菌菇汤推过去,
声音放得柔:“嫌膻就喝这个,伙夫新炖的,放了江南的笋干。”又转头对亲兵道,
“再去弄碟蜜饯来,解解腻。”我握着匕首的手顿了顿。这羊肉菌菇汤是我让人特意炖的,
他前几日风寒未愈,军医说喝这个养肺。帐内只剩木筷碰碗的轻响,苏婉用银匙舀着汤,
忽然“呀”了一声:“莲子怎么带芯?有点苦呢。”裴思骞二话不说伸过筷子,
把她碗里带芯的莲子全夹到自己碟中,又从另一碗里挑了几颗去芯的搁进去,
动作熟稔得像做过千百遍:“早让伙夫挑干净,还是毛躁。”苏婉抿唇笑,
眼角余光扫过我时,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得意。我低头喝着碗里的糙米粥,喉间忽然发紧。
去年中秋在军帐,我蹲在炭火旁替他剥了半夜去芯莲子,指尖被莲心染得发苦,
剥好的一碗全码得整整齐齐。他过来时只瞥了一眼,皱眉道:“太甜,腻得慌。
”如今他亲手挑拣的莲子,却连苏婉随口一句“苦”,都成了要紧事。“将军,
”我清了清嗓子,把军情简报往前推了推,“昨日哨探回报,
西侧峡谷似有敌军异动……”话没说完,就被苏婉的笑声打断。她指着帐外掠过的孤雁,
对裴思骞道:“阿骞你看,那雁飞得好急,是不是也想往江南去?
”裴思骞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竟顺着她的话答:“开春了,该北归了。
”完全没看我推过去的简报。炭火噼啪响着,我看着碗里渐渐凉透的粥,忽然觉得,
这军营的羊肉膻气,竟比不过江南来的一缕风,能吹软他眼底的冰。04深夜我起身寻水,
却在回廊撞见裴思骞。他将苏婉困在廊柱间,月光落在他脸上,映出从未有过的慌乱。
“婉婉,三年前你不告而别,如今回来为何要嫁旁人?”他的声音发颤,
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知道你怨我当年未能及时回来,致使爹娘将你错许给大哥,
可我那时正逢战事……”“阿骞,逝者已矣。”苏婉的声音带着哭腔,肩头微微耸动,
“你哥哥是因我而死,我怎能再占了你?温姑娘是个好女子,你该好好待她。
”我攥着廊柱的手骤然收紧,掌心被冻得生疼。原来他哥哥裴惊瑜的死,竟与苏婉有关。
三年前他的大哥裴思瑜在江南遇刺,裴思骞疯了似的赶去时,只见到灵堂里的白幡。
那时我刚入营,夜夜见他对着兄长的牌位枯坐,案上总摆着两碗酒,一碗倾在地上,
一碗他自己喝掉,却从不知背后还有这层纠葛。裴思骞忽然笑了,
笑得眼眶泛红:“可我心里只有你,当年若不是她父亲以救命之恩相挟,我怎会答应娶温姝?
”他抬手想去碰苏婉的脸颊,却在半空中停住,“她父亲是我军袍兄弟,我娶她,
不过是为了报恩。”苏婉的啜泣声越来越大,裴思骞终于忍不住将她揽进怀里:“别嫁旁人,
好不好?我去退亲,现在就去……”我转身回房时,才发现自己赤着脚站在青石板上。
寒气从脚底直窜心口,比去年在关外饮的雪水还要冷。去年在战场,我替他挡了一箭,
他抱着我狂奔时,满眼焦灼与疼惜。军医说我伤了肺腑,需静养百日,
他却第二日夜里接到一封来自江南的密信,当即翻身上马,连句交代都没有。
此时想来原来那时他急着救我,不过是怕老太太怪罪,怕对不起我爹的在天之灵。
妆奁里的木簪刻着并蒂莲,是他去年在军帐里刻的。那时我以为是情动,如今才知,
不过是他一时兴起的温柔。烛火明明灭灭中,他说:“等战事平息,我便娶你。
”如今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就像他教我射箭时,会亲自调整我的姿势,指尖触到我的手腕,
却在教会我之后,再也不曾碰过。03次日巡视后回营,刚卸下行囊,就见裴思骞站在帐外。
他眼下有青黑,像是彻夜未眠,玄色常服的领口歪着,少了往日的规整。
许是察觉到我的疏离,他语气生硬,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命令:“表妹身体差,
我只是暂时多照拂。”我低头整理兵书:“将军多虑了,属下明白分寸。
”案上的《孙子兵法》缺了页,是去年他教我排兵时,被箭簇划破的。
他似乎被我的疏离刺痛,伸手攥住我的手腕:“温姝,我们相识五年…”“将军,
敌军异动的军报。”秦风及时闯入,将一份密函递过来。他眼神在我们之间游移,
最终落在我发红的手腕上,欲言又止。秦风是少数知道我们关系的人,去年我养伤时,
是他偷偷给我送来了裴思骞的给的伤药,说:“将军嘴硬,心里还是记挂你的。
”裴思骞的手猛地松开,接过密函时,指节泛白。我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忽然想起昨夜苏婉鬓边的珍珠耳坠,那款式,与我妆奁里那对他送的,竟是一模一样。
那对耳坠是他去年生辰送我的,说是“犒劳幕僚的赏赐”,我一直舍不得戴,
想来不过是他给苏婉挑剩的款式。04这天军议上,苏婉突然出现,说有破敌良策。
她提出诱敌深入峡谷,再用火攻。裴思骞却当众赞道:“婉婉果然聪慧。”我站在帐下,
冷眼看着他采纳那荒唐的计策,他竟忘了峡谷两侧是砂岩,火势根本无法蔓延。
看着他将我熬夜绘制的布防图扔在一旁。图上标注的敌军粮草所在地,
是我派了三名死士才探来的机密,他们中最年轻的那个,才刚满十六岁,
出发前还笑着说“等打赢了,就娶邻村的阿翠”。“温先生可有异议?
”裴思骞的目光扫过来,带着几分审视。帐内的将领都看向我,
他们知道我是裴思骞最信任的幕僚,去年奇袭敌军粮仓的计策,便是出自我手。
我望着他眼底一闪而过的不悦,忽然笑了:“将军英明。”散帐时,秦风低声道:“先生,
将军这是昏了头。”他递来个油纸包,里面是我爱吃的糖糕,“这是让厨房做的,
特意给你送来的。知道你在营里苦,嘴馋这个。”我望着裴思骞陪苏婉离去的背影,
轻轻摇头:“随他吧。”七日后,捷报传来——敌军果然入了峡谷,
却因我军提前布下的绊马索乱了阵脚,最终溃败而逃。裴思骞在庆功宴上喝了许多酒,
被众将簇拥着,脸上却没什么笑意。他走到我面前,将一杯酒塞进我手里:“为何不提醒我?
”“将军自有考量。”我仰头饮尽,烈酒灼烧着喉咙,“属下只是幕僚,不敢冒犯。
”他盯着我看了许久,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往外走。帐外寒风呼啸,他将我按在廊柱上,
气息带着酒意:“温姝,你是不是在怪我?”“不敢。”我别过脸,避开他的目光。
“看着我!”他捏着我的下巴强迫我转头,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以为我不知道布防图是你换的?那些绊马索,是你连夜让人加的?”我心尖一颤,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你就这么想证明自己?”他的声音冷下来,“证明你比婉婉强?
”这句话像冰锥刺进心口。我猛地推开他:“裴思骞,我只是不想看到将士们白白送死!
”那个十六岁的少年,终究没能回来,他的尸体被敌军挂在城楼上,我派人去收尸时,
只找回了半块染血的玉佩。他踉跄着后退,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直呼我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