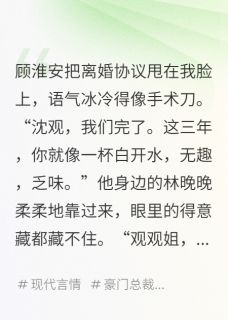顾淮安把离婚协议甩在我脸上,语气冰冷得像手术刀。“沈观,我们完了。这三年,
你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趣,乏味。”他身边的林晚晚柔柔地靠过来,眼里的得意藏都藏不住。
“观观姐,淮安只是累了,你别怪他。”我看着他们,没哭没闹,平静地拿起笔,签了字。
“净身出户,我只有一个要求,”我看着他,“把你名下,
城郊那座没人要的破山头过户给我。”顾淮安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轻蔑地签了**协议。
“给你,让你去山上当野人,正好。”他以为我会就此潦倒,哭着回来求他。他不知道,
那座破山头上,有我沈家断了三百年的道统。而我,是它唯一,也是最后一位继承人。今天,
我回家了。1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天是灰的,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顾淮安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将他身边的林晚晚护得滴水不漏。他甚至没回头看我一眼,
径直拉开车门,将林晚晚塞了进去,那辆熟悉的迈巴赫便绝尘而去,溅了我一身泥水。
我站在雨里,看着手里那份新鲜出炉的离婚证,以及另一份薄薄的山地**协议,
忽然就笑了。三年。我嫁给顾淮安三年,扮演了三年温顺、贤良、无趣的“顾太太”。
我收敛了所有锋芒,藏起了所有与他眼中“正常”相悖的习惯,只为了让他安心。我以为,
爱一个人,就是变成他喜欢的样子。结果,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杯白开水,
他却转头爱上了林晚晚那杯烈酒。他说我无趣,说我乏味,说我每天除了插花就是烹茶,
像个提前进入晚年的老太太。他不知道,我插花是为了理顺家中杂乱的气场,
我烹茶是为了安抚他身上从商场带回来的戾气。他更不知道,我之所以每天待在家里,
是因为他八字太轻,命格带煞,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我守着他,替他挡了三年的灾。
如今,他为了林晚晚,亲手把我这个“护身符”给扔了。也好。这三年的豪门阔太生活,
快把我骨子里的野性都磨平了。我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师傅,去西郊的长青山。
”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和不解:“姑娘,那地方荒山野岭的,
什么都没有啊。你这……是失恋了想不开?”我扯了扯嘴角:“不,是回家。
”2车子在山脚下停住。再往上,就是崎岖的土路,车开不进去了。我付了车费,
背上我那个只装了几件换洗衣物和全部积蓄的背包,一步步朝山上走去。
雨后的山路泥泞湿滑,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新气息。越往上走,
我越觉得四肢百骸都舒展开来,像是被囚禁了太久的鱼,终于回到了水里。走了近一个小时,
一座破败得几乎只剩下骨架的道观,出现在我眼前。门楣上方的牌匾早已腐朽,
只能依稀辨认出“三清观”三个字。朱红色的院墙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
院子里杂草丛生,比人还高。这里,就是我沈家的根。
也是顾淮安眼里一文不值的“破山头”。我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径直走向正殿。
殿内的三清神像蒙着厚厚的灰尘,神情却依旧悲悯。我放下背包,
从包里拿出三根我亲手做的檀香,点燃,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炉里。
“沈家第三十八代不孝子孙沈观,回来了。”我跪在蒲团上,对着神像,郑重地磕了三个头。
就在额头触地的瞬间,一股温润却强大的力量,从冰冷的地面,顺着我的额头,
猛地灌入我的四肢百骸!尘封在血脉深处的记忆和传承,如同决堤的洪水,
轰然涌入我的脑海。
《洞玄符经》、《太上感应篇》、《青囊相术》……那些我从小当故事书看的祖传典籍,
此刻不再是晦涩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灵魂里。原来,
我之前为顾淮安做的那些,不过是凭着血脉里的一点本能。而现在,我才是真正觉醒了。
我睁开眼,眼前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空气中,漂浮着各色驳杂的“气”,整个道观上方,
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却无比纯净的金色气运。这是祖师爷留下的庇佑。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胸中三年的郁结,一扫而空。顾淮安,谢谢你。谢谢你放我自由。从今天起,天高海阔,
我沈观,只为自己而活。3山上的生活很清苦。道观里没水没电,我只能每天下山去挑水。
吃的也只有背包里带来的几包方便面。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苦。我花了两天时间,
把道观的偏殿打扫出了一间能住人的屋子。又花了三天,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干净。
当我看着焕然一新的小院,虽然依旧破败,却充满了生机,心中满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是我的地方,是我可以随心所欲,做回自己的地方。钱很快就花完了。我必须想办法挣钱。
修复道观,需要一大笔钱。我总不能真的餐风露宿,靠吸收天地灵气过活。思来想去,
我把主意打到了时下最火的直播上。我用最后一点钱,
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智能手机和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又办了张流量卡。
我的直播间名字很简单,就叫“三清观观主”。开播第一天,我没露脸,
只是把镜头对着我刚刚清理出来的院子,然后默默地开始扎扫帚。
直播间里稀稀拉拉进来了几个人。【主播这是在哪?感觉好破啊。】【行为艺术?
直播扎扫帚?】【三清观?是道观吗?**姐是道士?求露脸!】我没理会弹幕,
专心做着手里的活。我扎的扫帚不是普通的扫帚,扫的是地,驱的是邪。
每一根竹枝的捆绑顺序和松紧,都有讲究。
一个网名叫“风一样的男子”的用户飘过一条弹幕:【主播,我最近天天晚上做噩梦,
梦到被人追,感觉快精神衰弱了,怎么办啊?】我手上的动作一顿,抬眼看了一下屏幕。
透过这行字,我仿佛能看到一个脸色发白,眼下乌青,精神萎靡的年轻人。他的头顶,
萦绕着一团若有若无的黑气。我拿起旁边的一支毛笔,蘸了点朱砂混着清水的“墨”,
在一张随手捡来的黄纸上,迅速画了一道“安神符”。然后,我把符纸对着镜头,
淡淡地开口,这是我直播以来的第一句话:“网名叫风一样的男子,你家卧室的床头,
是不是挂了一副抽象画,主体是黑红两色?”直播间里沉默了几秒,
然后“风一样的男子”的弹幕炸了。【**!主播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女朋友送的,
说是新锐艺术家的作品!】我把镜头对回自己画的符,声音依旧平淡:“那不是艺术,
那是情绪的垃圾桶。画家在画它的时候,充满了暴戾和怨气,你日日对着它睡,
不被影响才怪。”“把画烧了。然后,把我这张符的截图打印出来,放在枕头底下,
睡个好觉吧。”说完,我不再理他,继续扎我的扫帚。直播间里的其他人却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这么玄乎?】【算命的都跑到直播平台来了?骗子吧!】【我截图了,
坐等后续。@风一样的男子,兄弟,记得回来反馈啊!】“风一样的男子”没再说话,
估计是去照我说的做了。我扎好扫帚,天也差不多黑了。我对付了一包泡面,
对着镜头说了声“下播”,就关了直播。这一天,我的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是17人。
4第二天我再开播时,直播间里的人数明显多了起来,有五六十人,
大部分都是昨天来看热闹的。大家都在等“风一样的男子”的后续。我依旧没露脸,
镜头对着院子里的一块空地,我正在用最古老的步法丈量土地,规划着要开垦一块菜地。
弹幕里全是催更的。【主播,那个做噩梦的兄弟呢?是不是骗局被拆穿,不敢来了?
】【我就说嘛,网络大师,十个有九个是骗子。】就在这时,一个金色的“火箭”特效,
在小小的直播间里炸开。对于我这个粉丝数只有两位数的直播间来说,这简直是惊天动地。
紧接着,“风一样的男子”的弹幕飘了出来,字体都带着激动的颤抖:【大师!我来了!
大师你简直是神仙!我昨天回去就把那画给烧了,你都不知道,烧起来的时候,
那烟都是黑的,还带着一股腥臭味!然后我把你画的符打印出来放枕头下,
一觉睡到今天早上,连个梦都没做!我好几年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又一个火箭升空。
【大师,这点心意不成敬意!以后你就是我亲姐!不,你是我亲大师!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整个直播间瞬间沸腾。【**!真的假的?这么灵?】【我昨天也在场,我作证,
主播从头到尾就问了一句话,就全说中了!】【大师!收下我的膝盖!求大师也给我算算!
】【大师,我最近打麻将手气好差,是不是也中邪了?】看着满屏的“大师”,我有点无奈。
我只是想挣点修道观的钱,没想当什么大师。我停下脚步,对着镜头说:“第一,
我不是大师,是观主。第二,随缘指点,不特意算命。第三,打麻将手气差是你技术问题,
跟我没关系。”我的话很直接,甚至有点不客气。但直播间里的观众反而更兴奋了。
【哈哈哈,主播好耿直,我喜欢!】【有个性的大师,爱了爱了!】【观主,看看我!
我最近工作特别不顺,总是被领导穿小鞋,是不是办公室风水有问题?
】一个网名叫“打工魂”的用户问道。我想了想,反正地也量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开视频,我看看。”我说道。很快,一个视频请求发了过来。我接通,
屏幕那头出现一个格子衫小哥,背景是典型的办公室隔间。我扫了一眼,
立刻就找到了问题所在。“你背后,是不是正对着一条走廊的尽头?
”格子衫小哥一脸震惊地点头:“对啊观主!我这个位置就是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位置!
你怎么知道?”“这叫‘路冲煞’,”我言简意赅地解释道,
“人来人往的气流会直冲你的后背,让你心神不宁,容易出错,还容易招小人。你的领导,
办公室是不是就在走廊的另一头?”“是……是的!”格子衫小哥的嘴巴已经张成了O形。
“他看你,就像看一根顶门杠,自然不顺眼。”“那……那我该怎么办啊观主?
我又不能换位置。”“简单,”我说道,“去买一盆带刺的仙人掌,放在你椅子背后,
对着走廊。记住,要多刺的那种。另外,换一件红色的衣服穿,连续穿三天。
”“仙人掌挡煞,红色提气。就这么简单?”小哥有点不敢相信。“信不信由你。
”我淡淡地说完,就挂断了视频。直播间里的人已经彻底疯狂了。【学到了学到了!
我背后也是走廊,怪不得我老是背锅!】【观主,我背后是厕所门,怎么办?在线等,
挺急的!】【观主,开个班吧!我第一个报名!】我看着不断涌入的人流和礼物,
默默计算着这些钱够买多少砖瓦。嗯,离修好大殿,又近了一步。5与此同时,
山下的顾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可怕。顾淮安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自从和沈观离婚后,他就觉得诸事不顺。先是谈了两年、马上就要签约的欧洲大单,
对方突然毫无理由地变卦了。接着,公司新开发的一个楼盘,
在施工时接连出了好几次不大不小的安全事故,虽然没出人命,却也被监管部门叫停,
勒令整改,声誉大损。公司的股价,也因此连续跌了好几天。“淮安,别皱眉了,喝口汤吧。
这是我亲手给你炖的。”林晚晚端着一个精致的保温桶走进来,声音又甜又软。
她穿着一身香奈儿最新款的白色连衣裙,妆容精致,香气宜人。若是平时,
顾淮安或许会觉得赏心悦目。但今天,他看着林晚晚,
脑子里却莫名其妙地闪过沈观那张清汤寡水的脸。沈观从不用香水,
身上总是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她也从**得花枝招展,总是素色的棉麻长裙,
看着……很舒服。“你怎么了?是不是还在想观观姐?”林晚晚敏感地察觉到了他的走神,
眼圈一红,委屈地说道,“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她。也是,
毕竟三年的夫妻……”“别胡说!”顾淮安打断她,语气有些生硬,“我只是在想公司的事。
”他接过汤碗,喝了一口,却觉得那精心熬制的鸡汤,远不如沈观随手煮的一碗清粥妥帖。
“对了,淮安,”林晚晚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这是我特意去广济寺给你求的平安符,听说很灵的,你快戴上。”顾淮安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块成色极佳的翡翠玉佩,雕工精美。他皱了皱眉:“这得不少钱吧?”“哎呀,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平安嘛。”林晚晚娇嗔道,“快戴上,希望能保佑你顺顺利利的。
”顾淮安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将玉佩戴在了脖子上。冰凉的玉佩一接触到皮肤,
他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办公室的窗外,一只乌鸦“呱”地一声飞过,声音凄厉。
顾淮安的心,莫名地往下沉了沉。6我的直播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
“风一样的男子”和“打工魂”成了我直播间的两大护法,每天准时报到,疯狂刷礼物。
他们的现身说法,比任何广告都管用。我的粉丝数,在短短一周内,从两位数暴涨到了十万。
我立下的规矩也越来越清晰:一、只看风水、相面、解厄,不卜姻缘,不问前程。
命是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二、每天只接三单,随缘挑选。看不顺眼的,给再多钱也不看。
三、所有收入,除维持个人基本生活外,全部用于修缮三清观。我的“佛系”和“规矩多”,
反而成了最大的特色。无数人挤破了头,想成为那三个幸运儿之一。这天,
一个网名叫“珠光宝气”的富婆,刷了十个嘉年华,点名要我看看她家的风水。接通视频后,
一张保养得宜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金碧辉煌的欧式别墅。“观主,你帮我看看,
我这别墅是不是哪里不对劲?我老公最近老是不回家,我怀疑他在外面有人了!
”富婆开门见山。我扫了一眼她身后的环境,摇了摇头:“你老公回不回家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再在这房子里住下去,不出三个月,你就要破大财了。
”富婆脸色一变:“观主,你可别吓我!我这房子是请香港很有名的大师看过的!
”“有名不代表有本事,”我淡淡说道,“让你家保姆把镜头转一圈,我看看。
”镜头随着保姆的走动,将别墅的全貌展现给我。
当我看到客厅角落里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时,我开口道:“停。”“让你老公把鱼缸砸了。
”富婆大惊失色:“砸了?观主,这……这鱼缸是我老公最喜欢的,里面养的龙鱼,
花了大几十万呢!”“鱼是好鱼,缸是好缸,但位置不对。”我指着屏幕,“你家坐北朝南,
财位在西南。你把一个巨大的水缸放在财位上,这不叫‘以水催财’,这叫‘见财化水’。
你住进来多久,就漏了多久的财。”“你再看看你老公,印堂发黑,眼白浑浊,
最近是不是投资什么都亏本?”富婆愣住了,喃喃道:“是……是的。他最近投了几个项目,
全都赔了,已经亏进去上千万了……”“那条龙鱼,已经替你们挡了一部分。
但它也快撑不住了。”我说道,“你看它,是不是总在水面挣扎,鳞片也失去了光泽?
”富婆赶紧让保姆把镜头对准鱼缸,果然,那条价值不菲的龙鱼,状态极差,
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那……那怎么办?”富婆彻底慌了。“砸了鱼缸,把鱼放生。
在原来的位置,放一座假山石,或者一盆不开花的绿植。记住,土克水,以山镇水,
才能稳住你的财位。”“就这样?”“就这样。”挂断视频后,
直播间里的人对我的敬佩又上了一个新高度。而我,看着账户里又多出来的一笔巨款,
心满意足地盘算着,可以先给三清祖师爷换个金身了。7顾淮安最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公司的危机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反而越陷越深。
而他和林晚晚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他发现林晚晚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
她热衷于参加各种名媛派对,结交富二代,刷他的卡买起奢侈品来,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和他想象中那种岁月静好、红袖添香的爱情,完全是两回事。他开始频繁地失眠,
好不容易睡着,梦里却总是出现沈观的影子。梦里的她,还是那副清冷的样子,
默默地为他煮茶,为他抚平紧锁的眉头。他想抓住她,她却像一缕青烟,消失不见。这天,
助理小张敲门进来,脸色凝重。“顾总,城西那个项目的工地,又出事了。脚手架突然倒塌,
砸伤了三个工人。”顾淮安猛地站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请了安全顾问,二十四小时盯着吗!”“是……是的,”小张战战兢兢地说道,
“可就是邪门,所有的安全措施都做到了,但事故还是防不胜防。工人们现在都人心惶惶的,
说……说那块地不干净。”“胡说八道!”顾淮安怒斥道,“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
”小张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声说道:“顾总,空穴来风啊。而且,我听说,
之前给咱们公司做风水顾问的李大师,前几天突然金盆洗手,回老家种田去了。
说是……不敢再吃这碗饭了。”顾淮安愣住了。李大师是业内非常有名的风水师,
每年光是顾问费,顾氏就要付给他七位数。他怎么会突然不干了?一股寒意,
从顾淮安的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想起了沈观。那个在他看来“无趣乏味”的女人,
似乎总有些神神叨叨的本事。他搬新家,她说那盆造型奇特的滴水观音不能放卧室,他没听,
结果当晚就鬼压床。他买新车,她说车里不能挂那个羚羊头骨的挂件,他觉得酷,没理会,
结果第二天就出了追尾事故。这样的事情,三年里,发生过无数次。每一次,
他都当成是巧合,甚至嘲笑她封建迷信。现在想来,那哪里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