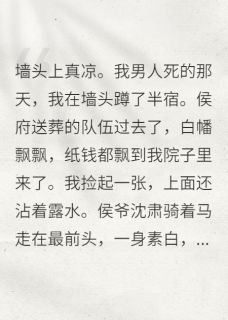墙头上真凉。
我男人死的那天,我在墙头蹲了半宿。侯府送葬的队伍过去了,白幡飘飘,纸钱都飘到我院子里来了。我捡起一张,上面还沾着露水。
侯爷沈肃骑着马走在最前头,一身素白,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就是看着比平时更冷。他好像往这边瞥了一眼。
我赶紧缩头,墙头的碎瓦片硌得我脚底板生疼。
“晦气。”我低骂一句,揉着脚跳下墙头。
我男人程明礼,是侯爷沈肃的远房表弟。半个月前,他跟着沈肃出去办事,回来的只有一副薄棺。侯府的人说,是意外失足,掉河里淹死了。捞上来的时候,人都泡发了。
我成了寡妇,才十八。
程明礼没什么家底,就城外几亩薄田,还有这个靠着侯府后巷的小破院。他死了,侯府给了二十两烧埋银子,算是仁至义尽。我捏着那二十两,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但不是因为伤心。
我和程明礼成亲刚一年,没什么情分。他就是个眼高手低的破落户,仗着和侯府沾点亲,总想着攀高枝。攀不上,回来就喝酒,喝多了就骂我,嫌我娘家穷,帮衬不了他。挨打是常事。
他死了,我心里头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解脱了。
可这解脱的滋味还没咂摸出点甜,麻烦就来了。
程明礼死得蹊跷。侯府说他是失足落水,可他那个人,贪生怕死得很,大晚上的,没事往河边跑什么?还偏偏是跟着沈肃出去的时候没的。
更怪的是,头七那天,我半夜被尿憋醒,迷迷糊糊去后院茅房。回来时,听见院墙根底下有动静,像是有人用指甲在抠墙皮。我吓得汗毛倒竖,壮着胆子凑近墙缝往外看。
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一个人影,穿着程明礼下葬时那身衣裳,正背对着我,一下一下地抠着我家墙角那块松动的砖!
我差点叫出声,死死捂住嘴。那影子动作僵硬,抠了几下,似乎没抠动,又慢腾腾地往前挪,消失在巷子另一头的黑暗里。
我腿一软,瘫在地上,后背全是冷汗。是鬼?还是……人?
那晚之后,我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还好,一到天黑,尤其是后半夜,我就忍不住爬上墙头,躲在阴影里,死死盯着巷子深处。我想看看,那晚的影子,还会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