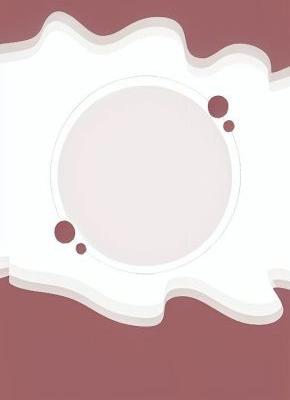秋雨连下了三日,密雨斜织成一张灰濛濛的网,将摩诃池笼在其中。水面涨起半尺,打落的芙蓉花瓣浮在水上,像撒了一层撕碎的锦缎,有的还黏在窗棂上,被雨水浸得发蔫。我正临着窗摹写父亲寄来的手书,指尖刚触到微凉的宣纸,就听得宫门外一阵喧哗,混着雨打芭蕉的声响格外刺耳。不等我唤宫人询问,贴身侍女碧月已慌慌张张跑进来,鬓边的银钗都歪了,裙角还沾着泥点:“娘娘,不好了,淑妃娘娘带着几位大臣的家眷闯进来了!”
我握着笔的手一顿,墨汁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黑点。淑妃周氏出身将门,兄长是镇守边境的节度使,在后宫中素来以家世自傲,先前虽也对我有过不满,却从未这般失态。我拢了拢衣襟,沉声道:“慌什么?让她们进来。”
不过片刻,周氏便带着四五位衣着华贵的命妇踏入暖阁,她身着绣金宫装,面色沉冷如霜,进门便扬声道:“花蕊夫人,你可知罪?”
我放下笔,亲手为她倒了杯热茶,语气平和:“淑妃姐姐此言差矣,我日日在苑中研诗作画,不知犯了何罪?”
“不知罪?”周氏猛地将茶杯掼在地上,青瓷碎裂的声响刺破雨幕,惊得窗外的雨势都似骤然急骤了几分。雨珠砸在暖阁的琉璃瓦上,噼啪作响,像是要把这精致的阁宇都砸穿。“前日西山地震,昨日锦江泛溢,钦天监已奏明陛下,此乃‘女祸’之兆!皆因你独占圣宠,迷乱君心,才引得上天示警!”
她身后的一位命妇立刻附和:“是啊夫人,如今朝堂上已有大臣上书,请求陛下将您迁出宫中,以安天意呢!”另一位则掩着帕子叹气:“听说淑妃娘娘的兄长已在边境整肃军备,若陛下再沉迷后宫,恐生变数啊。”
我心中一凛,原来她们是打着“天意”的旗号,实则想借外戚势力逼宫。周氏这招既狠又毒,将天灾与我的宠爱捆绑,既讨好了朝臣,又能顺理成章地打压我,若是应对不当,轻则失宠迁居,重则恐有性命之忧。
我缓缓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湿冷的雨风立刻卷着芙蓉的残香扑进来,拂得我鬓边的碎发微动。望着雨幕中虽被打弯、却依旧倔强托着花苞的芙蓉枝,我忽然笑了:“淑妃姐姐说我迷乱君心,可有凭据?说上天示警因我而起,又有何佐证?”
“凭据?”周氏冷笑,“陛下为你遍植芙蓉,耗银数万;为你仿制青城竹砚,调用能工巧匠数十人;甚至因李贵妃害你,便废黜一位妃嫔——这些难道不是你惑主的铁证?”
“这便是姐姐的道理?”我转身直视着她,声音陡然清亮,“陛下修芙蓉苑,是因成都气候适宜植花,既美化城郭,又能让百姓秋日赏花取乐,去年秋日芙蓉盛开时,市井间卖花的农户增收三成,这难道是祸事?调用工匠制砚,是陛下爱惜人才,那些工匠如今已入工部任职,凭手艺挣得俸禄,这难道是迷乱?”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面色渐白的命妇们,继续道:“至于废黜李贵妃,是因她行巫蛊害人之事,伤及宫闱安稳,陛下此举是整肃后宫规矩,而非单单为我。若说‘女祸’,那因嫉妒而害人的,才是真正动摇宫闱根基的祸端吧?”
周氏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手指紧紧攥着袖口,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你……你巧舌如簧!钦天监的话,难道还会有错?”
“钦天监观天象,却未必懂人心。”我取过案上的《诗经》,翻到《小雅·十月之交》,指尖划过泛黄的书页。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小了些,偶尔有一两片完整的芙蓉花瓣飘进窗内,落在书页上。“昔年幽王宠褒姒,并非因宠爱本身是错,而是错在烽火戏诸侯,错在荒废朝政。如今陛下虽宠爱我,却从未耽误早朝,更未因我而滥赏滥罚,蜀地粮仓充盈,边境安稳,这便是最好的‘天意’。”
正说着,门外传来太监尖细的唱喏:“陛下驾到——”
孟昶踏入暖阁时,身上带着一身雨后的清寒,明黄色的龙袍边角沾了些细密的雨珠。他目光扫过满地碎瓷、狼狈的命妇们,最后落在我身上——我立在窗前,衣袂轻扬,指尖还沾着墨渍,脚边落着片芙蓉花瓣。他皱了皱眉,先斥退了想要上前擦试龙袍的太监,才转向周氏:“淑妃,你在此喧哗,成何体统?”
周氏立刻跪伏在地,声音带着哭腔:“陛下,臣妾是为陛下分忧啊!如今天灾频发,皆因花蕊夫人专宠太过,还请陛下以江山为重,将她……”
“够了。”孟昶打断她,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天灾自有应对之法,与后宫何干?朕已命人开仓放粮,赈济受灾百姓,这才是安天意、顺民心的正道。”他走到我身边,见我指尖沾着墨渍,便伸手替我拭去,“慧娘方才说的话,朕都听见了,你说得对,民心才是真正的天意。”
周氏浑身一颤,不敢置信地抬头:“陛下……”
“淑妃闭门思过一月,抄写《女诫》百遍,”孟昶的语气不容置疑,“至于你兄长那边,朕会亲自去信,告诉他安心戍边,莫要插手后宫之事。”
命妇们见状,纷纷跪地告退,裙裾摩擦地面的声响混着渐歇的雨声,格外仓皇。周氏也只得狼狈离去,经过我身边时,狠狠剜了我一眼,那目光比窗外的秋雨还要凉。暖阁里终于恢复清静,只剩下铜炉中沉香燃烧的轻烟,和孟昶温热的掌心。**在他肩头,望着窗外渐渐放亮的天色,轻声道:“陛下这般维护我,怕是又要引来非议了。”
“非议又如何?”孟昶将我揽入怀中,下巴抵着我的发顶,“你以才情自守,以仁心待人,从未恃宠而骄,朕护着你,天经地义。”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不过你方才说的话,朕记下了。往后朕会更加勤勉,不让你再因这般无妄之灾受委屈。”
我心中一暖,却也生出几分隐忧。这次虽凭口舌化解危机,但周氏背后的外戚势力,绝非轻易就能撼动。她们今日败了,明日定会想出更狠毒的法子。我抬头望着孟昶,忽然道:“陛下,臣妾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
“臣妾想在芙蓉苑开设书斋,召集宫中识字的宫女学习诗文书画,”我解释道,“一来可让她们习得一技之长,二来也能让她们明白,女子并非只能靠争宠立足。”
孟昶眼中闪过赞许:“你既有此心,朕自然应允。明日朕便让人送来典籍笔墨,再派两位翰林院的学士来授课。”他轻轻刮了刮我的鼻子,“你啊,总是能想出这些好法子。”
书斋开设后,宫中渐渐有了新气象。不少宫女借着学习的机会,展露了各自的才华,有擅长记账的被调往尚宫局,有精通算术的被派去协助管理宫库,连皇后都对我的举措赞不绝口。周氏闭门思过期间,见我声望日增,更是恨得牙痒,却又无计可施。
可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秋雨彻底停了,成都的天空被洗得瓦蓝,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将满城的芙蓉花照得愈发艳丽,粉的、白的、红的花瓣上挂着水珠,像是缀了满地珍珠。可我站在芙蓉苑的廊下,望着那成片的花海,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欣喜。宫墙之内的风,从来都不会真正停歇,就像这秋日常变的天气,今日的晴空万里,或许只是为了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那日我在书斋教宫女们读诗,碧月悄悄进来禀报,说周氏的兄长派人送来了一盒珍宝,托人转交给了御书房的太监总管。我握着书卷的手指微微收紧,面上却依旧平静:“知道了,莫要声张,继续授课吧。”
窗外的芙蓉花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摇曳,阳光穿过花瓣,将影子投在书斋的案几上,斑驳细碎。方才还沾在花瓣上的露珠早已蒸发,只余下被阳光晒得温热的花香。我轻轻念出《诗经》中的句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话音刚落,一阵风卷过,吹落几朵芙蓉花,恰好落在正低头抄书的宫女发间。这深宫之路,我只能步步小心,方能在这繁华与危机并存的宫墙内,守住自己,也守住那份来之不易的温情。
书斋的竹帘被秋风掀起一角,暖融融的日光淌进来,落在宫女们抄诗的宣纸上,将“青青子衿”的字迹染得愈发清晰。我正指点小宫女阿沅勾描隶书的蚕头燕尾,忽听得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碧月脸色发白地冲进来,声音压得极低:“娘娘,御书房的刘总管带着人来了,说要查‘失窃的贡品’!”
我握着狼毫的手一顿,笔尖在纸上划出细劲的长撇。刘总管便是前几日收下周氏兄长珍宝的太监,此刻来查书斋,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放下笔,替阿沅理了理歪斜的笔杆,声音平稳如常:“慌什么?贡品失窃与咱们书斋有何相干?让他进来。”
不过片刻,身着织金蟒纹衣的刘总管便迈着四方步踏入书斋,身后跟着四个膀大腰圆的小太监。他皮笑肉不笑地向我躬身:“奴才给花蕊夫人请安。昨日御书房失窃了一方西域进贡的羊脂玉砚,据线人供称,赃物被藏在了芙蓉苑书斋,还请夫人行个方便。”
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棂照进来,将他脸上的皱纹刻得愈发深刻。我目光扫过他腰间系着的蜜蜡佛珠——那佛珠颗颗饱满,色泽温润,绝非寻常太监能佩戴,想来便是周氏兄长所赠。“刘总管说笑了,”我侧身让开通路,“书斋日日人来人往,若真藏了赃物,早该被人发现。总管要查便查,只是莫要惊吓了这些宫女。”
小太监们立刻翻箱倒柜,书架上的典籍被胡乱堆叠,案上的笔墨纸砚散落一地。阿沅吓得攥紧了衣角,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示意她安心。刘总管的目光在书斋里逡巡,最终落在我案头那方青城竹砚上——那是孟昶特意为我仿制的,砚台侧面刻着我亲手题的“芙蓉心”三字。
“夫人这方砚台倒是别致。”刘总管上前一步,伸手便要去拿。碧月正要阻拦,却被他身后的小太监推搡了一个趔趄。我抬手按住砚台,语气微冷:“这是陛下所赐的竹砚,并非什么羊脂玉砚,总管莫非看走了眼?”
“是不是,查过便知。”刘总管猛地用力一夺,竹砚“咚”地一声磕在案角,砚盖摔落在地,露出里面藏着的一块莹白的玉片——那玉片正是羊脂玉砚的碎片,边缘还粘着些许墨渍。阿沅惊呼一声,宫女们瞬间炸开了锅,纷纷跪倒在地:“娘娘冤枉啊!”
刘总管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厉声喝道:“人证物证俱在,花蕊夫人,你还有何话可说?这玉砚碎片藏在你的贴身砚台里,分明是你监守自盗,妄图私藏贡品!”
我弯腰拾起砚盖,指尖抚过砚台内侧的凹槽——那凹槽边缘光滑,显然是新凿出来的,绝非我平日使用的模样。昨夜我离开书斋前,曾亲手将竹砚擦拭干净,那时还并无此凹槽。我抬眸望向刘总管,目光锐利如刀:“总管何时发现玉砚失窃?又是何人指证赃物在我这里?”
“昨日亥时发现失窃,”刘总管眼神闪烁了一下,“是……是书斋的杂役宫女所指。”
“哦?”我转向跪在人群中的杂役宫女春桃,她正是周氏闭门思过时,被派来书斋当差的人,“春桃,你且说说,你何时看见我藏了玉砚碎片?”
春桃浑身颤抖,头埋得极低:“是……是昨日傍晚,我路过书房,看见娘娘在砚台里藏东西……”
“一派胡言!”一直沉默的阿沅突然开口,她膝行到我面前,举起手中的记账本,“娘娘昨日傍晚一直在教我们读诗,这是我记录的授课时辰,在场的二十三位宫女都可以作证!而且昨日戌时我打扫书房时,曾仔细擦拭过这方竹砚,那时砚台里干干净净,根本没有什么凹槽和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