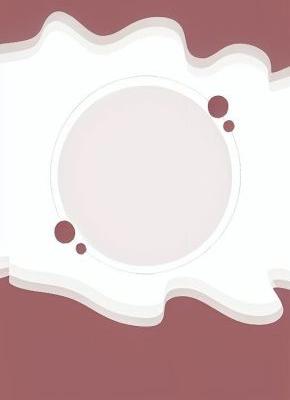第一章香江女阿飞成了天煞孤星我叫汪予曦,二十一世纪香江城的女阿飞。我是个孤儿,
在打打杀杀中长大,混成了黑道老大。我能打能赌,听力视力特别厉害,
眼睛还能透视物体内部。名下财产几千万,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可惜在一次火拼中,
我被人背后捅了刀子。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土炕上。屋子破得漏风,
墙皮掉得七七八八,屋里就一张桌子两个破凳子。我脑子里突然涌进一堆陌生记忆,
整个人都懵了。原来我穿越了,到了一个叫临兆国的架空时代。这副身体的原主也叫汪予曦,
是银杏村远近闻名的天煞孤女。村民都说她克父克母克全家,二十五岁了才嫁出去,
嫁的还是个街溜子。我挣扎着坐起来,浑身酸痛得厉害。原主是病死的,高烧了好几天,
没人管没人问。现在换了芯子,我汪予曦可没那么好欺负。正想着,
门被“砰”地一声踹开了。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男人摇摇晃晃走进来,浑身酒气。
他长得倒是不错,眉眼挺周正,就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让人来气。“喂,死了没?
没死就起来做饭!”他一**坐在炕沿上,鞋子都没脱。这就是我那个便宜丈夫龚运远,
银杏村有名的街溜子。好吃懒做,爱赌如命,整天游手好闲。我眯起眼睛打量他,
记忆里这人唯一的优点是不嫖不偷,赌钱也不借不赊——虽然那是因为根本没人肯借给他。
“看什么看?”龚运远被我看得发毛,“烧傻了?”他伸手想来探我额头,
我一巴掌拍开他的手。“啪”的一声脆响,把他打愣了。我也愣了——这身体弱得很,
但刚才那一下,我用了前世打架的技巧。龚运远瞪大眼睛:“你敢打我?”他站起来要发火,
我比他动作更快。虽然身体虚弱,但我二十年的打架经验不是白给的。
我一脚踹在他小腿迎面骨上,他“嗷”一声弯下腰,我顺势按住他脑袋往炕沿上磕。
当然我没真用力,但这架势够吓人。“从今天起,这个家我说了算。”我松开他,冷冷地说。
龚运远捂着头,一脸不敢置信。原主平时沉默寡言,性格软弱,挨打挨骂都不敢吭声。
“你、你中邪了?”龚运远后退两步。我慢慢下炕,虽然腿发软,但站得笔直。
“以前那个汪予曦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新的汪予曦。”我盯着他的眼睛,
“听懂了吗?”龚运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走到破桌子前,发现上面有几个铜板。
数了数,就十二文钱,够买两斤糙米。“钱呢?”我转头问他。
龚运远眼神躲闪:“输、输光了...”我深吸一口气。行,赌是吧。
老娘前世在**混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带我去**。”我说。
龚运远以为自己听错了:“啥?”“我说,带我去**。”我一字一顿,“现在,马上。
”第二章空手套**半个时辰后,我跟在龚运远身后进了镇上的赌坊。
这地方叫“如意坊”,门脸不大,里面乌烟瘴气。一群男人围在几张桌子前,吆五喝六的,
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和烟味。我一进门,所有人都看过来。女人进**,在这年头可是稀罕事。
“哟,龚老四,把你婆娘都带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笑道,“怎么,输得裤子都没了,
拿婆娘抵债?”龚运远脸涨得通红,我按住他肩膀,走到那汉子面前。“你是管事的?
”我问。汉子上下打量我,眼神猥琐:“小娘子找哥哥有事?”我笑了笑,抬手就是一耳光。
“啪!”全场瞬间安静了。汉子捂着脸,半天没反应过来。我甩了甩手:“嘴巴放干净点,
叫你们掌柜出来。”前世在香江,这种场子我见多了,不给下马威,他们以为你好欺负。
果然,几个打手围了上来。龚运远吓得直拉我袖子:“咱、咱走吧...”我没理他,
盯着从里间走出来的一个瘦高男人。这人四十来岁,穿着绸缎长衫,手里盘着两个核桃。
“这位娘子,好大的火气。”瘦高男人眯着眼睛,“在下姓刘,是这如意坊的掌柜。
不知娘子有何指教?”我拉了条凳子坐下:“来**,当然是赌钱。”周围响起哄笑声。
刘掌柜也笑了:“娘子带了多少本钱?”我掏出那十二个铜板,“啪”地拍在桌上:“这些。
”哄笑声更大了。龚运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刘掌柜摇摇头:“这点钱,
连最低注都不够...”我打断他:“赌大小,一局定胜负。我赢了,你这赌坊归我。
我输了,我这个人归你。”这话一出,全场哗然。龚运远急得跳脚:“你疯了?!
”刘掌柜眼神变了,重新打量我:“娘子说笑吧?”“你看我像说笑吗?”我直视他,
“不敢接?”刘掌柜沉默片刻,哈哈大笑:“好!有胆色!我接了!
”他挥手让人清出一张赌桌,拿出骰盅和三颗骰子。“娘子选,赌大还是赌小?
”我说:“赌大,谁点数大谁赢。”刘掌柜点头,亲自摇骰。他手法很花哨,
骰盅在手里转出残影,“砰”地扣在桌上。“娘子先请?”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所有人都盯着我。我闭上眼睛——其实不用闭,但得做做样子。前世我的透视眼跟过来了,
刚才试过,能看穿木板。我集中精神,视线穿透骰盅。三颗骰子,五点、六点、六点,
十七点,很大了。我睁开眼:“刘掌柜好手法。”他得意一笑:“该娘子了。”我接过骰盅,
掂了掂重量。前世我混**,摇骰子是基本功。我手腕一抖,骰子在盅里高速旋转。
透视眼让我能清楚看到每一颗骰子的转动。三颗骰子慢慢停下,六点、六点、六点,豹子,
通杀。我扣下骰盅,看向刘掌柜。“开吧。”我说。刘掌柜先开,果然是十七点。
周围一片赞叹声。轮到我了,我慢慢提起骰盅——三颗鲜红的六点刺眼地躺在桌上。死寂,
然后炸开了锅。“豹子!十八点!”“我的天,这女人神了!
”“刘掌柜输了...”刘掌柜脸色铁青,死死盯着骰子。
我站起来:“如意坊现在是我的了,刘掌柜,请吧。”打手们围了上来,但眼神犹豫。
我扫视一圈:“愿意留下的,工钱翻倍。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一半人动摇了。
刘掌柜咬牙:“愿赌服输,我们走!”他带着几个亲信离开了。
我转身看向目瞪口呆的龚运远:“还愣着干什么?清点账目。
”龚运远结结巴巴:“你、你真会赌?”我勾唇一笑:“不然呢?
你以为我刚才在跟你开玩笑?”第三章收编街溜子当天晚上,
我坐在如意坊的账房里翻看账本。赌坊生意不错,每月能赚二三十两银子。
这时代一两银子够普通人家过一个月了,但对见过大钱的我来说,这点收入还不够看。
龚运远在旁边坐立不安,时不时偷瞄我。我放下账本:“有话就说。
”他咽了口唾沫:“你真要把赌坊改成...麻将室?那是什么东西?
”我笑了:“能让我们赚大钱的东西。”前世在香江,我管过好几个麻将馆。赌坊风险大,
容易惹官司,麻将室就不同了,抽水稳当,还不容易出事。我画了麻将和扑克的图纸,
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镇上的木匠。木匠老李头看着图纸直挠头:“汪娘子,这、这些是什么呀?
”我耐心解释:“这叫麻将,一共一百三十六张牌。这是扑克,五十四张。能做吗?
”老李头研究了半天:“能做是能做,
就是费工夫...”我拍出五两银子:“十天内做出来,我再加五两。
”老李头眼睛亮了:“保证按时完成!”从木匠铺出来,我去了一趟集市。
银杏村所在的清河镇不大,但位置不错,往来的客商不少。路过一个巷口时,
我看见几个混混在围殴一个少年。少年抱着头蜷在地上,一声不吭。我本不想管闲事,
但其中一个混混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叫你偷老子东西!龚老四都不敢惹我们黑虎帮,
你算哪根葱?”龚运远的名字让我停住脚步。我走过去:“住手。”混混们回头,看见我,
都笑了。“哟,小娘子想英雄救美?”为首的黄牙汉子朝我走来,
“长得不错嘛...”我一脚踹在他肚子上,他“嗷”一声跪倒在地。另外三个混混冲上来,
我侧身躲过一拳,肘击一人肋下,抬腿踢中另一人膝盖,最后一个被我抓住手腕一拧一推,
摔了个狗吃屎。四个混混躺在地上**。我走到少年面前,伸手拉他起来。少年十五六岁,
瘦得跟竹竿似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但眼睛很亮。“谢谢...”他低声说。
“他们为什么打你?”我问。少年抿着嘴不说话。黄牙汉子爬起来想跑,
我一脚踩住他后背:“我问话呢。
”黄牙汉子哭丧着脸:“他、他偷我们帮主的钱袋...”少年突然开口:“我没偷!
那钱袋是我捡的!他们污蔑我!”我看向黄牙汉子,他眼神躲闪。我明白了,
蹲下身看着少年:“你叫什么?多大了?”“我叫王小石,十六了。”少年说,
“爹娘都死了,我在镇上讨生活。”我想了想:“想不想有口饭吃?
”王小石眼睛一亮:“想!”“跟我来。”我转身往赌坊走,几个混混连滚爬爬跑了。
王小石跟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问:“您是...”“汪予曦,如意坊的新掌柜。
”我头也不回地说。回到赌坊,龚运远正在指挥人打扫。看见我带回个半大小子,
他愣住了:“这是谁?”我没理他,对王小石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干活,管吃管住,
每月给你二百文。”王小石激动得直点头。龚运远把我拉到一边:“你疯了?
收留个来路不明的小子!”我瞥他一眼:“你有意见?
”龚运远缩了缩脖子:“没、没有...”我拍拍他的脸:“乖,听话就不挨打。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整顿赌坊。原来的打手走了大半,留下的都是老实本分的。
我把规矩立得清清楚楚:不准出老千,不准欺负穷人,不准逼债逼死人。违者打断腿扔出去。
镇上的混混们听说如意坊易主了,还是个女人当家,都跑来凑热闹。我把他们全召集起来,
站在赌坊门口说话。“从今天起,如意坊改名叫‘闲趣堂’。想继续赌的,去别处。
想找正经活干的,留下。”一个疤脸汉子嗤笑:“女人当家,房倒屋塌!兄弟们,
咱们...”话没说完,我一拳砸在他鼻梁上。他惨叫一声倒下去,鼻血直流。
其他混混都愣住了。我甩甩手:“还有谁不服?”没人敢说话。
我继续说:“闲趣堂要开镖局,缺人手。愿意干的,每月一两银子,包吃住。不愿意的,
现在滚蛋。”混混们面面相觑。镖局?他们这些街溜子能干镖师?
王小石第一个站出来:“**!”有几个混混犹豫着也站了过来。最后二十几个混混,
留下了十二个。我看着他们:“丑话说在前头,进了我的门,就得守我的规矩。不欺负穷人,
不调戏妇女,不偷不抢。做得到吗?”十二个人稀稀拉拉应声。我眼神一冷:“大声点!
”“做得到!”这次整齐多了。我点点头:“今天先练站姿,站满一个时辰才能吃饭。
”龚运远在旁边小声嘀咕:“真能折腾...”我转头看他:“你也一起站。
”龚运远瞪大眼睛:“我?”我笑了:“怎么,你不是我的人?
”龚运远不情不愿地站进队伍里。我看着这群歪歪扭扭的汉子,心想:慢慢来,
总会**出来的。第四章末世征兆现十天后,老李头送来了第一批麻将和扑克。
我把闲趣堂重新布置,一楼摆八张麻将桌,二楼设雅间。开业那天,我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
吸引了不少人来看热闹。我让王小石当荷官,教客人打麻将。起初大家都不懂,
但玩了几圈后,渐渐上了瘾。麻将这种游戏,比单纯赌大小有趣多了,还能聊天喝茶。
第一天下来,抽水就收了五两银子。
龚运远数钱时手都在抖:“这、这也太好赚了...”我拍开他的手:“别动歪心思,
这是正经生意。”晚上打烊后,我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十二个前混混,加上王小石和龚运远,
一共十四个人。“从明天开始,上午练武,下午干活。”我说,
“我请了镇上的武师傅教你们基本功。三个月后,镖局开张。
”一个叫赵大的汉子挠头:“掌柜的,咱们真能当镖师?”我点头:“只要肯下功夫,
没什么不能的。”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帮人底子差,得狠狠操练。但没办法,
这年头招人不容易,只能自己培养。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把人叫起来了。武师傅姓陈,
是退伍的老兵。他一看这群歪瓜裂枣就皱眉头:“汪娘子,
这些人...”我塞给他二两银子:“陈师傅多费心,练得好的有赏。”陈师傅这才点头。
于是闲趣堂后院成了练武场,每天早晨都响起哼哼哈哈的声音。龚运远最不情愿,
没练两天就想偷懒。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按在地上打了一顿**。“都给我听好了!
”我踩在龚运远背上,“练好了,有肉吃有钱拿。练不好,就像他一样!”龚运远羞愤欲死,
但从此再不敢偷懒。日子一天天过去,麻将馆生意越来越好。镇上有些老人看不惯,
说女人不该抛头露面。我全当没听见,该干嘛干嘛。一个月后,闲趣堂净赚了八十两银子。
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留作周转,一份给大家发赏钱,一份存起来准备开镖局。这天晚上,
我正算账,王小石慌慌张张跑进来:“掌柜的,出事了!”我抬头:“怎么了?
”王小石喘着气:“镇东头的李屠户,他、他疯了!”我和龚运远赶到李屠户家时,
外面围了好多人。屋里传来野兽般的嘶吼,还有砸东西的声音。几个壮汉堵在门口,
不敢进去。“怎么回事?”我问邻居。一个老太太拍着大腿:“造孽啊!好端端的人,
突然就发狂了,见人就咬!”我心里一沉,扒开人群往里看。只见李屠户眼睛血红,
嘴角流着涎水,正疯狂地撕咬一只活鸡。那样子...根本不像人。
龚运远吓得往后缩:“这、这是中邪了吧?”我盯着李屠户,突然发现他脖子上有个伤口,
已经溃烂发黑。那伤口形状很奇怪,像是被什么动物咬的。“他最近去过哪里?
”我问李屠户的老婆。女人哭哭啼啼:“前天上山砍柴,
回来就说被什么东西咬了...”正说着,李屠户突然转向门口,朝我们扑过来。
人群尖叫着散开。我抄起门边的扁担,一棍子抽在他腿上。李屠户摔倒在地,
但马上又爬起来,完全感觉不到疼痛。“捆起来!”我大喝。几个胆子大的汉子找来绳子,
七手八脚把李屠户捆成粽子。即使这样,他还在挣扎嘶吼,力气大得吓人。镇长赶来了,
一看这情况也傻眼。“快,快去请大夫!”镇长吩咐。大夫来了,
把脉后直摇头:“脉象紊乱,邪气入体,老朽无能为力...”李屠户的老婆哭晕过去。
我看着被捆住的李屠户,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前世我经历过末世题材的电影和小说,
这种症状太像...丧尸了。但这是古代啊,怎么可能?当天夜里,
镇上又出了三起类似的案例。都是上山被咬,回来后发狂。镇长下令封山,但已经晚了。
三天后,镇上出现了十几个发狂的人。他们力大无穷,不知疼痛,见活物就咬。被咬伤的人,
半天后也会发狂。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闲趣堂关了门,所有人都聚在后院。
陈师傅面色凝重:“老夫从军二十年,没见过这种怪病。”王小石小声说:“掌柜的,
咱们怎么办?”我看着院子里练武的汉子们,突然有了主意。“从今天起,闲趣堂改行。
”我说,“不做麻将馆了,做安保公司。”所有人都没听懂。我解释道:“就是保护镇子,
打那些发狂的人。愿意干的,工钱翻三倍。”龚运远第一个反对:“你疯了?
那东西会咬人的!”我冷冷看他:“那你自己跑啊,看你能跑多远。”其实我已经想好了,
这种时候,抱团才能活下来。我让人把前院的桌椅全拆了,改成训练场。
又去铁匠铺订了一批长棍和盾牌。长棍可以远距离攻击,盾牌能防咬。陈师傅教大家结阵,
三人一组,互相照应。我则开始盘点库存——粮食够吃两个月,水井在后院,暂时没问题。
第四天,镇长带着人找上门来。“汪娘子,听说你在训练人手?”镇长擦着汗,
“现在镇子危在旦夕,衙门的人手不够,能否请你们帮忙?”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帮忙可以,但有条件。”我说,“第一,镇上所有粮食统一调配。第二,
所有青壮年听我指挥。第三,我要临时治安官的职位。
”镇长愣住了:“这、这不合规矩...”我笑了:“镇长,现在还有功夫讲规矩吗?
外面那些东西越来越多,再不想办法,全镇人都得死。”镇长咬牙:“好!我答应你!
”当天下午,我成了清河镇的临时治安官。我把镇上所有能打的人编成三队,轮流巡逻。
又组织妇女老人做饭、做绷带。发狂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三十几个了。
我们把病人隔离在镇西的祠堂,派人看守。这天夜里,我正在巡视,
突然听见远处传来惨叫声。我和龚运远带着一队人赶过去,看见祠堂方向火光冲天。“坏了!
”我暗叫不好。等我们赶到时,祠堂的门被撞开了,十几个发狂的人冲了出来。
他们眼睛在黑暗中发着红光,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一个守夜的汉子被扑倒,
脖子被咬穿,鲜血喷溅。我抡起长棍,一棍砸在那个发狂者的头上。“咔嚓”一声,
头骨碎裂,但他还在动。“打脖子!”我大喊。陈师傅教的,颈椎是最脆弱的地方。
队员们反应过来,专攻颈部。一番混战后,总算把冲出来的发狂者全放倒了。
但那个被咬的汉子,已经开始抽搐。他眼睛渐渐变红,挣扎着要站起来。我走过去,
举起长棍。汉子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杀...杀了我...”我闭了闭眼,
一棍砸在他后颈上。他倒下去,不动了。周围一片死寂。
龚运远脸色惨白:“你、你杀人了...”我擦掉溅到脸上的血:“他已经不是人了。
都看清楚,被咬的人,半个时辰内就会变。发现谁被咬了,马上隔离。”回去的路上,
没人说话。这是我穿越后第一次杀人,但奇怪的是,我没什么感觉。前世打打杀杀见多了,
现在只想活下去。第二天,我下令把所有发狂者和被咬的人都集中到祠堂,烧掉。
镇长坚决反对:“那是活人啊!”我盯着他:“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不烧掉,病毒会扩散。
镇长,你想全镇人都变成那样吗?”镇长说不出话,最后痛苦地点头。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黑烟笼罩清河镇,空气里都是焦臭味。妇女们在哭,男人们沉默着。我站在闲趣堂的屋顶上,
看着这一切,心里发冷。这世道,真的要乱了吗?第五章末世求生路大火之后,
清河镇平静了几天。发狂的人没再出现,但也没人敢上山了。镇上的存粮开始紧张,
虽然统一调配,但也撑不了多久。我让王小石带人去统计各家各户的余粮,结果不容乐观。
“最多还能撑半个月。”王小石汇报时愁眉苦脸。龚运远这几天老实多了,
大概是见识了生死,整个人都蔫了。这天晚饭后,
他磨磨蹭蹭凑过来:“那个...你真觉得这是病?”我正擦着长棍,头也不抬:“不然呢?
”龚运远压低声音:“我听说,是山神发怒了...”我嗤笑:“山神发怒就让人发狂咬人?
那这山神也太没品了。”龚运远被噎得说不出话。其实我心里也没底。这症状太像丧尸病毒,
但传播速度没那么快,被咬的人要半天才变。而且,他们怕火,烧了就没事。如果是病毒,
应该会通过空气传播才对。半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陈师傅。
他脸色很难看:“掌柜的,出事了。镇子外面来了一群人,说是从隔壁县逃难来的。
”我和龚运远赶到镇口,看见外面黑压压站了几十号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眼神里满是恐惧。为首的是个中年书生,看见我们,噗通跪下了:“求各位行行好,
收留我们吧!我们县...全完了!”书生说,他们县三天前开始出现发狂的人,
比清河镇严重得多。衙门压不住,整个县都乱了。他们这群人逃出来时,
县城已经成了人间地狱。“那些人...他们吃人...”书生浑身发抖,“不是咬,
是吃...”我头皮发麻。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态比我想的严重多了。镇长也来了,
一听这话就摇头:“不行不行,我们粮食都不够,哪能收留你们?”难民们哭成一片。
我看着这些老弱妇孺,心里挣扎。前世我是混黑道的,不是什么好人。
但让我眼睁睁看着这些人死,我也做不到。最后我说:“可以收留,但有条件。
”所有人都看向我。我继续说:“青壮年编入巡逻队,妇女老人帮忙干活。粮食按劳分配,
不干活没饭吃。同意的留下,不同意的请自便。”书生连连磕头:“同意!我们都同意!
”于是清河镇又多了五十三口人。粮食更紧张了,我决定组织人上山打猎。虽然危险,
但总比饿死强。我挑了二十个身手好的,包括龚运远——他现在棍法练得还不错。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武器进山。山里静得可怕,连鸟叫都听不见。走了半个时辰,
突然听见前面有动静。我示意大家停下,自己悄悄摸过去。透过树林缝隙,
我看见一幕骇人的景象:七八个发狂的人正在分食一只野猪。他们不是咬,
是真的在撕扯生肉,满嘴是血。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动作比之前快多了,眼神也更凶狠。
我慢慢退回去,打了个手势:撤。但就在这时,龚运远踩断了一根枯枝。“咔嚓”一声,
那些发狂的人齐刷刷转过头来。他们的眼睛,在树林的阴影里闪着红光。“跑!”我大喊。
所有人转身就跑。但那些东西速度太快了,转眼就追了上来。一个队员被扑倒,
我返身一棍砸在袭击者头上。这次用了全力,那东西的头像个西瓜一样爆开。
但更多的扑了上来。我们背靠背围成圈,长棍乱舞。龚运远吓坏了,棍法全乱,差点被咬到。
我一把拉开他,自己手臂却被划了一道。伤口不深,但见血了。“掌柜的!”王小石惊叫。
我低头看看伤口,又看看那些发狂的人——他们闻到血腥味更疯狂了。我咬牙:“别管我,
撤!”我们边打边退,好不容易退到山脚。清点人数,少了三个人。我的手臂**辣地疼,
脑子开始发晕。龚运远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被划伤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按照之前的经验,被咬会感染,划伤呢?“先回去再说。”我咬牙坚持。回到镇上,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伤口已经发黑,流出的血是暗红色的。我头晕得厉害,浑身发冷。
这不是好兆头。龚运远在门外敲门:“你、你还好吗?”我没回答,盯着伤口看。突然,
我想起一件事——我的透视眼。我集中精神看向伤口内部,看见黑色的细丝顺着血管往上爬。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试着用内力——前世我会一点气功,但不多——逼那些黑丝。
没想到还真有效,黑丝后退了一点。我大喜,盘腿坐下,全力运转那点微薄的内力。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浑身被汗湿透,但头不晕了。再看伤口,黑色褪去,流出鲜红的血。
我包扎好伤口,打开门。龚运远还等在门外,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没变?
”我笑了:“怎么,失望了?”他连连摇头:“不是不是...你没事就好。
”我拍拍他的肩:“去告诉大家,划伤不一定会感染,但要及时处理。
”这件事给了我启发:内力可以对抗这种病毒。我把所有会武功的人召集起来,包括陈师傅。
“从今天起,上午练武,下午练内功。”我说,“这能保命。”陈师傅将信将疑,
但还是照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清河镇成了方圆百里唯一的避难所。越来越多的难民涌来,
镇子住不下了,我们开始扩建围墙。我让人用木头和石头垒起三米高的墙,
把整个镇子围起来。粮食成了大问题。我组织人开垦镇外的荒地,种上生长快的蔬菜。
又挖了三个大鱼塘,养鱼养鸭。虽然还是不够吃,但至少不会饿死。这天,我正在巡视围墙,
王小石跑过来:“掌柜的,外面来了一队官兵!”我上墙一看,果然,
二十几个穿着盔甲的士兵站在镇外。为首的是个年轻将领,面色冷峻。“开门!”将领喝道,
“本将奉知府之命,征调所有青壮年入伍!”镇长赶紧跑过来:“军爷,
我们镇子现在自顾不暇,实在抽不出人啊...”将领冷笑:“抗命者,按逃兵论处,斩!
”士兵们拔出了刀。墙上的民兵也举起了长棍。气氛剑拔弩张。我走下围墙,
打开侧门走了出去。“将军怎么称呼?”我问。将领打量我:“你就是那个女治安官?
本将姓秦。”我点点头:“秦将军,现在到处都有发狂的人,你把青壮年都带走,
镇上这些老弱妇孺怎么办?”秦将军不耐烦:“那是你们的事!军令如山,违者死!
”我笑了:“将军,你带这些人去打仗,打得过那些发狂的东西吗?他们不怕刀剑,不怕死,
你砍掉他一只手,他还能用嘴咬你。”秦将军脸色一变,显然见过那种场面。
“那你说怎么办?”他语气软了一些。我正色道:“合作。你们有铠甲兵器,
我们有围墙和经验。我们提供粮食,你们提供保护。如何?”秦将军思考良久,
终于点头:“可以,但我需要见见你们主事的。”镇长想上前,我拦住他:“我就是主事的。
”秦将军诧异:“女人当家?”我直视他:“有问题吗?”他看了我半晌,突然笑了:“好,
有胆色。就这么定了。”于是二十几个士兵住进了清河镇。
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不止我们这里,整个临兆国都出现了发狂的人。朝廷已经乱了,
各地自立为王,末世真的来了。晚上,我站在围墙上,看着星空。龚运远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站在我旁边。“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我摇摇头:“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以前觉得你凶,现在觉得...你挺厉害的。
”我转头看他。月光下,他的侧脸线条柔和了些。这几个月,他变了,不再游手好闲,
练武比谁都刻苦。有次巡逻,他还救了一个小孩。“你也变了。”我说。
他挠挠头:“被逼的呗。这世道,不变就得死。”我笑了:“是啊,不变就得死。
”远处传来守夜人的梆子声,三更天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会有新的挑战。但我不怕。
前世我从街头混到老大,什么风浪没见过。今生虽然换了时代,换了身份,但我还是我。
天煞孤星又如何?末世来了又如何?我汪予曦,就是要在这乱世里,活出个人样来。
“回去吧。”我对龚运远说,“明天还要训练呢。”他点点头,跟在我身后。
我们一前一后走下围墙,影子在月光下拉得很长。清河镇的灯火在身后明明灭灭,
像黑暗里的一点希望。这末世,才刚刚开始。但我知道,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而我,
会带着这群人,在这乱世里,杀出一条生路。
第六章军民的磨合秦将军的士兵们住进清河镇后,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这些当兵的看不起镇上的民兵,觉得他们就是一群拿着棍子的农民。
而镇民们则觉得士兵们白吃白喝,还不守规矩。第三天中午,冲突就爆发了。
一个叫李老四的士兵喝醉了,调戏做饭的刘寡妇。王小石带人制止,双方推搡起来。
等我和秦将军赶到时,两拨人已经抄起家伙对峙。“都放下!”秦将军喝道。
士兵们不情不愿地收了刀,但民兵们还举着长棍。我走过去,
一巴掌扇在李老四脸上:“镇上的规矩,调戏妇女者,打断一条腿。”李老四酒醒了,
瞪着秦将军:“将军,她打我!”秦将军脸色铁青:“汪娘子,我的人我来管教。
”我冷笑:“秦将军,你的人要是管得好,就不会有今天这事。我再说一遍,在清河镇,
守我的规矩。”气氛又紧张起来。秦将军的手按在刀柄上,我身后的民兵也往前一步。
就在这时,龚运远突然开口:“都别吵了!外面那些发狂的随时可能攻进来,
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死吗?”所有人都愣住了。龚运远走到两拨人中间:“李老四做错了,
该罚。但现在是特殊时期,能不能折中一下?罚他扫一个月茅厕,再给刘娘子赔礼道歉。
”我看了一眼龚运远,这小子倒是会来事。秦将军趁机下台阶:“就按龚兄弟说的办。
李老四,还不滚去扫茅厕!”李老四灰溜溜走了。我摆摆手,民兵们也散了。回去的路上,
龚运远跟在我身后,欲言又止。我头也不回:“有话就说。
”他快走两步跟我并肩:“其实秦将军人不坏,就是好面子。你当着那么多人打他手下,
他脸上挂不住。”我停下脚步:“所以呢?刘寡妇就该被调戏?
”龚运远连连摆手:“不是不是,我是说...有时候不用那么硬来。你看刚才,各退一步,
事情不就解决了?”我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笑了:“你倒是会当和事佬了。
”龚运远挠头:“这不跟你学的嘛,打打杀杀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拍拍他肩膀:“行,
下次你当白脸,我当红脸。”这件事之后,我主动找秦将军谈了谈。
我们达成协议:士兵负责外围巡逻和训练民兵,镇民负责后勤和围墙维护。
每月开一次联席会,有问题一起商量。秦将军带来的消息越来越糟。临兆国已经四分五裂,
北边起了义军,南边有藩王自立,朝廷只剩京城周边还能控制。
发狂的人——现在大家都叫他们“尸人”——已经蔓延到全国。“最可怕的是,
”秦将军压低声音,“有些尸人开始...变异了。”我一惊:“什么意思?
”他面色凝重:“我手下有个斥候,在百里外的黑风山见过一种尸人,速度奇快,能爬墙。
”我倒吸一口凉气。如果真是这样,那围墙也不安全了。当天我就召集所有人开会,
包括秦将军和他的几个副手。“从今天起,围墙加高三尺,墙上插碎瓷片。
晚上巡逻增加一倍人手。”陈师傅提出:“可以在墙外挖壕沟,灌水。”这个建议好,
我立刻采纳。于是全镇男女老少齐上阵,挖沟的挖沟,砌墙的砌墙。
秦将军的士兵也加入进来,干得比谁都卖力。这天挖沟时,我和秦将军站在高处监工。
他突然问:“汪娘子,你这些治军之法,跟谁学的?”我随口说:“自己琢磨的。
”他摇头:“不像。你的排兵布阵,有章法,像是...军中老手。”我心里一紧,
面上不动声色:“秦将军想多了,我就是个普通妇人。”他深深看我一眼,没再追问。
但我能感觉到,他开始怀疑我了。十天后,壕沟挖好了,宽两丈,深一丈。
我们从河里引水灌满,成了护城河。墙上也插满了碎瓷片和竹签。看着加固后的防御工事,
我心里踏实了些。但很快,新的问题来了——粮食真的不够了。虽然开了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