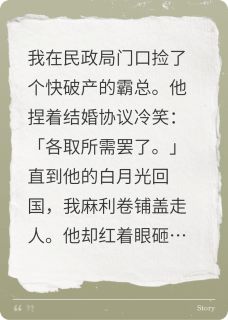我在民政局门口捡了个快破产的霸总。
他捏着结婚协议冷笑:「各取所需罢了。」
直到他的白月光回国,我麻利卷铺盖走人。
他却红着眼砸了整层楼:「谁说这是契约婚姻?」
后来我举着孕检单起诉重婚罪时,
他当庭撕碎假结婚证:「老婆,法律只认事实婚姻。」
*新来的律师助理没认出来,他正是我当年用十块钱买来的合约丈夫。我翻着诉讼材料眼皮直跳:「傅总这案子赢面不大。」他慢条斯理解开袖扣:「要不赌个彩头?」三天后我捂着酸痛的腰踹人:「傅律师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他攥着我脚踝轻笑:「傅太太,重婚罪的追溯期有十年...」
*所有人都等着看「替身」被扫地出门的笑话,傅氏总部却挂出粉色横幅:「恭迎小傅总夫人指挥收购案」而真正的白月光在直播中泣不成声:「当年雇我演戏的钱该结清了!」
民政局门口的冷风跟不要钱似的往我脖子里钻。十月份的天,愣是刮出了数九寒天的气势。我跺着快冻麻的脚,后悔没听我妈的话套上那条丑到爆的加绒秋裤。眼角余光里,一道格格不入的影子杵在旁边——纯黑色羊绒大衣裹着宽肩窄腰,侧脸线条跟刀子削过似的,冷硬,锋锐,沾着点挥之不去的倦。他指间夹着根烟,猩红的火点在风里明明灭灭,衬得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更像个精美的冰雕。
好死不死,糖炒栗子的焦香混着冬夜湿冷的风,狠狠呛了我一口,撕心裂肺的咳嗽在空旷的大理石台阶上格外刺耳。
冰雕动了。烟蒂精准地弹进几步外的垃圾桶。
“咳…咳咳…谢、谢谢啊…”我捂着喉咙,咳得泪花都出来了,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冰雕掀了掀眼皮,黑沉沉的眼珠看向我,不,更像是穿透我,看着后面民政局那锃亮的国徽标志。那眼神空得让人心头发毛。薄唇动了动,声音比深秋的风还冷冽。
“要进去?”
我愣住。这开场白…过于硬核了点。
没等我接话,他像是被什么念头点燃了,带着点孤注一掷的劲头,甚至没给我点头摇头的时间。手腕被他攥住,力气大得惊人,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直接把我拖进了那扇厚重明亮的玻璃门。
里面暖气开得很足,瞬间驱散了外面的严寒,也蒸得我脸颊发烫。排号机的电子女声毫无感情地响着:“请A003号到2号窗口办理。”
手腕上的钳制松开了。他站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那股迫人的气势收敛了些,但周身散发的冷意依旧拒人千里。我揉了揉被他捏得发麻的手腕,抬眼偷偷打量——这男人,太扎眼了。纯黑的大衣里露出的衬衫领口一丝不苟,袖口是颗墨蓝色的宝石袖扣。他刚才攥我的那只手上,戴了枚款式极其简洁的铂金戒指,套在无名指上。
有钱人,失意的有钱人。结合门口那根烟里的死气,这结论呼之欲出。
我们并排坐在办理窗口前的小圆凳上。气氛凝滞得几乎要结冰。对面穿着制服的大姐一脸公式化地问:“双方户口本、身份证带了吗?”
冰雕…哦不,这位从天而降的新郎官,没应声。他直接从西服内袋里掏出一个极薄的文件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抽出一式两份打印好的文件,推到钢化玻璃下方的传递口。
白纸黑字,标题加粗——《婚前协议》。
大姐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梭巡,带着点儿不易察觉的同情和了然。我吸了口冷气,强迫自己凑过去看。协议比我想象的简洁得多,核心内容炸得我脑仁嗡嗡响。
甲方(男方)傅沉洲。
乙方(女方)……名字空着,显然在等我填。
协议第一条:婚姻存续期暂定一年。一年期满,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离婚手续。
第二条:甲方支付乙方酬劳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婚前一次性支付)。
第三条:在婚姻存续期间,乙方需严格履行妻子对外职责,配合甲方应对家族、商业所需;不得泄露协议内容;不得干涉甲方任何私人事务。
……
最后加了一条:甲方对乙方无任何实质性婚姻义务要求,反之亦然。双方保持绝对身体距离和财产界限。
我的指尖碰到冰凉光滑的纸页,心脏像被那行“壹仟万元整”的字烫得猛地一跳。冷静,苏禾!天上掉的不是馅饼,是包着糖衣的核弹!这男人快破产了吧?否则怎么会需要找个陌生人形婚?领完证立刻要求支付一千万,协议里可写着婚前支付!他账户要是冻结了,或者干脆反悔赖账……
傅沉洲仿佛会读心。他侧过头,那张过分好看却冰冷的脸凑近了些,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眼瞳里倒映出的、我自己那点惊惶又警惕的蠢样子。他嘴角扯起一个极浅的弧度,不是笑,是淬了冰的嘲讽。
“账没问题。”低沉的声音擦过耳边,带着砂砾般的质感,“签了字,钱立刻转到你名下的干净账户。或者…”他顿了顿,目光像手术刀一样刮过我的脸,“怕了?不敢赌了?”
被戳中心事的慌乱和被轻视的羞恼同时涌上来。“我苏禾字典里没‘怕’字!”我梗着脖子,声音因为激动有点变调,“签字前我得问清楚!”
他重新靠回椅背,双手随意交叠放在腿上,一副耐心告罄但勉强施舍给我说话机会的冷淡样。
“傅先生,您这协议看着就像急着签个‘有法律效应的长期家政工’,”我指了指协议第七条,“‘乙方需每日与甲方父母共进早餐’?还有第十条‘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换甲方指定的私人医生团队’?”我深吸一口气,目光迎上他深不见底的黑眸,“我查过你。傅家。盘根错节的大家族。你找契约妻子应急可以理解。但这附加条件…傅先生,您不是单纯的破产危机吧?这场戏里,我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危险系数有点高?”
空气凝固了。他交叠的手指微微一动,指尖在膝盖上轻点了一下。冰封的面容终于裂开一丝缝隙,眼神里沉淀的墨色剧烈地搅动翻涌,一丝压抑到极致的疲惫和更深沉的东西倾泻出来,快得像是错觉。他薄唇抿成一条没有情绪的直线,没有立即回答。
窗口里的大姐轻咳一声:“材料放好了。户口本、身份证、照片,新人准备一下签字。”
傅沉洲收回了目光,再次落在面前那份空白的乙方落款处,语调回归那彻底的冰冷,毫无波澜:“机会只有一次。签,或者不签。我的时间有限。”他掏出万宝龙镶铂金边的钢笔,旋开笔帽,动作优雅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感,在甲方栏签下名字——“傅沉洲”。三个字龙飞凤舞,却又力透纸背。
我死死盯着那签名。脑子里两个小人疯狂拉扯。一个尖叫着:一千万!一千万!签了它立刻变身富婆!逃离那窒息的原生家庭!债务压力瞬间清零!另一个小人悲鸣: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傅沉洲这潭水深不见底,沾上了还能全身而退吗?那协议里的“危险系数”,绝非空穴来风!
万宝龙钢笔的笔尖悬停在乙方的空白处,冷硬的不锈钢笔尖在窗口惨白的灯光下反着瘆人的冷光。
签?还是不签?
窗口大姐的手指开始无意义地敲击键盘,发出“嗒嗒”的声响,这细微的催促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喉头滚动了一下,口腔里干涩得像塞满了沙子。一千万。足以斩断身后那个家如同跗骨之蛆般的吸血鬼,彻底堵住那群人贪婪的叫嚣。管它是不是深渊,至少现在,我需要这张……带血的通行证。
“给我!”声音有些劈叉,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钢笔。金属笔杆握在掌心冰凉刺骨,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我几乎是恶狠狠地在那空白处划拉上我的名字——苏禾。潦草又用力,最后一笔长长拖出去,差点划破纸张。
傅沉洲眼底极快地掠过一丝东西,快得捕捉不到,又或许只是我眼花了。他拿出手机,解锁,屏幕的光映着他没有丝毫温度的眼,指尖在屏幕上快速点动,动作行云流水。几秒后,我那个八百年没响过除了催债短信之外任何东西的破手机,在口袋里狠狠震动了一下。
我掏出来,冰冷的塑料外壳沾了点汗意。屏幕亮起,是一条崭新的银行入账通知,那一串长得像天文数字的零,看得我眼球发胀,心脏跳得擂鼓一般。
钢印“咚咚”两声,沉闷地砸下来,落在两个贴着照片的红本本上。照片是十分钟前现照的,我和傅沉洲肩并肩站在民政局那个脏兮兮的红布前。他比我高出大半个头,侧脸线条紧绷着,下巴微扬。我呢?穿着件皱巴巴的米色毛衣,笑得比哭还难看,眼底的慌张藏都藏不住。这张照片,凝固了我此刻全部的局促不安和不真实的眩晕。
揣着那两本刚出炉、还散发着纸张和油墨新鲜气息的红本子,我站在民政局门口被冷风一吹,激灵灵打了个哆嗦。周围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喧嚣的车流,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荒谬。真的结婚了?和一个名字在财经板块和八卦头条里都属于传说级的人物?用法律和一张薄纸绑在了一起?心脏后知后觉地疯狂撞击着肋骨,手心全是黏腻的冷汗。
傅沉洲就站在我前面一步的距离,背影挺拔孤绝,像一尊亘古不化的冰山。他没有回头看我,声音在喧嚣的风声车流里几乎被吹散,但那股子冰渣子的质感依然清晰:“钱收到了?”
“…嗯。”我攥紧了手里的红本本,声音闷在喉咙里。本子的尖角硌得掌心有点疼。这真实的触感提醒我,那不是梦。
“那就好。”他语气平淡,像是在确认一笔无关紧要的货款是否交割成功,“林秘书一会儿开车送你回……”
他的话像被按了暂停键,戛然而止。
我的目光循着他骤然锐利起来的视线望去。
几米开外,花坛边,站着一个女人。
白色的长款羊绒大衣被风吹得衣角翻飞,像只伶仃又惹人怜惜的蝴蝶。微卷的栗色长发柔软地搭在肩头,巴掌大的小脸,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唇色是带着点羸弱的粉。她正微微侧着头,望着……民政局门口巨大的LOGO牌,那眼神复杂极了,迷茫,难以置信,还有一种被全世界背叛了的脆弱空茫。
林薇。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个名字像被淬了毒的针,狠狠扎了我一下。傅沉洲的初恋,他放在心尖尖上整个青春时代、据说远在国外求学的…白月光。她怎么会在这里?现在?!这个时间点?!
傅沉洲挺拔的身躯瞬间僵硬得如同一块钢板。方才周身那股生人勿近的冷气,此刻凝成了肉眼可见的寒冰风暴。他甚至连呼吸都停滞了,瞳孔猛地收缩,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情绪——震惊,愤怒,一种被猝不及防狠狠刺伤的、难以置信的痛楚。
林薇像是感知到了,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来。她的视线先落在傅沉洲脸上,那眼神里的破碎感像被打碎了最珍爱的水晶。然后,她的目光滑落,定在了我手上。
我下意识地想把手里的红本子往身后藏,这动作近乎本能,可我的胳膊像被冻住了一样沉重僵硬。那两个鲜红的、刺眼的小本子,无所遁形地暴露在她的视线里。
她没看我。她的目光穿透了我,死死地锁住傅沉洲。泪水毫无征兆,如同断线的珍珠,大颗大颗地从她通红的眼眶里滚落,砸在她白色大衣的衣襟上,洇开深色的湿痕。没有任何哭喊和质问,她只是死死盯着他,仿佛要用目光在他身上剜出一个洞来,泪水无声流淌,那份绝望的控诉比任何歇斯底里都更具冲击力。
下一瞬,她猛地一拧身,纤细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决绝地朝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冲去!
“薇薇——!”
那一声嘶吼仿佛带着血丝,炸响在我耳边,是傅沉洲!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像困兽濒死般的绝望和恐惧。他甚至忘了我的存在,在我身边猛地刮起一阵风——他像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
黑色羊绒大衣的下摆像搏杀时的猎豹张开的皮裘,狂卷着凛冽的杀气。他朝着那个白色的、不顾一切扑向死亡车流的身影追去。
刺耳的、几乎撕裂耳膜的刹车声!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地狱般的尖啸!一辆黑色轿车带着骇人的气势猛地横插过来,精准地、带着玉石俱焚般的狠戾,斜挡在即将冲到路中间的白影前方!车门砰地弹开。
傅沉洲的身影消失在那个半开的车门后。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我像个被施了定身法的傻子,僵硬地站在原地,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两个崭新的红本。刚才那震耳欲聋的刹车声和傅沉洲最后那声撕心裂肺的“薇薇”还在耳膜里嗡嗡作响。
一阵冷风卷着枯叶砸在我脸上。
手里,被塑料封皮包裹着的红色结婚证,一角磕在我冰凉的手指骨节上。
又冷。
又硬。
口袋里,那台廉价智能手机忽然又震动了一下,沉闷而规律。我木然地掏出来,屏幕还停留在那个银行到账短信的界面,上面那一连串足以彻底改变我底层人生的零,在暮色四合的光线下,显得毫无温度,甚至……有些讽刺。
手机还在震。不是短信。
是一条微博推送。
冰冷的字体弹出来,每一个字都像带着倒刺的冰锥——
#突发!傅氏集团总裁傅沉洲现身民政局,疑与神秘女闪婚!身侧娇妻清丽可人,疑似傅氏集团破产危机下的联姻之举?傅沉洲深爱多年的白月光林薇又该何去何从?[爆][沸][热]
下面是几张高糊却依旧能辨认主角轮廓的照片。第一张,他攥着我的手腕拖我进民政局的背影;第二张,我们并肩坐在窗口前等待的侧影(我的毛衣皱得更加明显了);第三张……是他冲出去追林薇,而我像个被遗弃的道具,拿着两本红本傻傻站在原地的定格。
推送还在疯狂弹消息。
热搜榜以惊人的速度刷新着——
#傅沉洲闪婚#
#白月光回国即遇晴天霹雳#
#傅氏集团破产联姻疑云#
#林薇心痛离场#
无数网友的评论、转发、爆料如同雪崩,瞬间淹没了小小的手机屏幕。铺天盖地的质疑、嘲讽、同情、猎奇,像巨大的海啸,透过冰冷的屏幕,将我脚下这片仅存的水泥地也彻底淹没。
手里那两本鲜红的结婚证,硌得指骨生疼。
我缓缓地、缓缓地抬起头。
暮色彻底笼罩下来。不远处那辆突兀停在路中间、嚣张地挡住了半条车道的黑色轿车,依旧静静地停在原地。车门紧闭,车窗贴了深色的防窥膜,像隔绝一切的堡垒。我看不到里面一丝一毫的光景。不知道那个叫林薇的女人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刚刚和我签下一年之约、给了我一千万的傅沉洲,此刻在里面是什么表情。
傅沉洲没回来。自始至终,那扇贴着深色膜的车门,再也没有打开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新的推送——
@圈内人爆料:最新消息!林薇**情绪崩溃被送医,傅沉洲全程陪护!民政局门口神秘“闪婚妻”独守寒风![新]
冷风卷着沙尘迷了我的眼。我用力眨掉那点涩意,把那两本烫手的结婚证塞进帆布包里最深的角落,硌着包里刚签完的婚前协议文件袋。
就在我抬脚准备走向最近的地铁站,彻底离开这片冰冷的战场时——
一辆纯黑色的、线条冷硬如刀的劳斯莱斯幻影,像无声的幽灵,碾过满地枯叶,稳稳地停在我面前。车窗无声下降,露出一张严肃刻板的中年男人的脸。他穿着笔挺的深灰色西装,眼神锐利。
“苏禾**,”声音平板无波,带着绝对的公式化,“我是周特助。傅总交待,送您回华庭。”他顿了顿,没有给我任何拒绝的余地,补充道,“夫人交待,请您务必回家。”
夫人?
傅沉洲的母亲?协议里那个需要我“每日共进早餐”的对象?
那辆黑色轿车的阴影仿佛还在眼前。手机里关于“白月光送医”、“神秘妻被弃”的爆料还在无声滚动发酵。
回华庭?
去那个……即将迎来腥风血雨的傅家大宅?
车门锁咔哒一声轻响,已经自动弹开。
冰冷的、皮革和顶级香薰混合的气息,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从车内弥漫出来。
周特助开的车又快又稳,车厢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嚣,只剩下顶级音响里流淌出来的几不可闻的巴赫。没人说话。**在后排冰冷的真皮座椅上,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被五光十色霓虹切割的陌生城市,大脑一片混沌。
手里的帆布包像个炸弹,里面装着一千万的烫手山芋和两本足以让我卷入顶级旋涡的结婚证。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林薇最后那破碎的眼神和傅沉洲失控嘶吼的样子。手机屏幕无声熄灭,沉甸甸地躺在腿上,但那推送带来的冰冷寒意已经扎进了骨头缝里。这算什么?刚上岗就面临地狱难度?
车子滑入一片被茂密乔木环绕的低密度区域,空气都陡然安静下来。华庭到了。
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一座袖珍的皇家园林。厚重的铁艺大门无声洞开,车子驶过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和姿态各异的罗汉松,最终停在一栋灯火通明的欧式主宅前。廊柱高耸,灯火辉煌得甚至有点刺眼。
周特助下车为我拉开车门,引着我往里走。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吊灯,晃得人有些眼晕。空气里有淡淡的花香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一种陈旧木头和权势沉淀下来特有的冰冷气息。
客厅极大,沙发是厚重的米白色欧式古典款。壁炉没有生火,旁边放着一张铺着柔软毛毯的单人躺椅。
一位穿着香奈儿经典斜纹软呢套裙、身形优雅的中年妇人正靠坐在主位的沙发里。花白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典雅的髻。她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瓷杯,杯壁很薄,更显得她指节修长。傅沉洲的轮廓有五六分像她,只是她的线条更柔和,也……更冷。
周特助微微躬身:“夫人,苏**到了。”
傅夫人闻声,慢条斯理地抬起眼。那是一双和傅沉洲极其相似的眼睛,深邃、沉静,像结冰的湖水,只是少了傅沉洲的那种锐利和压抑的灼热,里面沉淀的是一种洞悉世情、无悲无喜的审视。目光落在我身上,如同冰凉的绸缎滑过皮肤。没有任何温度,只有精准的衡量。
她没说话。手里的茶杯轻轻放回了描金的骨瓷托盘里,发出极细微的一声“叮”。
坐在她对面的女人却飞快地转过头。那是个打扮得相当用力的贵妇,深紫色的丝绒套装,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坠子几乎有鸽子蛋那么大,晃眼得很。她的视线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身上来回扫射了几遍,随即夸张地用手捂住了嘴,惊讶都透着一股子刻意的味道:“哎呀!这就是那个……那个苏**?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清汤寡水……啊不,是清秀,真清秀!我们沉洲这次可真是……眼光独特!”
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刺,裹着糖衣的毒针。
傅夫人没接她的话,眼皮都没抬一下,但那冰湖似的目光却让贵妇讪讪地收敛了笑意。
“周管家。”傅夫人开口,声音不高,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从容和微冷,“带苏**去她的房间。收拾妥当,再过来陪我喝点茶。”
“是,夫人。”一位穿着黑色管家制服、头发花白但身姿笔挺的老者无声无息地出现,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跟在他身后,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步子发虚。那位贵妇探究的、带着轻蔑的目光,如同黏在脊背上的蛇,令人极度不适。转角处,依稀还能听到那贵妇刻意压低却丝毫不低的“惋惜”:“大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放着好好的薇薇不要,临门一脚……哎,现在可好了!虽说为了集团,什么手段都得用……但这娶回来的……”后面的话被拐角吞没了,但那语调里的鄙夷,清晰得像是刻在了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