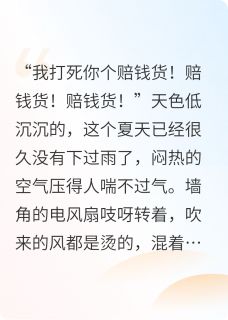蝴蝶不怕飞不过群山,因为有星星指路。七岁的星星每天只有一个愿望,和妈妈好好活下去。
1“我打死你个赔钱货!赔钱货!赔钱货!”天色低沉沉的,
这个夏天已经很久没有下过雨了,闷热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墙角的电风扇吱呀转着,
吹来的风都是烫的,混着父亲身上浓烈的酒气,在逼仄的房间里发酵成更令人窒息的味道。
比起闷热的空气,父亲在外面的谩骂更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我紧绷的神经。
我努力缩在衣柜的角落里,后背紧紧贴着冰冷的木板,试图从那点凉意中汲取一丝力气。
衣柜里堆满了母亲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带着皂角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这是此刻唯一能让我稍感安心的气息。耳边是玻璃碎裂声,清脆的“哐当”声接二连三,
像是有人在敲碎这个家最后一点支撑;还有母亲压抑的啜泣,像漏了气的风箱,
一声比一声微弱。父亲醉醺醺的咒骂穿透门板,
每一个字都像石子砸在我心上:“胡小蝶你这个赔钱货!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当初就不该留了你……那卖豆腐陈嫂子早就给他家添了儿子,人家现在多风光,哪像你,
只会赔钱!”我听着那些谩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叫嚣:冲出去,
快出去,去保护她,去啊!可身体像被钉在原地,恐惧像藤蔓缠住了我的四肢。我才七岁,
我能做什么呢?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柜门突然被打开一条缝,
一个缺了口的粗瓷碗“啪”地砸在脚边,瓷片溅到我的小腿上,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紧接着,
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用力将柜门重新关上,锁扣“咔哒”一声扣上,黑暗瞬间将我吞噬。
我吓得浑身一抖,手中的蜡笔被紧紧攥住,硌得手心生疼。在恐惧中,
我摸索着柜门内侧粗糙的木板,想起母亲温柔的话。她说:“星星,蝴蝶都是在茧里长大的,
等长大了,就能冲破茧,飞到天上去了。”我颤抖着抬手,
用蜡笔在门板上画下一只振翅的蝴蝶。蜡笔是母亲捡来的,只剩一小截,
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可在我眼里,这只蝴蝶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即使闷热的环境、缺氧的空间令人窒息,可这衣柜也是我最后的庇护港了。
是稚嫩蝴蝶的硬茧,保护我这弱小的身躯。“星星,快跑!”突然,衣柜门被猛地踹开,
刺眼的白光瞬间涌了进来,晃得我睁不开眼。一双带着浓重酒气的手伸了进来,
像抓小鸡一样将里面蜷缩的我扯了出来。我重重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到桌角,眼前一阵发黑。
“你别碰她!”母亲发了狠,像一头被激怒的母兽,猛地撞开男人,将我护进怀里。
她的怀抱很瘦小,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巴掌像雨点一样落下,
“啪啪”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落在母亲并不宽阔的肩膀上。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可她抱我的力气却越来越大。我害怕得发抖,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她的双手也在颤抖,却很用力地抱紧我,
我手中的蜡笔蹭到她的衣服上,留下一道歪歪扭扭的彩色痕迹。我死死咬着嘴唇,
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我怕我的哭声会让父亲更生气。……“别打妈妈,
别打了,别打妈妈。”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尖叫着哭喊,声音嘶哑得不像样子。
我的求饶没有换来一丝的怜悯,父亲的打骂反而更凶了。寂静的夜里,
这座破落的单元楼里传出的惨叫声飘了很远很远,穿过狭窄的巷子,越过低矮的屋顶,
却怎么也飘不出这重重叠叠的大山去。窗户外,星星点点的灯火,那是别人家的温暖,
却不是我的灯塔。我看着那些摇曳的光,突然觉得自己像迷失在茫茫大山里的一只小虫,
找不到回家的路。哭了太久,声音逐渐嘶哑,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疼。
我这时才彻底冷静下来,看着眼前的男人。他是我的父亲,可此刻却那样陌生。
他通红的眼睛里满是暴戾,嘴角挂着狰狞的笑,好像是一只没有人性的野兽,
看到了猎物垂死的挣扎,却变得更加兴奋。我闭上眼,
心里的火焰要烧干这具单薄瘦弱的躯体。在血与泪的缝隙里,我一遍遍描绘着男人的轮廓,
那轮廓在心里无比清晰,又渐渐模糊。我知道,有些东西,从这一刻起,已经碎了。
2“新鲜的豆腐,卤水豆腐……”清晨五点,菜市场还弥漫着潮湿的水汽,
卖豆腐的陈嫂尖利的吆喝声像一根针,把我从混沌的睡眠中扎醒。
仿佛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可身上隐隐的酸痛提醒我,现实比噩梦更沉重。
我蹲在菜市场角落的小板凳上剥毛豆,一盆毛豆堆得像座小山。
指尖被豆荚边缘划开了好几道细小的口子,渗着血丝,泡在浑浊的水里,一阵阵刺痒。
母亲说,多剥点毛豆,中午可以煮一盘,给我补补身子。母亲在不远处摆摊卖鱼,
腥气顺着风钻进鼻腔,混着隔壁猪肉摊的苍蝇嗡嗡声,构成了我生活的背景音。
“听说老林家的丫头数学考了年级第一?”卖豆腐的胖婶陈嫂嗓门尖利,
她一边用抹布擦着案板,一边有意无意地朝我们这边瞥,“可惜是个女娃,
读再多书最后也是别人家的。不像我家小子,将来可是要顶门立户的。”说完,
她眼神不屑地扫过我们,从鼻子里哼了口气,那声音里的轻蔑像冰锥一样扎人。
母亲杀鱼的手顿了顿,一把锋利的刀悬在半空中。我瞥见她袖口滑落,
露出一块铜钱大的淤青,青紫色在她蜡黄的皮肤上格外刺眼。她怔了半晌,嘴唇嗫嚅着,
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低下头,继续处理手里的鱼,刀刃划过鱼鳞的声音“沙沙”作响。
一直忙到夜半,菜市场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零星几个收摊的小贩。我陪着母亲收拾东西,
破旧的三轮车被各种杂物堆得满满当当。路灯的灯光寥落地洒在地上,
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听见了她的声音,因为一天的沉默而有些沙哑,
粗哑的嗓音并不好听,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她说:“星星,弱德不是弱者,
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那不是弱德。弱德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持守,
是在重大的不幸遭遇之下,负担承受并且要完成自己的一种力量。”我抬头看着她,
路灯的光勾勒出她消瘦的轮廓,鬓角有几缕白发被风吹得飘动。这么些年,
每次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会同我语重心长地说这些话。路灯照在她瘦弱的身躯上,
却在身后留下了厚重的身影,像一座沉默的山。“星星,你不该留在这里,去天边,
高高亮起来。”她粗粝的大手包裹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有很多裂口,像干涸的土地,
可掌心的温度却很暖。灯光拉长了我们的影子,紧紧依偎在一起。深夜,
我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在旧挂历背面画下胖婶扭曲的嘴。
挂历是去年的,上面的日期已经模糊不清,纸页脆得像枯叶。
我想把那些刻薄的嘴脸都画下来,然后用力撕掉。突然,桌子被猛地掀翻,“哐当”一声,
桌上的空碗摔在地上碎了。“电费不要钱啊?大半夜不睡觉瞎折腾什么!
”醉醺醺的男人闯了进来,眼睛通红,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挂历,撕得粉碎。
纸片像蝴蝶一样飞散,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却漏了一片飘进床底的——上面有只被撕去半边翅膀的蝴蝶,那是我下午偷偷画的。
疼痛如雨点一样落在身上,**辣的,从后背蔓延到四肢。我咬紧牙关,憋住不出声,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乖一点,母亲可能就免受牵连。
只是心里的火焰已然要将这副躯体燃尽,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屋子里终于没有了声音,
只有我沉重的喘息。身上的疼痛告诉我这不是一场梦。过了不知多久,
门外传来吱嘎的开门声,是母亲收摊回来了。随后,谩骂声、打砸声又响了起来。
我再也忍不住,不顾一切地冲出门,扑在母亲的怀里。原来退让和沉默只能助长恶的火焰,
让它烧得更旺。他发了一顿邪火,终于累了,回屋子里躺下了,鼾声如雷,
震得屋顶的灰尘都要掉下来。满地的狼藉中,我摸过旁边破碎的瓷片,
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传来。我攥紧瓷片,锋利的边缘割破了手心,鲜血渗了出来,
我却感觉不到疼。我红着眼看向屋子里那个熟睡的身影,心里有个疯狂的念头在滋生。
“星星,别……”母亲按住我的手,她的手也在抖,一点点掰开我的手指,夺下了那片瓷片。
一直以来如此倔强坚强的母亲,此刻落下了泪,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滚烫。“不值得,
他不值得你搭进去……我们还有希望,星星,我们还有希望。”3美术课上,
四周响着笔尖接触纸张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
照出空气中飞舞的细小尘埃。新来的美术老师李璐在班里巡视,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
和这个灰暗的小镇格格不入。她的脚步声很轻,在我面前止住了。接着,
我听到一声倒吸的凉气声。她捏着我的速写本,先是震惊,眼睛睁得大大的,
随后又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是你画的?没有人教你?”她翻了几页,语气越发激动,
“有天赋!真是个好苗子!”画纸上是菜市场众生相:鱼鳃翕动的死鱼眼睛,
浑浊的眼珠里映出天空的一角;案板上神经未死的蛙腿,
还在微微抽搐;母亲龟裂手指间的毛豆绿壳,沾着泥土和水渍。
每一笔都带着我对生活最真实的感受。我张了张嘴,想说说些什么,
想说我每天都在菜市场里看这些,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沉默地低下头。
“你愿意接受系统的学习吗?”李老师的声音带着期待,“我可以给你课后辅导,不收钱的。
说不定你能是这个小镇上第一个考上美院的学生。”我沉默着,头垂得更低了。
垂眸看向手里的画纸,那是本翻旧的台历,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我想让她帮我,
或许她真的可以帮我呢?可是这么多年,母亲试过反抗,我也偷偷哭过闹过,
可最后都失败了。这座大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我们能逃得出去吗?两滴泪水落在本子上,
晕染了画上那纷乱的菜市场,墨迹像藤蔓一样散开。我悄悄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谢谢老师,不用了……”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连我自己都听不清。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门前那条浑浊的小河,缓缓流淌,没有波澜。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十八岁了。录取通知书来的那晚,红色的信封像一团火,
烫得我手心发疼。我不敢让父亲看到,偷偷将它藏在屋子角落的墙缝里,
用一块松动的砖挡住。可还是被他发现了。父亲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地闯进我的房间,
一眼就看到了我藏信时露出的一角。他一把抢过信封,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
然后把烟头摁在我的画册上:“陈家给了五万彩礼,下个月就让你嫁过去。读什么狗屁大学,
女孩子家,早点嫁人换点钱才是正经事。”火苗窜起时,画纸卷曲着,烧成了灰蝴蝶,
在空中打了个旋,然后落下来。画册烧得支离破碎,那些我画了无数个日夜的画,
那些承载着我梦想的纸页,就这样化为灰烬。母亲疯了一样冲过来,拼命伸手扑灭火焰,
双手被烧伤了也不管。她将残破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铁盒里,
盒里还有一张褪色的照片,那是我小时候在衣柜门上画的蜡笔蝴蝶,母亲偷**下来保存着。
“星星不是别人生养的工具,她要去上学,她是……”母亲的话如此洪亮,这十八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