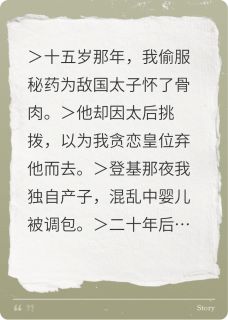>十五岁那年,我偷服秘药为敌国太子怀了骨肉。>他却因太后挑拨,
以为我贪恋皇位弃他而去。>登基那夜我独自产子,混乱中婴儿被调包。>二十年后,
我的养子诬陷侯府世子谋逆。>廷杖落下衣襟撕裂,那火焰胎记灼痛我眼——>是我亲儿。
>他不知身份,正为护着敌国质子与我针锋相对。>像极当年为他父亲对抗全世界的我。
---早春的寒气在朱红宫墙内凝结,沉甸甸地压在飞檐斗拱之上,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
卫国皇宫的御书房里,龙涎香的清冽也驱不散这无形的滞重。
刘瑾的目光长久地凝固在御案一角,那里躺着一份来自南岳边境的紧急军报。墨字冰冷,
条陈着南岳新君萧子染登基后的厉兵秣马,字字句句,都似淬了北地寒冰的针,
扎进他心底最深处那个从未结痂的旧创口。他搁下朱笔,
指尖无意识地抚过袖中暗袋里那方早已失去光泽的旧剑穗。粗糙的丝线纹理磨着指腹,
带来一点微不足道的刺痛,却奇异地让那颗被冰封了二十年的心,泛起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
二十年前,也是这般乍暖还寒的时节。十五岁的少年皇子,情窦初开,炽烈如火,
一头撞进了那个南岳质子萧子染织就的温柔陷阱里。情到浓时,懵懂又疯狂,
竟不知从何处寻来那传说中的“逆天石”,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只为能与心上人,
真正骨血相融。逆天石……刘瑾闭上眼,指尖深深掐入掌心。
那东西带来的何止是逆转阴阳、男子生子的奇诡?更有每月一次的剜骨之痛,
如同阴魂不散的诅咒,日日夜夜啃噬着他的脏腑。每一次绞痛发作,冷汗浸透龙袍,
他都死死咬住牙关,将那破碎的**尽数咽回腹中。无人知晓这九五之尊的龙袍之下,
裹着怎样一副被秘药日夜折磨的残躯。这秘密,连同那个未能宣之于口的孩子,
是他龙椅之下最深的基石,亦是心头最毒的荆棘。他忘不了那场撕心裂肺的分娩。
就在他踩着政敌尸骨,终于戴上那顶染血帝冠的登基大典前夜。没有稳婆,没有太医,
只有忠心却同样惊惶的老内侍福安守在偏殿外。剧烈的宫缩如同无形的巨锤,
一次次凶狠地砸断他的脊骨。他蜷在冰冷的金砖地上,牙齿死死咬住塞入口中的软木,
汗如雨下,眼前阵阵发黑。血水浸透了身下厚厚的锦褥,腥甜的气味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在意识沉入黑暗深渊的前一刹,他依稀听到了婴儿微弱如猫崽的啼哭。紧接着,
便是周太后猝然薨逝带来的惊天混乱。整个皇宫乱作一团,灵幡白幔遮天蔽日。
就在那片混乱里,他的孩子……他拼却性命生下的骨肉,如同投入沸水的一点雪沫,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福安只来得及带回一个冰冷的死婴,说是“皇子早夭”。那一刻,
刘瑾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那小小的躯体一起僵冷、碎裂。他抱着那毫无生息的小小襁褓,
枯坐一夜,泪早已流干,只剩下无边无际、能将灵魂都冻毙的寒意。后来,他不动声色地查。
蛛丝马迹最终指向了当夜同样在宫中待产、却因劳累奔波而早产的太后侄女,
威远侯夫人小周氏。混乱之中,婴儿被调换。他的亲生骨肉,
竟被小周氏当作亲子抱回了侯府,成了名正言顺的威远侯世子周临渊。
而小周氏自己那苦命的孩子,则被有心人趁乱裹挟出宫,弃于荒野,幸而被云游的神医所救。
至于那个被换到他怀中的死婴……刘瑾眼中寒光一闪,当年的太医令,早已“病故”多年了。
二十年来,他守着这滔天的秘密,守着这冰冷的龙椅,
守着对萧子染那早已被鲜血和权谋浸透的、无法言说的执念。后宫形同虚设,
他广纳宗室子弟为养子,只为堵住悠悠众口。其中,尤以齐王世子刘珏最为出挑,
也……最为野心勃勃。“陛下,”大太监福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廷尉府急奏,齐王殿下……在宫外长街遇刺!”刘瑾猛地睁开眼,
方才眼中的一丝恍惚瞬间被帝王的锐利取代,寒芒刺骨:“说下去!
”“刺客……刺客身上搜出了威远侯府的令牌!”福安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沉甸甸的份量。
威远侯府……周临渊!一股难以言喻的躁动猛地撞上刘瑾的心口,又被他强行按捺下去。
他霍然起身,玄色龙袍带起一阵冷风:“传旨!宣威远侯世子周临渊,即刻入宫见驾!
朕要亲自审问!”声音低沉,却蕴含着雷霆万钧之力,震得殿内空气嗡嗡作响。
那压抑了二十年的寻觅与渴望,此刻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谋逆”罪名骤然点燃,
带着玉石俱焚般的灼热。沉重的宫门在周临渊身后缓缓合拢,发出“哐当”一声闷响,
隔绝了外界的光线,也将一种无形的威压彻底笼罩下来。引路的内侍提着灯笼,
昏黄的光晕在深长的宫道上跳跃,映照着两侧高耸的宫墙,投下巨大而扭曲的阴影,
如同蛰伏的巨兽,随时会扑噬而来。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木料、尘土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皇权的冰冷气息,沉甸甸地压在肩头。
周临渊的背脊挺得笔直,如同雪地里一杆宁折不弯的青竹。他心中惊涛翻涌。齐王刘珏遇刺,
竟从他侯府侍卫身上搜出令牌?这栽赃的手法拙劣得可笑,却因涉及天家贵胄,
瞬间变得致命。更令他心头一紧的是,事发之时,燕离恰好在他府上!
那位寄居侯府、身份敏感的庆国质子……周临渊的指节在宽袖下悄然攥紧,
指甲几乎陷进掌心。踏入宣政殿的瞬间,肃杀之气扑面而来。殿内灯火通明,
却驱不散那股森冷。御座高踞丹陛之上,卫帝刘瑾端坐其中,
玄色龙袍上的金线在灯下反射出冷硬的光泽。他并未戴冠,墨发以一根简单的玉簪束起,
面容在明暗交错的光影里显得异常深刻,也异常冰冷。那双眼睛,如同两口封冻千年的寒潭,
目光扫过殿中跪着的周临渊,没有一丝温度,只有审视与无形的重压。“威远侯世子周临渊,
”刘瑾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大殿每一个角落,带着金石相击般的冷硬,“齐王遇刺,
刺客身携你侯府令牌。你有何话说?”“陛下明鉴!”周临渊叩首,声音清朗,
竭力维持着镇定,“臣府中令牌管理虽有疏漏,但刺杀齐王殿下这等滔天大罪,
绝非臣与侯府所为!此乃奸人构陷,欲借刀杀人,离间天家与勋贵!臣恳请陛下彻查!
”“构陷?”刘瑾唇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似笑非笑,眼神却锐利如刀,
仿佛要剖开周临渊的皮囊,直刺他灵魂深处,“证据确凿,一句‘构陷’就想撇清?朕听闻,
事发之时,庆国质子燕离,正在你府上?”他目光一转,
如同冰锥般刺向跪在周临渊侧后方的那个清瘦身影。燕离一身素净的青衣,
在这煌煌大殿中显得格格不入的卑微。他深深伏地,
声音带着质子特有的、被磨平了棱角的恭顺:“回陛下,小人当时确在世子书房请教棋艺。
世子清誉,小人愿以性命担保,断与此事无关。”他微微抬起脸,
露出苍白却难掩清俊的轮廓,眼神沉静,不卑不亢。“担保?”刘瑾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讥诮,“一个敌国质子,自身难保,拿什么担保?”他猛地一拍御案,
震得笔架砚台嗡嗡作响,“周临渊!你私交敌国质子,本已犯忌!如今更牵涉谋刺亲王!
你眼中可还有王法,可还有朕?!”“陛下!”周临渊霍然抬头,
直视着那双深不见底的帝王之眼,胸膛因激愤而剧烈起伏,“燕质子入卫为质,
乃两国邦交之约!臣与之相交,不过君子论道,切磋学问,何来‘私交敌国’之说?
陛下以此定臣之罪,臣……不服!”他眼中是年轻气盛的倔强,
像一头被逼入绝境却不肯低头的幼兽。“不服?”刘瑾缓缓站起身,一步一步走下丹陛。
玄黑龙袍的下摆拖过光洁的金砖,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如同毒蛇游过地面。
那无形的压迫感随着他的脚步层层逼近,几乎令人窒息。他停在周临渊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眼神幽暗难测,“好一个铁骨铮铮的威远侯世子!朕倒要看看,
你的骨头,是否真如你的嘴这般硬!”他冰冷的目光扫过周临渊倔强的脸,
转向殿侧肃立的金吾卫,声音冷酷如铁:“威远侯世子周临渊,御前失仪,顶撞君上,
藐视国法!拖下去——”“杖三十!”“陛下!”燕离失声惊呼,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陛下息怒!”几位老臣也慌忙出列劝阻。刘瑾却置若罔闻,眼神如同凝固的寒冰,
只死死锁在周临渊身上。两个身材魁梧如铁塔般的金吾卫校尉已如狼似虎地扑上,
一左一右钳住了周临渊的手臂,粗暴地将他向外拖拽。周临渊没有挣扎,只是猛地扭过头,
目光越过如狼似虎的侍卫,
地投向御座之旁、那个一直垂手侍立、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冷笑的年轻亲王——齐王刘珏!
那眼神锐利如电,带着无声的控诉和凛然的寒意。刘珏接触到这目光,唇角的笑意微微一僵,
随即化为更深沉的阴鸷,微微侧过头,避开了那锋芒。殿外空旷的庭院里,
春日稀薄的阳光无力地洒落。冰冷的刑凳早已备好。周临渊被死死按在硬木之上,
粗糙的木纹硌着腹部。厚实的廷杖带着沉闷的风声,狠狠砸落!“一!”“二!
”沉闷的杖击声在空旷的宫苑内回荡,每一下都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殿内殿外所有人的心上。
燕离被死死按在殿内,只能听到那一声声钝响,如同敲在朽木之上,
却又带着筋骨碎裂的恐怖质感。他脸色惨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几乎要刺出血来。
御座上的刘瑾,面沉如水,宽大的龙袍袖口内,指骨已因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唯有那双眼,
如同淬了火的寒冰,死死钉在殿外那个受刑的身影上,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廷杖无情地起落,发出令人心悸的“噗、噗”声。周临渊紧咬着牙关,额上青筋暴起,
冷汗瞬间浸透了里衣,黏腻地贴在背上。剧痛如同烧红的烙铁,反复熨烫着他的腰臀。
每一次重击落下,都让他眼前发黑,喉头涌上浓重的血腥气。他死死攥着拳头,
指节捏得咯咯作响,牙关紧咬,硬是将那几乎冲破喉咙的惨哼死死堵了回去。
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砸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十五下……十六下……十七下……行刑的金吾卫校尉臂力惊人,
每一杖都带着开碑裂石的狠劲。周临渊背部的衣料在反复的抽打下,终于承受不住,
“嗤啦”一声,从右肩胛处撕裂开来!刺耳的裂帛声在沉闷的杖击间隙显得格外清晰。
御座之上,刘瑾的目光骤然凝滞!撕裂的衣襟下,
暴露出一小片少年紧实、此刻却已布满青紫杖痕的肌肤。就在那肩胛骨下方,
靠近脊柱的位置,赫然烙印着一块胎记!那胎记形状奇特,边缘并不规则,却异常清晰,
殷红如血,仿佛一团被禁锢在皮肉之下、正熊熊燃烧的火焰!即便隔着数丈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