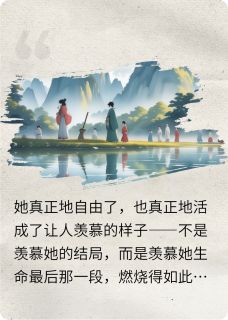前引顾砚深在我病危时,正躺在情人床上。“苏晚?她最会装可怜了。”他掐灭烟轻笑,
“死了正好清净。”后来他翻遍太平间,才从我僵冷的手指找到皱巴巴的孕检单。
停尸房彻夜亮着灯,他抱着录音机听我生前絮语:“砚深,今天雪好大,
你会回来吃火锅吗?”“医生说宝宝很健康……你说取什么名字好?
”“我在ICU好疼啊……你电话还是打不通。
”录音最后只剩呼吸声:“算了……我今天不等你了。
”那天顾砚深疯了抱着我的骨灰跳海。再睁眼他重生到我确诊那天,
红着眼冲进医院:“阿晚,我们不离婚了!”我笑着抽出癌症晚期报告:“顾总,
协议书签好了。”正文1.冬夜的医院走廊,被一种无处可逃的死寂沉沉笼罩着。
惨白的灯光如同白布,冰冷地涂抹在光洁的地板和墙壁上,空气中悬浮着消毒水的尖锐气味,
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食冰冷的刀片,割得喉咙生疼。病房里仪器的滴答声,
规律得如同催命的符咒,一下,又一下,敲打在濒临崩断的神经末梢上。
意识仿佛沉在冰冷的海底,模糊而遥远。苏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却只能勉强撑开沉重的眼帘一线。视线里一片朦胧的白色,惨白的天花板,惨白的被褥,
惨白的灯光……一切都在无情地旋转、扭曲。床边那个模糊而熟悉的轮廓,是张姨吧?
那张布满岁月沟壑的脸庞,此刻每一道皱纹里都盛满了悲戚和无措的泪水。
“张……张姨……”声音微弱得如同游丝,从她干裂的唇瓣间艰难地挤出,
带着铁锈般的血腥气。胸腔里像被塞满了滚烫的烙铁,每一次喘息都灼痛难忍,
“疼……好疼……”她的指尖下意识地抽搐着,仿佛想抓住点什么,
抓住这具身体正飞速流失的温度,抓住那不断沉入黑暗的意识。冰冷彻骨的绝望感,
如同无情的海水一寸寸漫上来,淹没了口鼻,扼住了咽喉。她清晰地感觉到,
生命正像指间流沙般难以挽回地逝去。最后一丝微弱的知觉,停留在右手无名指上。
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道浅淡的戒痕,像一个早已被遗忘的、褪色的印记。
她蜷了蜷冰凉的手指,仿佛想确认那曾经存在过的、微不足道的温暖。
意识彻底沉入无边寂静的黑暗前,一滴冰冷的液体顺着眼角滑落,无声地渗入鬓角的发丝里,
再无痕迹。2.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端,却是截然不同的滚烫人间。
浓烈得化不开的甜腻香水味混杂着雪茄的陈腐烟气,在装潢奢靡的公寓里肆意弥漫。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火树银花,流光溢彩,映照着室内一片迷离的昏暗。
昂贵的波斯地毯上,散落着凌乱的衣物,无声地诉说着放纵的痕迹。柔软的大床上,
顾砚深慵懒地陷在蓬松的羽绒枕里,结实的手臂随意地搭在身边女人光裸的肩头。
女人卷曲的长发如同海藻,铺散在他麦色的胸膛上,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正带着挑逗的意味,
在他心口处暧昧地画着圈。床头柜上的手机,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
嗡嗡的蜂鸣声执拗地穿透这片绮靡的空气。顾砚深蹙了蹙眉,被打扰的不悦清晰地写在脸上。
他连眼皮都懒得抬,慵懒地伸出手去摸索那恼人的源头。指尖触到冰冷的机身,
他摸索着按下拒接键,动作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烦。“谁啊?这么晚了还打。
”旁边的女人贴得更近,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和黏腻,柔软的躯体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
温热的气息喷在他耳边。顾砚深瞥了一眼屏幕,那串熟悉的号码一闪而过,备注是“苏晚”。
他眼底掠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厌烦和不屑,如同看到了什么惹人嫌恶的尘埃。
薄唇勾起一个凉薄的弧度,鼻腔里发出一声嗤笑。“还能有谁?苏晚。
”他将手机随意地丢回床头柜,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顺手拿起床头的打火机。
“啪嗒”一声脆响,幽蓝的火苗窜起,点燃了叼在唇间的香烟。
橘红的火光在他深邃的眸子里跳跃了一下,映出里面一片冰冷的漠然。
“整天一副病怏怏的死样子,谁知道又在玩什么花样。”他深吸了一口烟,
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又从薄唇间缓缓吐出,模糊了他脸上那毫不留情的讥诮,
“死了倒清净,省得天天碍眼。”他掐灭烟,翻身将身边的女人压在身下,
用行动彻底隔绝了那个不合时宜的来电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公寓厚重的窗帘隔绝了外面冰冷的世界。隔绝了医院里那盏代表生命流逝的微弱灯光。
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无声地旁观着这场奢靡的沉沦。
3.太平间的门轴发出沉重而滞涩的“嘎吱”声,缓缓向内开启。
一股混合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深入骨髓的冰冷气息朝他扑面涌来,
瞬间浸透了顾砚深单薄的衣衫,渗入骨髓。他的身躯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仿佛被这股绝对冰冷的气息击中了心脏。里面是望不到头的惨白。惨白的墙壁,
惨白的瓷砖地面,惨白的灯光,一排排冰冷的金属停尸柜整齐排列,泛着生铁的寒光,
如同通往地狱的墓碑。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冷冻设备运转时发出的、持续不断嗡嗡低鸣,
单调得令人窒息,像无数亡魂在暗中窃窃私语。顾砚深僵立在门口,
如同被无形的钉子钉在了原地。西装外套不知何时被他紧紧攥在手中,
昂贵的面料被揉搓得不成样子,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骇人的青白色。
他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死灰般的惨白,
甚至比他身后那些冰冷的金属柜还要惨淡几分。那双平日里深邃的眼眸,此刻却很空洞,
视线没有焦点,只在白瓷地面和冰冷的金属柜门上茫然地扫过,
里面翻涌着一种惊愕到极致的茫然。“苏……晚?
”一声低哑的呼唤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出来,破碎得不成调,更像是一声濒死的呜咽,
瞬间被这巨大的、吞噬一切的冰冷空间吸收得干干净净,没有激起一丝回响。
他艰难地挪动脚步,皮鞋落在光滑冰冷的瓷砖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万丈悬崖的边缘。引路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拉开一个编号冰冷的金属抽屉。
沉闷的滑轮滚动声在死寂中格外刺耳。一片刺目的白布覆盖着。那白布下,
是一个瘦小得触目惊心的轮廓。顾砚深的呼吸骤然停滞。他猛地向前踉跄一步,伸出手,
指尖颤抖,几次才终于触碰到那层粗糙的白布。布料冰冷的触感顺着指尖瞬间蔓延至全身,
冻结了他的血液和心跳。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掀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
白布下露出的,是一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曾经温婉柔和的眉眼,此刻紧紧闭着,
覆盖着一层灰败的死气。嘴唇是毫无生气的青紫色,微微张开着,
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最后的绝望。脸颊深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
勾勒出一副被病魔和绝望彻底榨干的模样。真的是她。
那个总是低眉顺眼、安静得几乎没有存在感的苏晚。那个在他厌烦时只会默默退开的苏晚。
那个……被他认定死了清静的苏晚。顾砚深的身躯晃了晃,几乎栽倒。
他猛地用手撑住冰冷的金属柜边缘,他剧烈地喘息着,胸膛急促起伏,
仿佛溺水的鱼被强行捞出水面,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
他死死地盯着那张灰败的脸,仿佛要用目光在那上面灼烧出两个洞来。视线一点点往下挪移,
最终落在她垂在身侧、僵硬蜷曲的右手上。那枯瘦得只剩一层薄皮包裹骨骼的手指,
以一种固执而扭曲的姿态紧握着。指节因为临终时的剧痛而僵硬地凸起,
仿佛用尽了生命最后一点力气,死死地攥着一个小小的、皱巴巴的纸团。是什么?
是什么让她在生命的尽头,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痛苦中,还要如此拼命地抓着?
顾砚深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要捏爆。他颤抖着伸出僵硬的手,
指尖带着不自控的痉挛,小心翼翼地试图去碰触那截冰冷僵硬的手指,
去掰开那凝固的、誓死守护的姿态。指尖碰触到她皮肤的刹那,
那冰冷和僵硬触感让他猛地缩回手,如同被滚烫的铁块烙了一下。他闭上眼,
狠狠吸了一口气,然后再次伸出手,带着颤抖,用尽全身力气,一根,一根,极其缓慢,
去掰开那早已失去生命温度的僵硬指节。他的动作笨拙而艰难,
仿佛在与一个无形的对手角力。终于,那如同铁钳般紧握的手指被掰开了。
一个小小的、被揉得不成样子的纸团,如同被遗弃的枯叶,
无声地跌落在顾砚深剧烈颤抖的掌心。冰冷的纸团躺在他温热的掌心,
那突兀的温差像一根烧红的针刺入神经。他急促地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
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浓重的、令人作呕的消毒水和死亡混合的气息。他几乎是屏住了呼吸,
用同样冰冷颤抖的手指,
一点点、极其艰难地展开那张布满折痕、边缘被汗水和某种深色痕迹浸透的薄纸。纸张很薄,
被揉搓得脆弱不堪,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开来。
他强迫自己将视线聚焦在那些模糊的字迹上。
【早孕报告单】姓名:苏晚诊断结果:宫内早孕,约6周。胚胎发育正常。
报告日期清晰印着——正是两个月前,他和苏晚最后一次平静对话的那天。
那天她似乎欲言又止,
底深处藏着一点他当时不耐烦深究的微弱光亮……轰——一声巨响在顾砚深的颅内猛然炸开!
仿佛整个太平间、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无声地、剧烈地坍塌、粉碎!
巨大的耳鸣瞬间吞噬了冷冻设备的嗡嗡声,眼前猛地陷入一片刺目的白光,
随即又被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彻底淹没。那张灰败的、毫无生气的脸,
那冰冷的触感,还有掌心这张薄薄的、却重逾千钧的纸片,如同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他的眼球上、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
“嗬……呃……”一声破碎的、不成调的单音从喉咙深处挤出。他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
双膝一软,“咚”地一声沉闷巨响,重重地跪倒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
膝盖骨撞击瓷砖的剧痛似乎完全被屏蔽,他只是死死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片,
骨节因用力而爆出可怕的青白色,仿佛要将它揉碎嵌入自己的皮肉骨髓里。他猛地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球死死盯着停尸柜里那张沉寂的脸,
瞳孔深处是山崩地裂后的彻底荒芜和难以置信的疯狂。
一股腥甜的铁锈味不受控制地涌上喉头,他生生咽了下去,口腔里弥漫开浓烈的血腥。
“孩子……我的……”破碎的音节从他紧咬的牙关间挤出,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嘶哑,
“苏晚……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啊!!!”他猛地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什么,
想要摇晃那具冰冷僵硬的身体,将她从这永恒的沉眠中唤醒,质问这残忍的真相!
但指尖在即将触碰到的瞬间,却死死僵在了空气里。巨大的绝望和悔恨如同冰冷的毒蛇,
瞬间缠紧了他的心脏,绞得他无法呼吸。
4.顾砚深那座位于半山、俯瞰全城夜景的顶级公寓,彻底变了模样。
曾经代表身份与品味的昂贵艺术品被统统粗暴地扫落在地毯上,
水晶吊灯被打砸得只剩下扭曲的金属骨架,意大利定制的沙发被刀锋撕裂,
昂贵的羽绒填充物如同惨白的雪片,洋洋洒洒铺满了狼藉的地板。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气息、破碎物品的粉尘味。公寓中央,
唯一一块稍显完整的空间里,一盏光线暗淡的落地灯孤零零地亮着,
像风暴中心唯一平静的死眼。顾砚深蜷坐在灯下冰冷的地板上,背靠着同样冰冷的墙壁。
他身上昂贵的丝质睡袍沾满了酒渍和灰尘,皱巴巴地裹着微微发抖的身体。他的怀里,
紧紧抱着一个老旧的、与这废墟格格不入的黑色录音机。那是苏晚的遗物,
他像疯子一样翻遍了他们那个早已被遗忘的“家”才在最角落的抽屉里找到它。
机器发出滋滋的电流底噪,在死寂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他颤抖的手指,
一遍又一遍地按下倒带键,又按下播放键。机器运转的沙沙声过后,
一个熟悉到让他心脏骤停的女声清晰而虚弱地流淌出来,
带着一种遥远的、努力维持的平静:“……砚深,今天窗外下了好大的雪。
最爱吃辣的火锅暖身子……我记得冰箱里还有你喜欢的毛肚和鹅肠……我炖了骨头汤做锅底,
放了枸杞红枣,很温补的……”声音顿了一下,传来几声极力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呛咳,
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接上,气息更加微弱,“……汤……还在锅里温着。你……要是忙完了,
能回来吃一点吗?医生说……我现在的状况,
不适合吃太**的……但我可以……陪你少吃一点点……”顾砚深死死抱着录音机,
指甲深深掐进塑胶外壳里,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他痛苦地闭上眼,
仿佛看到那个单薄的身影孤独地站在落地窗前,望着外面纷飞的大雪,
锅里炖着为他准备的汤,脸上带着卑微的、期盼的微光……而那时的他,搂着新认识的名模,
在灯火辉煌的私人会所享受着顶级的和牛火锅,杯盏交错,笑语喧哗。
他当时甚至不耐烦地按掉了她打来的几个电话。“哧啦——”磁带飞速转动,
跳到了下一段录音:“……砚深?
我……今天去医院做了产检……”录音里的声音带着极力抑制的激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像是捧着易碎的珍宝,“医生说……宝宝很健康……心跳声特别有力,像小火车一样!
咕咚咕咚的……”一阵极轻的、带着无限爱怜的笑声传来,短暂得像拂过心尖的羽毛,
“……你说……给宝宝取什么名字好呢?我想了好久……如果是女孩,叫‘念安’好不好?
平安顺遂……如果是男孩……你说……叫‘予珩’怎么样?
美玉的意思……希望他温润坚韧……”声音渐渐低下去,
带着浓重的疲惫和无法掩饰的疼痛喘息,
过没关系……宝宝好好的……就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商量一下……好吗?
”“砰!”顾砚深的额头狠狠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温热的液体顺着额角蜿蜒流下,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有心脏被生生撕裂般的剧痛。
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记得那天一个电话打进来,她小心翼翼地说去医院了,
他只冷冷回了句“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就挂了电话,
转头去赴一个无关紧要的商务酒局。他甚至没问一句她去医院做什么!
他以为又是那些无病**的“装可怜”!他像一头濒死的困兽,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
蜷缩着身体,脸颊死死贴着录音机外壳,
贪婪地汲取着那里面传出的、每一丝属于她的气息和声音。手指痉挛般地按下按键。
滋滋……滋滋……录音机里传出的不再是清晰的语句,而是一段嘈杂的背景音。
耳的仪器蜂鸣声、模糊不清的医护人员急促的交谈声、金属器械冰冷的碰撞声….层层叠叠,
如同来自深渊的噪音,编织着一张令人窒息的大网。在这片混乱的、象征绝望的声潮底部,
一个如同风中残烛般的女声断断续续地挣扎着。
好冷……好疼……骨头……像被……碾碎了……”声音被剧烈的、如同溺水般的喘息声打断,
每一次拉风箱似的抽气都带着濒临破碎的颤音,
电话……就……一句……一句就好……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求你……”“啊——!
!!”一声凄厉的叫声从顾砚深喉咙里爆发出来!他再也无法忍受,他松开录音机,
双手死死抱住剧痛欲裂的头颅,整个身体像被电击般剧烈地抽搐、蜷缩、翻滚!
额头上的伤口在粗糙的地毯上反复摩擦,渗出更多的血,染红了昂贵的织物。
他疯狂地用拳头砸向冰冷坚硬的地板!一下!又一下!
指骨碎裂般的剧痛也无法抵消心口那凌迟般的折磨!他仿佛看见了,看见了!
那个瘦弱的身影躺在ICU冰冷的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在无边的剧痛和死亡的阴影里,
一遍遍徒劳地拨打着那个永远不会接听的号码,
直到意识彻底被黑暗吞没……而那个号码的主人,正巧笑嫣然地搂着新欢,
享受着情人的温存!“为什么……为什么……”他像受伤的野兽般哀嚎,声音嘶哑破裂,
混杂着绝望的哽咽和浓重的血腥味,“苏晚……是我……是我该死……是我——!!!
”他猛地扑向被甩开的录音机,像抓住唯一的浮木,再次死死抱在怀里,
颤抖的手胡乱地摁着按键。滋……滋……录音机里长时间的空白电流声,
像极了生命临终前那漫长而寂静的弥留。就在顾砚深以为这就是尽头,
心脏被彻底冻结成冰时——一个极其微弱、极其平静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空茫得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失去了所有痛苦、委屈和不甘的波澜,
只剩下一种耗尽了所有生命力后的、近乎虚无的疲惫和解脱。
没有……”“……算了……不等了……”“……砚深……我今天……不等你了……”“咔哒。
”录音到此为止。机器自动停止了转动,只剩下令人窒息的绝对寂静。顾砚深僵住了。
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嘶吼、所有的挣扎,都在这一瞬间凝固。
他维持着蜷缩在地、紧抱录音机的姿势,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破旧木偶。
只有那双死死盯着录音机扬声口的眼睛,瞳孔深处最后的光芒熄灭了。那张英俊冷酷的脸上,
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彻底的、万念俱灰的死寂。房间里的毁灭气息,
窗外的万家灯火,怀里的冰冷机器……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缓慢地、极其缓慢地低下头,将冰冷的脸颊深深埋进那台同样冰冷的录音机外壳里。
肩膀几不可察地微微抽动了一下,再也没有抬起。再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午夜的寒风带着刺骨的湿意,卷起地上零星的落叶。黑色的跑车如同一头发狂的钢铁巨兽,
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在空旷寂静的街道上横冲直撞,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啸,
留下两道焦黑的痕迹。车内弥漫着浓重的酒气,混杂着一种濒临爆裂的疯狂气息。
顾砚深死死攥着方向盘,指关节因用力而发出咯咯的响声。
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眼底深处却是空的,
只有录音机里苏晚那句“不等你了”在疯狂盘旋。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黑色的跑车最终停在了悬崖边。车灯熄灭,四周只剩下海浪咆哮着猛烈拍打礁石的巨响,
如同无数怨魂在深渊之下发出的永恒呜咽。寒风呼啸着从敞开的车门灌入,
卷起顾砚深凌乱的发丝和外套。他抱着那个冰冷的骨灰盒,
脚步踉跄却异常坚定地走向悬崖边缘。脚下的碎石在他沉重的步伐下簌簌滚落,
瞬间被下方翻涌的墨色巨浪吞噬。悬崖边缘,狂风猎猎,吹得他破烂的衣衫紧贴在身上,
勾勒出里面轮廓清晰的骨节。他缓缓低下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一丝属于“顾砚深”的往日神采,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死寂和空洞。
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极其轻柔地摩挲着骨灰盒冰冷光滑的表面,动作小心翼翼,
如同抚摸着世界上最珍贵的易碎品。冰冷的触感透过指尖蔓延全身,
他脸上却奇异地浮现出一丝近乎虚弱的、扭曲的温柔笑意。
“阿晚……”声音嘶哑得几乎只剩气音,被狂风瞬间撕碎,“这里……好冷……是不是?
”他低头,将脸颊轻轻贴上冰冷的盒子,仿佛在汲取一丝早已不存在的温暖,
“……不怕……我这就……来陪你……”他抬起头,
望向前方那片吞噬一切光线的、翻涌的黑暗海面。
死寂的眼底终于燃起最后一簇疯狂而决绝的火焰——一种奔向毁灭的、唯一的救赎。他向前,
踏出了最后一步。冰冷刺骨的海水瞬间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挤压过来!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知觉!咸涩的海水带着死亡的气息,
凶猛地灌入他的口鼻、耳道!身体不受控制地被巨大的力量向下拖拽,
沉重得如同绑缚了千斤巨石!意识在冰冷和窒息中迅速沉沦……眼皮沉重得如同压着两座山。
意识在冰冷的虚无中挣扎,像是溺水者终于冲破水面。5.“……顾砚深?顾先生?
”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声音传来。顾砚深猛地睁开眼!
刺目的、毫无温度的日光灯灯光瞬间刺入他的瞳孔,让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
消毒水的味道……熟悉的消毒水味道!心脏如同被巨锤狠狠击中!
他不是……抱着阿晚的骨灰……跳进了……他猛地坐起身!
剧烈的动作牵扯着还未恢复的身体,带来一阵眩晕,胸膛剧烈起伏。
视线急切地扫过四周——惨白的墙壁,冰冷的金属仪器,
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有……眼前这个穿着护士服、一脸惊愕看着他的年轻护士?!
这里是……医院病房?!不是太平间?不是冰冷的海底?!
难道我被救回来了?阿晚的骨灰盒呢?
护士被他突然坐起和脸上近乎狰狞的癫狂表情吓了一跳,下意识后退一步:“顾先生?!
医生!医生……”“阿晚呢?!苏晚呢?!”顾砚深根本听不见护士在说什么,
他猛地掀开身上的薄被子,双脚急切地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一阵虚软袭来,他踉跄了一下。
护士被他眼中那种不顾一切的疯狂和恐慌震慑住了,一时忘了挣脱,
结结巴巴地说:“苏……苏**?
她……她在隔壁……医生办公室……说是……签什么……”后面的话语戛然而止。
因为顾砚深突然呆住,然后疯狂的摇晃护士问到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
护士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报了一下今天的日期。而后顾砚深像一阵飓风般冲了出去!
他赤着脚,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冲向护士指的那个方向!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
血液如同滚烫的熔岩在血管里奔流!他撞开挡路的移动输液架,撞开走廊里茫然无措的病人,
所有的感官只剩下一个目标——找到她!马上找到她!告诉她他不离婚了!他要守着她!
守着她和孩子!一辈子!“砰!”医生办公室虚掩的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撞开!
门板重重砸在墙壁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办公室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猛地抬头。
顾砚深剧烈地喘息着,胸膛剧烈起伏。他赤脚站在冰冷的瓷砖地上,狼狈不堪,
病号服凌乱地敞开着,露出里面线条分明的胸膛。汗水浸湿了他的额发,凌乱地贴在额角。
然而,当他看到那个坐在医生办公桌旁的、背对着他的单薄身影时,
那双布满血丝的、因为急切和狂喜而闪烁着异常光芒的眼睛,瞬间如同点亮了所有的星辰!
是她!真的是她!苏晚安静地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旧却很干净的米白色针织开衫。
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射进来,在她乌黑的发顶镀上一层柔和的浅金色光晕。仅仅是一个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