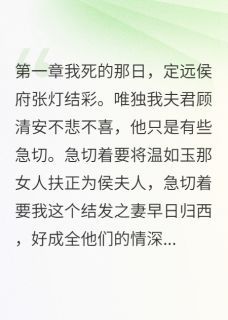我死的那日,定远侯府张灯结彩。
唯独我夫君顾清安不悲不喜,他只是有些急切。
急切着要将温如玉那女人扶正为侯夫人,急切着要我这个结发之妻早日归西,好成全他们的情深义重。
三年前父亲沈青山为了一批胡椒香料的生意,将我许配给了当时还是世子的顾清安。彼时他刚从边关回京,满身煞气,却在见到我时,眼中竟有几分温和。
大婚当夜,他轻抚我的发丝,嗓音低沉:"如意,从今往后,我便是你的依靠。"
那时我信了。
却不知,原来男人的话,如水中月影,看得见摸不着。
前些日子顾清安的心上人温如玉从江南归来,我才恍然明白,什么叫做真心错付。
那女人生得娇弱,走路都要人扶着,说话细声细气,仿佛稍大声些就要晕厥过去。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轻易便夺走了我夫君的魂魄。
温如玉回京的第一日,顾清安便搬出了我们的正院,说是不想冲撞了温姑娘的清誉。
第二日,他开始在后院为温如玉修建独立的小院,亭台楼阁,一应俱全。
第三日,他将我娘家陪嫁的那套紫檀木家具搬了去,说温如玉需要用。
我在正室立了三年,享受的待遇竟不如一个外来的客人。
昨夜我实在忍不住,寻到顾清安理论。
彼时他正在温如玉的院子里,两人相对而坐,温如玉正为他弹琴。那琴音袅袅,如诉如泣,听得人心都要化了。
我立在门外,看着顾清安眼中的温柔缱绻,忽然明白什么叫做讽刺。
三年来我苦心经营,想要换得他一个回眸,可他的眼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神色。
"夫君。"我硬着头皮唤了一声。
顾清安皱起眉头,眼中闪过不耐:"如意,你来作甚?"
"我是来问问夫君,这府中到底谁是主母?"我强撑着笑容,声音却有些颤抖。
温如玉此时停了琴音,楚楚可怜地看着我:"沈妹妹,是如玉打扰了你们夫妻,如玉这就离开。"
她作势要起身,顾清安连忙按住她的手:"如玉别动,你身子弱,经不起折腾。"
然后他转过头来看我,眼中竟有了几分冷意:"如意,如玉是我的客人,你作为主母,怎可如此失礼?"
客人?
我差点笑出声来。
哪有客人住在主人家三个月不走的?哪有客人要主母让出当家权的?
"好一个客人。"我冷笑道,"既是客人,为何要用我的陪嫁?为何要住主院?为何要管府中中馈?"
顾清安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沈如意,你不要得寸进尺!如玉她..."
"她什么?"我打断他的话,"她是你的什么人?值得你这般护着?"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温如玉低着头不说话,顾清安的脸色青白不定。
良久,他开口,声音冷得如同寒冬腊月的雪:"如意,如玉是我心尖上的人,这辈子我都不会辜负她。至于你..."
他顿了顿,眼中的光芒彻底暗淡下去:"你只是我的责任。"
责任。
这两个字如钢刀一般,生生**我的心里。
我嫁给他三年,为他生儿育女,为他操持家务,换来的却是一句"责任"。
而那个温如玉,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坐在那里弹弹琴,便是他心尖上的人。
"好,很好。"我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既然我只是责任,那这个责任,我不要了。"
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温如玉的哭声和顾清安的安慰声。
回到正院,我看着这个我住了三年的地方,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
床榻还是那张床榻,可枕边再无那个人的温度。
梳妆台还是那张梳妆台,可镜中的人却憔悴得如同枯花。
我在铜镜前坐下,看着镜中那个面容苍白的女子,忽然想起了什么。
半月前,大夫为我诊脉时,曾说我身子有些虚弱,需要好生调养。可我忙着府中事务,一直未曾当真。
如今想来,那日我便有些胸闷气短,只当是累的。
这些日子为了顾清安和温如玉的事心烦意乱,更是茶饭不思。
我伸手按了按胸口,那里隐隐作痛,仿佛有什么东西堵着,让我喘不过气来。
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我猝不及防,竟咳出一口血来。
鲜红的血滴在白绢上,触目惊心。
我怔住了。
难道我真的病了?
正想着,房门被推开,丫鬟小桃慌慌张张跑进来:"夫人,不好了!侯爷说要纳温姑娘为侧室,已经在准备纳妾的仪式了!"
纳侧室?
我手中的白绢缓缓滑落。
原来在顾清安心中,我连正妻的体面都保不住了。
又是一阵咳嗽袭来,这回血吐得更多。
小桃吓坏了,要去请大夫,我摆摆手制止了她。
"不必了。"我缓缓说道,"我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