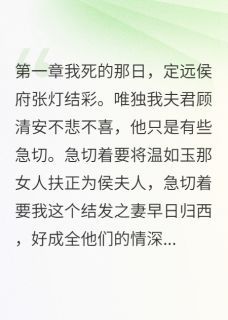纳侧室的日子定在三日后。
消息传出,整个京城都在看笑话。
说定远侯不过新婚三年,便要纳妾,这沈家的女儿怕是不得宠。
也有人说,沈如意这些年都未曾为侯府诞下一儿半女,侯爷纳妾也是无奈之举。
更有甚者,直接议论我是否有什么隐疾,不然夫君为何如此急切地要纳妾。
这些话传到我耳中,如一根根银针,扎得我心口发疼。
我嫁给顾清安三年,兢兢业业操持侯府,未曾有过半点差错。可到头来,在外人眼中,我却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怨妇。
更可笑的是,我确实无法为顾清安生儿育女。
去年秋天,我曾有过身孕,满心欢喜地告诉顾清安。他虽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喜悦,但也算上心,专门请了大夫为我调理身体。
可谁知那胎儿只在我腹中待了两个月便没了。
大夫说我身子底子薄,又操劳过度,才导致滑胎。
那段时间我整日以泪洗面,顾清安倒也算温和,常常陪在我身边,安慰我说孩子的事不要急,慢慢来便是。
我那时还以为他是真心疼惜我,却不想,他心中想的是另一个人。
如今想来,那时的温柔,或许也只是责任使然。
这三日来,我很少出房门,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飘落。
小桃几次三番劝我去找老夫人,说老夫人疼我,定不会让侯爷如此胡来。
我只是摇头。
老夫人确实疼我,可顾清安是她的独子,为了顾家的香火传承,她不会阻止这门亲事。
况且温如玉那女人善于伪装,在老夫人面前装得乖巧懂事,很得老人家喜欢。
前些日子老夫人还在我面前夸赞温如玉知书达理,说这样的女子做妾室,定能帮我分担家务。
我当时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
如今想来,老夫人或许早就知道顾清安的心思,那些话不过是在为今日的事做铺垫。
第三日清晨,我又咳了血。
这回小桃再也坐不住了,不顾我的阻止,径直去请了大夫。
那大夫姓王,是城中有名的郎中,专治内疾。他为我诊脉许久,脸色越来越凝重。
"王大夫,我夫人的病如何?"小桃着急地问。
王大夫收回手,叹了口气:"夫人这病,怕是积郁成疾,再加上身子底子薄弱,若不好生调养,恐怕..."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我倒是平静得很,淡淡问道:"还有多久?"
王大夫一愣,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地问这个问题。
"若是好生调养,配合汤药,还能撑个一年半载。若是再受**,或是操劳过度..."他摇摇头,"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
撑不过这个冬天。
如今已是深秋,距离冬天不过一月有余。
我点点头,示意王大夫开方子。
王大夫开了一大堆药,什么人参、燕窝、阿胶,都是极贵重的。
小桃拿着方子,眼圈都红了:"夫人,咱们赶紧按方子抓药吧,您的身子要紧。"
我看着那张方子,忽然笑了:"这些药,一副就要几十两银子,我一个将死之人,何必浪费这些钱财。"
"夫人!"小桃急了,"您别说这样的话,您会好起来的!"
我摆摆手,没有再说什么。
下午时分,侯府张灯结彩,开始准备纳妾的仪式。
我坐在房中,听着外面的锣鼓喧天,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三年前我嫁进这个府邸时,也是这般热闹。
可那时的新郎眼中有我,如今的新郎心中只有别人。
黄昏时分,温如玉换上了大红的嫁衣,从我的窗下经过。
那一抹红色如血一般刺眼,刺得我心口生疼。
我掀开窗帘看了一眼,正好与轿中的温如玉四目相对。
她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那笑容分明在说:沈如意,你输了。
是啊,我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一无所有。
夜深时分,侯府终于安静下来。
我知道顾清安今夜是要住在温如玉那里的,这个想法让我心如刀绞。
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伤心了。
这三个月来,我的眼泪早已流干,心也早已死了一半。
如今只剩下这副残躯,如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
我在床上躺下,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说过的话。
母亲说,女子这一生,若是遇不到良人,便不如早日归去,省得受这人世间的苦。
那时我还小,不懂母亲话中的深意。
如今想来,母亲或许早就看透了世事,知道女子在这世上的艰难。
我闭上眼睛,任由眼泪无声地滑落。
顾清安,这三年的夫妻情分,就当我还你了。
从今往后,我们各不相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