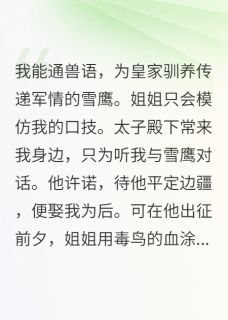我能通兽语,为皇家驯养传递军情的雪鹰。姐姐只会模仿我的口技。太子殿下常来我身边,
只为听我与雪鹰对话。他许诺,待他平定边疆,便娶我为后。可在他出征前夕,
姐姐用毒鸟的血涂满了我的身体。我被万鸟追啄,被**的野兽给……十年后,
太子已经成为皇帝,邻国送来一头上古凶兽,无人能近。1我没有死,
而是作为邻国使臣出使大燕。凶兽的咆哮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
下一刻,一道肉眼可见的黑色风压自它爪下挥出。劲风隔着十丈,精准地掠过皇后的发髻。
那顶象征着无上荣光的九凤金步摇,连带着一缕被削断的青丝,无声地坠落在地。
“铛”的一声脆响,像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整个大燕皇室的脸上。皇后闻人歌,颜面尽失。
我爹,当朝国丈闻泰,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肥硕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剧烈颤抖。“陛下!陛下明察!此女诡异,定是与这凶兽一党!
是她引来的灾祸!”他一边磕头,一边用凄厉的声音嘶吼,
试图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我的身上。“恳请陛下降旨,将这妖女与凶兽一同射杀!以正国威!
以安民心!”他身后,满朝文武,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跟着跪了一地,山呼海啸般地附和。
“恳请陛下,诛杀妖女!”萧玄策没有看他们,甚至没有看他那受了惊吓的皇后。他的视线,
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穿透所有奔逃的人影,穿透弥漫的尘嚣,死死地钉在我的身上。
我无视周遭的一切声浪,也无视他那几乎要将我洞穿的目光。我缓缓抬起右手,
苍白的手指在空中虚虚一握。然后以一种极其古老而优美的韵律,描画出一个无形的符文。
那符文没有光,没有声音,却仿佛带着某种源自天地初开时的律令。暴怒的凶兽,
竟在那符文成型的瞬间,彻底安静了下来。它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近乎哽咽的悲鸣。
然后,在全场死寂的注视下,它收敛了所有的利爪与獠牙,缓缓地,单膝跪地。
一个充满臣服与哀伤的动作,一个完完全全拟人化的动作。这比它刚才的暴虐,
更让全场感到震撼与恐惧。高台之上的萧玄策,身体猛地一震,
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帝王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认得那个符文。那是十年前,
在鹰营的星空下,我趴在他背上,用手指蘸着露水,一笔一划教他画出的。
那是独属于我们二人的,雪鹰传信的密记。“锵——”天子剑应声出鞘,剑鸣如龙吟。
他提着剑,一步步走下高台,无视了所有跪地的大臣,径直来到我的面前。冰冷的剑锋,
抵住了我咽喉的皮肤。“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压抑着十年火山喷发般的惊涛海浪,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迎着那足以割裂一切的剑锋,平静地抬起眼,
透过面具的缝隙看着他。“一个能解你身上血咒的人。”我没有点明,只说他。
但他龙袍之下,那每逢月圆之夜便会发作的隐疾,与眼前这头凶兽身上的上古血咒,
本就同根同源。萧玄策握剑的手,青筋暴起。此事乃皇室代代相传的最高机密,
除了他与贴身总管卫峥,绝无第三人知晓。他眼中的杀意几乎要凝为实质,翻腾不休,
但最终,还是被一个帝王的理智强行压了下去。“带她下去。”他收剑回鞘,
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刻意的沉重,声音也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交由御兽监,严加看管。
协助调查凶兽来历。”我爹闻泰与我娘柳氏,在人群后方交换了一个惊恐万分的眼神。
我清楚地看见,我娘那只保养得宜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那个做工精巧的驱虫香囊。
深夜,我获准进入了关押那头凶兽的玄铁兽苑。它被更粗的玄铁链锁着四肢,
但眼神中的暴戾已经褪去不少,取而代代的是一种迷茫的痛苦。它不是凶兽,它叫谢无衣。
我划破手掌,温热的血顺着掌心滴落。我将血,一滴滴地,
滴在他额头那枚诡异的古老烙印之上。烙印红光大盛,谢无衣发出野兽般痛苦的嘶吼,
**与人性在他的体内激烈地冲撞。但最终,他的眼神,恢复了片刻遥远而陌生的清明。
同一瞬间,灯火通明的皇宫寝殿内。正在批阅奏折的萧玄策,猛地感到心口一阵绞痛,
喉头一甜,一口暗沉的黑血喷在了明黄的奏章上。他一把撕开繁复的龙袍,只见心口处,
一个与谢无衣额头完全相同的烙印,正灼烧着他的皮肤,滚烫如烙铁。
贴身总管卫峥大惊失色,急忙取来御用的丹药。萧玄策却一把将他推开。
他眼中的杀机与悔恨交织,最终化为一道冰冷的密令。“去查。”“用尽一切手段,
去查十年前,闻人雀暴毙当晚,皇后闻人歌的所有动向。”“任何蛛丝馬跡,朕都要知道。
”2卫峥的效率高得可怕,他就像是萧玄策在暗影中最锋利的爪牙。
他的调查如同一把无声的尖刀,精准地剖开了中宫那张维持了十年的华美画皮,
直指核心的腐烂。闻人歌彻底慌了,她那份靠着模仿与谎言得来的尊荣,摇摇欲坠。
在我爹闻泰的授意下,她用金钱收买,用家人性命威胁,找到了当年鹰营的一名老卒。
朝堂之上,那老卒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跪在冰冷的地砖上,哭得涕泪横流,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陛下!陛下要为老臣做主啊!”他声嘶力竭地控诉,
每一个字都淬满了伪装的悲愤。“当年闻人雀**,
因嫉妒如今的皇后娘娘能得太子殿下青睐,心生恶念,心术不正啊!”“她妄图偷学禁术,
想操控鹰群谋害当时的太子殿下,结果道行不够,反遭天谴,被万鹰啄身而死!
老臣亲眼所见啊!”这番话说得声情并茂,殿中不少不明真相的大臣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萧玄策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神情隐在御座的阴影里,看不出喜怒。他静静地听完老卒的哭诉,
没有发怒,也没有安抚,只是突然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命令。“传踏雪。
”满朝哗然。踏雪,这个名字,对于很多老臣而言,并不陌生。那是十年前,
被誉为京城第一驯鹰天才的闻人雀,最心爱的那只白色海东青。
当那只老鹰被两名侍卫用特制的架子抬上殿时,所有人都看到了一股迟暮之气。它太老了,
羽毛失去了光泽,眼神也浑浊不堪,萎靡地站在架子上,仿佛随时都会死去。可当它的视线,
越过人群,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猛地爆发出惊人的光彩。
我向前走了一步,整个大殿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只是用十年未曾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
轻声唤它的名字。“踏雪。”那只已经老得几乎飞不动的老鹰,竟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悲鸣。
它不顾一切地挣脱了侍卫的束缚,用尽最后的气力,扑扇着翅膀,飞到了我的肩上。
它的飞行轨迹摇摇晃晃,却无比执着。它用它那苍老的头颅,一遍又一遍地,
亲昵地蹭着我的银色面具。喉咙里发出呜咽般的咕咕声,拒绝任何人的靠近。动物的爱,
永远比人真诚。我爹闻泰见到此情此景,脸色煞白,厉声呵斥起来,
试图用声音掩盖他的心虚。“妖女!定是你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妖术!迷惑了神鹰!
”萧玄策冰冷的眼神,如同实质的冰锥,扫了过去。“国丈是认为,
这只为大燕服役了二十年的御鹰,也中了你的妖术?”他不再看闻泰,
而是将矛头直指那个跪在地上、已经开始瑟瑟发抖的作伪证的老卒。“你,再说一遍,
她是怎么死的?”就在此刻,我缓缓地抬起了手,摘下了脸上那张戴了十年的银色面具。
我的手,抚上了那张覆了我十年爱恨的面具。银是冷的,一如我坠入深谷后的人心。
指尖微一用力,它便无声滑落,如同一片凋零的月光。大殿之上,吸气声此起彼伏,
不是惊艳,而是被极致的丑陋扼住了喉咙的惊骇。
我将那张沟壑纵横、鬼神见之也要避退的脸,当作我最锋利的投名状,
呈给这满朝虚伪的衣冠。“鹰有灵性,视主如亲。”我的声音不大,却因为这张脸的衬托,
而带着一种地狱归来的分量。“除非,活人的身上,
被一滴不漏地涂满了它们最痛恨的腐尸鹫之血,否则,它们就算死,
也绝不会攻击自己的主人。”那名老卒看到我这张脸,再听到腐尸鹫三个字,
像是看到了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索命冤魂,吓得魂飞魄散。他当场瘫倒在地,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状若疯癫,嘴里含糊不清地高喊着“有鬼有鬼归来索命了”。
萧玄策从龙椅上走了下来。他一步一步,走得极慢,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十年悔恨的刀尖上。
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那双深不见底的帝王眼中,
翻涌着滔天的悔恨、痛苦,以及一丝失而复得的狂喜。他伸出手,
似乎想触摸我脸颊上最深的那道伤疤。我毫不留情地侧身避开,如同躲避什么肮脏的东西。
他的手,就那样僵在了半空,收不回,也放不下,显得无比狼狈。
“雀儿”一声迟了十年的呼唤,充满了无尽的苍凉与卑微。“啊——!
”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划破了金銮殿的沉重。闻人歌彻底崩溃了。她像个疯子一样,
挣脱了宫人的拉扯,披头散发地扑向我,扭曲的指甲闪着恶毒的光。“你为什么不死!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你这个怪物!!”侍卫们反应过来,立刻冲上来,强行将她拖了下去。
她的咒骂与尖叫声,在金銮殿高大的梁柱间,回荡不休,显得格外凄厉。乱局之中,
一直被特制的玄铁链锁在殿外的谢无衣,再也无法忍受。他身上的锁链寸寸断裂,
如同挣脱了所有枷锁的远古魔神,轰然撞入了大殿。
他无视所有惊恐的官员与手持兵刃的侍卫,猩红的目光,
径直锁定了那张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龙椅。他发出一声充满挑战与仇恨的怒吼。
仿佛那把椅子,才是他真正的、不共戴天的敌人。3谢无衣的举动,
被视为对皇权最**的挑衅与蔑视。殿前的金甲禁军瞬间涌入,将他团团包围,
无数柄锋利的长戟对准了他,杀气腾腾。我却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挡在了他的身前。
我张开双臂,用我瘦弱的身体,为他筑起一道防线。我用这个姿态,
无声地向萧玄策表明:他恨的不是你这个皇帝。他恨的,是附着在这把龙椅上,
那道看不见的、代代相传的血腥诅咒。阴冷潮湿、终年不见天日的天牢深处,
我单独面对被剥去凤袍,狼狈不堪的闻人歌。她被铁链绑在冰冷的刑架上,头发散乱,
眼神怨毒,早已没了半分皇后的仪态。我从袖中取出一根磨得极亮的银针,
在她惊恐的眼前缓缓晃了晃。“姐姐,你这副引以为傲的、能模仿百鸟之鸣的嗓子,
一定很宝贵吧。”我捏住她的下巴,逼她张开嘴,缓缓将那根冰冷的银针,
刺入她保养得宜、曾让萧玄策驻足的喉咙。剧痛让她浑身剧烈地抽搐,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当年,给你腐尸鹫之血的那个鬼面人,是谁?”我贴着她的耳朵,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问。闻人歌在极致的痛苦与恐惧下,精神防线彻底崩溃。
她拼命地点头,眼中满是哀求。我拔出银针,她立刻像一条濒死的鱼一样大口喘息着。
“我说!我全都说!”她断断续续地招供,那个脸上戴着青铜鬼面的神秘人,每隔一年,
便会与我爹闻泰在城外三十里的鬼见愁密会一次。有一次,她按捺不住好奇心,
悄悄跟了过去,无意中偷听到他们提及两个字。换龙。从天牢出来,
萧玄策就站在昏暗的甬道尽头等我,仿佛已经等了很久。他告诉我,
他愿意以这万里江山为聘,废掉闻人歌,重立我为大燕的国母,
以此来弥补他这十年来的亏欠。江山为聘。真是天底下最动听,也最讽刺的笑话。
我没有回答他那自以为是的深情,
而是从怀中拿出了一份我从鹰营旧址的地砖下找到的残破星图。
星图的材质是百年不腐的鲛绡,上面用星辰的轨迹,赫然绘出了大燕皇陵的完整构造图。
而在那构造图的中心,地宫的最深处,被人用凝固的朱砂,重重地标记了一个血红的孽字。
我向他揭露了那个被萧氏皇族掩盖了数百年的,惊天真相。“诅咒,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源自你们萧氏的皇陵!”“你们皇室的血脉,从立国之初就有了缺陷,每一代君王,
都会暗中寻找一个命格奇特的承孽者,在继位之前,将自身的诅咒转移出去。
”我看着他瞬间惨白如纸的脸,一字一句地,将他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撕了下来。
“而我闻人雀,那个生来能通兽语的异类,就是你,伟大的君王萧玄策,为自己选定的,
那个本该在大婚前夕,就悄无声息地死去,为你承担一切罪孽的祭品!
”萧玄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后背重重地撞在冰冷的石墙上,无法辩驳。他继承皇位时,
确实从先帝留下的密诏中,得知了承孽的仪式。但他一直以为,
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祈求国运的仪式。他从未想过,那会真的牺牲掉我,
那个他曾许诺要一生一世守护的女孩。他的无知与自负,成了我十年地狱的开端。
“唯一的解法,就是进入皇陵,找到诅咒的源头。”我冷漠地提出了我的条件,
不带一丝感情。“我,与谢无衣,是我们这一代的孽主与镇陵卫,是开启陵墓核心的钥匙。
”“而你,萧玄策,必须用你的皇族之血,作为开启仪式的引。”我转身,
向着甬道唯一的光源走去,用一个决绝的背影告诉他。我们之间,
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的风花雪月。只剩下**裸的交易,与不死不休的清算。皇陵深处,
阴风刺骨,吹得火把上的火焰都变成了诡异的绿色。我们三人,用各自的血,
在尘封的石门上,画下了开启的法阵。地面发出轰隆的巨响,缓缓裂开,
一座由整块黑水晶雕琢而成的巨大棺椁,从地底缓缓升起。棺中躺着的,
并非身着龙袍的先帝。而是一个穿着古老战甲、与谢无衣长相有七分相似的男人。
男人的心口,端端正正地插着一把剑。那剑柄之上,盘绕的,
正是萧玄策血脉相连的真龙图腾!水晶棺彻底开启的瞬间,那个沉睡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男人,
猛地睁开了双眼!4那双睁开的眼中没有理智,没有生机,
只有被囚禁了百年的、凝为实质的怨毒与疯狂。黑水晶棺中的男人,大燕的先帝萧承渊,
张开了他干瘪的嘴,发出一声不属于人类的凄厉尖啸。那啸声并非声波,
而是一种直接冲击灵魂的诅咒。无数由黑色怨气凝结成的鬼脸毒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