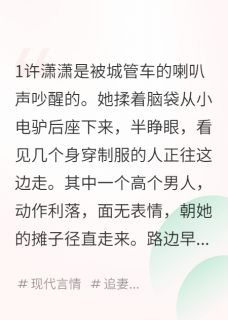1许潇潇是被城管车的喇叭声吵醒的。她揉着脑袋从小电驴后座下来,半睁眼,
看见几个身穿制服的人正往这边走。其中一个高个男人,动作利落,面无表情,
朝她的摊子径直走来。路边早起的几个摊主已经开始收拾东西,远远提醒她:“小许,快收,
今天城管来真的!”她皱了皱眉头,头发还没扎好,
三脚两脚跑过去护住自己刚刚摆好的玫瑰干花和香薰灯。“哎——别动我东西啊,
这是我自己做的,合规手工艺品!”她声调不高不低,
像是这几年应对执法队员练出来的职业素养。可男人的动作比她快,他已经蹲下了身,
一手摁住了木箱角。他没动,也没翻查,而是静静地看着她。那双眼,深而沉,
像是多年前午夜图书馆里,她转身一撞、撞进他怀里时的模样。她脑子轰一声炸开,
半晌才挤出一句话:“季……队长?”男人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他只是摘下执法记录仪,
语气冷静而公事公办:“许潇潇,今天你摊位被市民实名举报违规占道,请配合我调查。
”“你疯了?”她抬头,狠狠地盯住他,手却已经下意识地把一串花灯拽回了怀里。
“你不认识我了?”“认识。”他嗓音低哑,“五年前,我是你男朋友。现在,
我是执法人员。”“你**讲道理。”她冷笑一声,心口堵得厉害。她以为五年过去,
这人早就忘了她。她也骗自己忘了他。可这一句“我是执法人员”,
竟比当年那句“我们分手吧”还要扎人。“你想干什么?拆我摊?罚我款?拘留我?
”她眼神发狠,“还是想报复我当年甩了你?”“都不是。”他忽然垂眸,
嗓音低下去几分:“你今天别摆了,跟我回队里录个笔录,走流程。”“呵,走流程?
我看你是走心了。”“潇潇。”他忽然喊了她的名字。这声太熟了。她心里一跳。
“你别叫我这个。”她撇过脸,头顶的晨光晃眼。他站直身,看她动作很轻,
却一步也不让地站在她摊子前。这姿态,她太熟。从前上学时,她被老师点名批评,
死不认错,他站在她前面说:“她不是那意思。”他那时候不说废话,句句带执行力。
而现在,他成了真正的执法者,站在她人生里最不愿被打扰的地方。她冷笑着低头收摊,
一边收,一边咬牙。“你真行,季队长。当年追**一身穷书卷气,
现在回来靠一身制服威风?”他没动,手却伸过来,接住她差点掉下去的花瓶。她抬眼,
看见他手背上的疤——大学毕业前那个夜里,他们搬家时弄的。
那时候他说:“等我工作安定了,我们租个大点的屋子。”现在,他穿着制服站在她摊前,
竟像个陌生人。她不说话,他也不催,只等她慢慢把摊收完。最后,她提着箱子,
从他身边走过去时停住脚。“我摊子合不合规你自己清楚。真想查,就查清楚再来。
”“举报人说你占用非划定区域。”“那举报人是不是你派的?”“不是。
”“你还会撒谎了。”她走了两步,又回头盯着他:“你还记得当年你说什么分手理由吗?
”“潇潇。”“你说你要去考公务员,要在市里站稳脚跟,要跟我分手,
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她一字一顿,咬得极重:“现在你考上了,成了城管。
就回来管我这个小摊贩了?”他低声说:“不是回来管你,是回来找你。”她一愣,
脚下顿住。“可我不想再见你。”“那天我没来送你,你记恨我很久了,对吗?
”“我不是记恨。”她抬起头,笑得讽刺,“我就是怕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被你看见。
”他沉默半晌,嗓音落得极低:“我早就知道你在做摊子了。”“你以为你藏得住?
”“你做的花灯我认得出,你以前说过,想开一家‘夜花小铺’。”她怔住,脸色瞬间变了。
“所以你是故意来的?”“我在接举报之前,看到照片就认出是你了。”“那你还来?
”“你以为我不来,就能再见到你?”他的声音忽然拔高,连他自己都像吓了一跳。
她睫毛颤了颤,拎着木箱的手更紧了。“我不想和你重来。
”“那你为什么还住在我们以前租的那条街?
”“你为什么连摊子都摆在我们约会的那家烤地瓜店前?”她呼吸一顿,转头就走。
“我警告你,别以为你现在穿了这身衣服,我就得听你的话。”他没动,
却低声应了一句:“不是要你听我话。”“我只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现在看到了,
我不放心。”她步子一顿,没说话,也没回头,木箱的滚轮在石板地上一路颠簸,
像她此刻跳得快爆炸的心跳。她不知道季屿到底想干什么。可她知道,
自己原本用五年时间堆出来的盔甲,在这个男人一句“我不放心”里,开始裂开缝了。
2许潇潇回家那天,天刚亮。她蹲在门口拆箱子,头发散乱,指甲缝里全是玫瑰花泥。
她把那些还没来得及上架的香薰灯一个个掏出来,放在塑料布上晒。
香味混着泥土气息在清晨的风里游动,像是某种温柔的嘲笑。她失眠了。
昨晚季屿站在她摊前时那双眼睛,像个锈了的钉子,一直扎在她脑子里。
她以为自己早就彻底放下了。可身体诚实得很,她连夜整理摊子的时候,手都在抖。
门口的老邻居给她送来两根油条,叹气:“小许啊,早说过让你早点去申请个临时证,
听说城管那边现在换了队长,人特别狠。”她点点头没作声,
脑海里又浮现出季屿摘下执法记录仪那一幕。她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狠。明明一身正装,
却偏要在人最软的地方下手。他明知道自己是她这辈子最不愿再提的人。
偏要穿着制服出现在她摊前,像是要她把旧账一笔笔翻清楚。她死死咬着油条,
一口也咽不下去。手机忽然响了。是微信推送,联系人备注是“季屿”,她犹豫片刻,
才点开。只有一句话:【我申请了临时摊贩牌照给你,别乱跑,等批。】她气得笑了。
她连“我不需要你管”这句话都打了一半,最后还是删了。
她现在不是那个什么都可以跟他吵的大学生了。她活得太清楚,什么叫无依无靠。那天晚上,
她把那条街上所有能靠摊为生的人都问了一圈,确实,是有人在背后盯着她。
有人不愿她在那边生意做下去。同行太多,利益太挤。她本想着自己默默搬摊,
换条街重新开始。可季屿一出现,就像把她所有的“默默”都撕碎了。她去批发市场拿货时,
刚到门口,手机又响了。【你在哪儿?】她没回。一分钟后,电话打过来。
她冷笑接起:“你是不是精神病?你现在管我生活起居了?”“我来送你东西。
”“我什么都不需要。”“你昨晚掉了一只手套,我怕你手冻。”她手一紧,
看见手边确实空了一只灰色布手套。“你鬼啊?”“你那天把摊子丢我那儿,我整理了一下。
”“你整理我东西?”“我只动了手套,别紧张。”“那你现在在哪?”“在你后面。
”她猛地回头。他穿着便服,手里提着纸袋,像是路人。只不过这“路人”眼神太熟。
他从大学时期就是这种不紧不慢、稳到极致的男人,眼神看人像在计算温度。她看他一眼,
想走。他追了两步,递过纸袋。“里面有围巾、暖宝宝,还有新的手套。
”“你觉得我是乞丐?”“我觉得你手凉。”她咬着牙,扭头走。他在后面喊:“潇潇,
你不想听听我那年为什么走吗?”“我知道。”“你想考公务员,不想我等你。”“不对。
”他声音有些沉。“我考上了。可组织把我安排去外省培训两年,我那天是接到调令才走的。
”“你怎么不说?”“我说了,你肯定跟着来。”“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把我扔下?
”“不是扔。”他一步步靠近,压低声音。“是怕你跟着我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再断了自己发展。”“我怕我拖你。”“所以你选择让我一个人扛?
”“我以为……你会更恨我,这样好放下。”她喉咙一紧,没想到这人解释得这么干脆。
她忽然觉得——她这五年,是不是被他用两句话就打败了全部苦难的价值。她不能认。
她咬着牙,吐出一句:“你太自以为是了。”“对。我是。”他沉声,“我以为你会忘了我。
可你还在做‘夜花’。”她一愣。“你还记得我店名?”“我怎么可能忘?
”“我们那时候连Logo都画好了,就差开店了。”“潇潇,我不是突然回来。
我早就在调回市里的时候,就在找你。”“你没必要找我。”“有。”他看着她,
眼里是从未卸下过的克制和痛。“我来,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重新试试。”她嗤笑一声。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现在是公务员,身价不一样了,我就会倒贴回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也不是。”她扭头,“你以前不会这样欺负我。
”他没再说话。只把那纸袋放在她电动车踏板上。“你做的花,好看。”“我妈放在屋里,
说每天都像过节。”她愣住。“你妈……还好?”“你走那年,她查出来慢性病。
我怕你难过,就没告诉你。”“她还惦记你,说你比我还懂生活。”许潇潇的鼻子忽然一酸。
“你再说一句,我可能就原谅你了。”他笑了,声音轻得像风。“那我不说了。
”“等你愿意原谅的时候,你告诉我。”她站在原地,背影僵直。等他走远,
她才打开那纸袋,看到里面除了围巾手套,还有她爱吃的豆沙饼,一层纸包得严严实实。
她蹲下,抱着膝盖,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五年过去。那个连分手都说得决绝的男人,
还是记得她喜欢豆沙多、不要芝麻的口味。她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回来追她。她只知道,
她那副早就该死透的心,竟然,还在跳。3自从那天起,
许潇潇的摊前就多了一个“不速之客”。每天六点半,她刚把伞撑开、灯串挂起,
季屿就出现在摊子旁。不是来查摊,也不讲话,就站着。风吹得他制服猎猎响,
她假装看不见。可身边那股带着薄荷味的干净气息,
和他站姿里那股“我是公权力”的压迫感,她闭着眼都认得出。“你到底想干嘛?
”她第三天没忍住,黑着脸开口。“陪你看摊。”“我不需要你陪。”“我在执行公务,
巡查该街区域摊贩秩序。”“你每天都来我这边巡,是不是太‘偏心’了点?
”“你是重点保护对象。”他理直气壮地说完,抬手递过来一杯热豆浆。“早饭没吃。
”她瞪了他一眼,没接。他就不动了,拿着那杯豆浆,一直举在她面前。
周围摊贩早就看傻了眼。“潇潇啊,你家这位城管男朋友真体贴。”“不是。”她咬牙,
“他不是我男朋友。”“那他这执法态度,也太不标准了吧?”“你们别瞎起哄。
”“可我看他比你还准点上下班。”“对,他有病。”季屿没回应,
只默默在一旁拆了包子递过来。“今早换口味,韭菜鸡蛋,清淡一点。
”她盯着包子皮上的热气,咬牙接过:“吃你一顿算我倒霉。”他忽然笑了,
那一瞬间连眼尾都染了暖色。“那我继续倒你霉。”她心跳一滞,转头不再理他。
可心里有一块地方,被他轻轻按了一下,没来由地软了。第七天早上,她起晚了。风太大,
手推车上的一串香薰蜡掉下来,碎了一地。她蹲下身去捡,手指被玻璃划破。鲜血涌出来,
她咬着唇,继续收拾。这时那熟悉的皮鞋声响起。“你怎么不戴手套?”“我懒得戴。
”“你这人怎么就不学会照顾自己?”他弯腰,拿出随身急救包,动作娴熟地给她包扎。
她盯着他认真包扎的手,忽然喉头哽住。她想起大学那次她发烧,他凌晨两点跑去买退烧贴,
回来湿透了外套。那时候的他和现在好像没差太多。只是现在更沉、更稳,也更让人放不下。
她低声问:“你这几天到底想干什么?”“想追你。”“你以前追我,也没这么不要脸。
”“以前是你先表白的。”“我那时候脑子进水。”他忽然抬头看她,
眼里没笑:“那我现在来,让你重新喜欢我。”“你觉得你配?”“我配。”他说得很轻,
却极稳:“你一个人撑了五年,我知道你不容易。”“你不需要我,但我需要你。”“潇潇,
我想跟你在一起。”她怔住。他说这话时,阳光打在他肩膀上,制服下摆在风中轻摆,
他像极了那个从图书馆走来、把她从人群里一眼认出来的少年。只是那少年曾转身离去,
如今又执意回来。当晚收摊,她本以为他走了。可她刚回到小区门口,
就看到他蹲在楼下台阶上,手里拎着一袋菜。“你还不走?”“给你做饭。
”“你是不是疯了?”“我想吃你做的饭。”“我不做。”“那我做。”他说完就起身,
跟着她进了楼。她住在老旧小区的五楼,楼道灯坏了,楼梯湿滑。他跟在后面,
一路提着菜没发出一点声。进门后,她靠着门口不动。“你真要做饭?”“嗯。
”“我厨房油烟机坏了,火小,菜刀钝,盐也快没了。”“我带了盐。”她差点被他气笑了。
他开始洗菜,她躲在沙发上抱着枕头偷看。他动作不像一个只会执法的城管。切菜利落,
配菜搭配有序,连调味料都掌握得极好。她终于忍不住:“你是不是提前练过?
”“我练了半年。”“你练做饭干嘛?”“等你哪天愿意嫁我,不至于饿着你。
”她脸“腾”地红了,差点把抱枕扔他脸上。“你别逼我扔人。”“你扔吧,我接着。
”饭做好了,他递给她一碗豆腐炖鲫鱼。她没动,盯着他看:“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这一套?
”“没有。”他停顿一瞬,声音低了下去。“我只是想弥补。”“你这些年怎么过的?
”“还行。”“你没谈恋爱?”“没有。”“你为什么不谈?”他看着她,
语气平静:“我在等你。”她喉咙像被堵住了。她努力把眼泪逼回去。可那晚吃完饭,
他走后,她抱着碗坐在厨房,哭了很久。她不知道该不该信。可她的心,已经开始动摇。
第二天,摊前多了一张折叠椅。椅上坐着季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她走近一看,
是她的正规摊贩牌照审批件。他递过来一支笔。“签个字,官方盖章,摊位从此合法。
”她盯着那纸看了三秒,没动。“你给我办的?”“我走正规程序,没插队。
”“你为什么帮我?”“你是我未来老婆,我不帮你,帮谁?”她呼吸一顿,
差点把那支笔砸他脸上。“你有病。”“嗯,病得不轻。”“那你赶紧去治。”“你不治我,
我不会好。”她没忍住笑了。笑完,又觉得心酸。他是那个她哭着想放下的人。可他一笑,
她的心就不听话了。他是她的软肋,也是她的执念。现在,他穿着制服回来,说要追她。
她不敢信,却又无法拒绝。因为她知道,如果这次还不回头,她可能再也走不出去了。
4事情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清晨爆发的。许潇潇刚把摊子摆好,还没来得及点亮灯串,
就看到两辆城管执法车停在了街口。不是季屿那一队。而是她从没打过照面的二分队,
带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短头发女队长,语气比她摊子上的玫瑰刺还扎人。“许潇潇,
你涉嫌多次无证摆摊、超区域经营,现在我们要对你的摊位进行暂扣清理。
”她还没反应过来,摊前就围了好几个执法队员。她气得发抖:“我有临时摊贩许可证!
这是正规渠道批下来的!”“那你出示。”她连忙翻包,找到那张刚打印没几天的纸,
递过去。女队长皱着眉翻了几页,冷笑了一声:“你这个批件,是季屿提名的吧?
”她怔住:“……对。”“你和他什么关系?”“我们……没关系。”她一口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