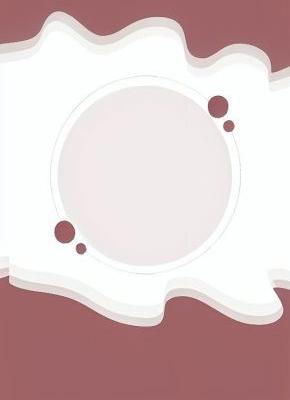复苏的庄原
张永
(1)
50年代末,中原大地上发生了饥荒。短短几年之间,整个中原的庄户上,饿殍遍野,人口数量骤然下降。人们为了抵抗饥饿,是想尽了办法。野菜、野草、树叶、树皮......几乎所有可以入腹的事物,都成为了人们充饥的食物。在饥荒闹正凶的时候,太康县下辖的所有公社,开始组织乡民们吃大锅饭。田地、牲畜、房屋、粮食统一收归集体,由队里分配管理,人们只需按劳力分工,每日按劳力级别分发食物。开始时,大家伙每天下田劳动完回到村里,尚能够分到一顿饱饭。孩子们也能分到二、三级馍,勉强能够充饥,大家伙的日子总算还过得去。只是,没几个月,积贫积弱的庄户上,再也支撑不起大伙吃大锅饭,人们一度陷入恐怖的饥饿里。而吃大锅饭就在这样极度贫弱的饥荒里,戛然结束了。
这时,杨凤莲刚好十二岁,还是杨庙公社铁佛寺小学校的一名小学生。对于这个年月里的孩子们来说,读书并不是必要的事,只有找到食物充饥才是头等的大事。杨凤莲家中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中两个哥哥,大哥杨学明已经结婚,二哥杨学成已经充当家中劳力不再读书,只有她领着妹妹凤英在上学堂。对于杨凤莲来说,她本是不愿读书的,只是碍于不读书就得帮着家里干活儿,所以也就硬着头皮去读了书。即便去学堂,繁重的家务她依然没有少干。每一天去上早课之前,她都必须到村里水井边去挑两担水,作为一家人一天的吃水。而且,到了晚上,她还要跟着娘亲吴氏学着纺棉织布,尤其是到了麦收、秋收时节,她还要跟妹妹凤英,到队里的田亩上去捡麦子、玉米棒。其实,说是去捡,很多时候就是偷拿队上的小麦、红薯、花生......在这会儿,没有人认为偷东西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家家户户都在偷,不偷就意味着饿肚子,甚至于饿死。所以,即便家家户户冒着被抓、挨批斗的风险,也要去偷食物充饥的。
春天,对于庄户上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救命的季节。只要草木一返青,人们就有了食物。对于杨家村的人来说,除了极少的说是吃了中毒的草木花叶不被采食以外,整个庄原上凡是有生命的事物,几乎都是人们充饥的食物。十几岁的杨凤莲,对于这段时间的记忆,是最为深刻的。作为一个被饥饿驱赶着的女孩子,她几乎挖遍了整个庄户上的野菜及其能吃的野草,也爬遍了所有能采食花叶的树木。尽管春天有食物可吃,可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杨凤莲的记忆里,就有一件发生在春天关于吃的事情。
那年春天,等人们采食过榆钱、槐花、树叶......等庄户上只剩下些不大中吃的食材时,人们就变着法的找其他食物充饥。一次,村子里的几个孩子,采摘了一棵粗大椿树上的叶子,拿回家用热水煮了撒上盐巴吃。这样吃过的孩子们都说好吃。一听说这椿树叶也能吃,杨凤莲跟同村的杨红霞也爬到树上采摘了这椿树叶。两人回到家都照着其他人的吃法,将椿树叶煮了撒上盐巴吃。已经被饿的面黄肌瘦的杨红霞一吃这椿树叶,觉得简直好吃极了,于是就连着三天都拿这椿树叶充饥。不料,几天下来,杨红霞的脸肿胀得像个硕大的圆球。这引得孩子们在一段时日里嘲笑杨红霞。杨红霞除了在家人面前哭泣,就是找跟她关系好的杨凤莲诉苦。最后,为了躲避其他孩子们的嘲笑,连学也不去上了。杨红霞的脸肿胀了半个月才逐渐地消了肿。这件事对村里人的影响很大,从此后,哪怕再饿,也没人再敢吃椿树叶了。
等到地上的野菜、草木被人们搜刮的一干二净时,刚好迎来一年中最重大的事件:麦收。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日。小学校已经放了麦假,孩子们个个挎着篮子、背着布袋,在田间地头上转悠。散落在田间地头上的麦子早已被捡干净,孩子们只是瞅着队上的人,趁着他们一不注意就将麦垄上的麦子,连抓带折的装进篮子、布袋,待篮子、布袋一装满,就各自朝家跑去。杨凤莲也是这些捡麦子孩子中的一个,由于比着其他的孩子年龄大一些,队上的人一发现田垄上的麦子有被窃的迹象,就拿着她这般年龄大些的孩子出气。虽说,她并不怕队上当官的人拿话吓唬她,可她怕自己辛苦获取的麦子被没收。有几年麦收时节,有好多次,杨凤莲跟妹妹凤英冒着毒日头,在田间捡来的麦子都被大队上的人没收充了公。每一次被没收麦子,两人都要大哭一场。不过,受着饥饿的驱使,两人每当被没收了麦子,接着依旧是想着法的继续“捡”麦子。因为“捡”麦子,也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杨凤莲跟妹妹还有村子里的其他几个孩子,一起在田地里捡麦子,恰好遇到队上的人巡查。等有孩子发现了巡查的人,就立即喊着:“来人了,来人了......”说着,孩子们拔腿就跑。杨凤莲见妹妹人小,可能被赶上,就立即把妹妹凤英推到金黄的麦田里说:“拿着布袋快藏起来。”说完,她就跟其他伙伴们一起跑了。只有八岁的小凤英身材矮小,却很是机灵,她听到姐姐的话,就立马扒开麦垄趴下,麦垄正好淹没掉她整个幼小的身子。这次,杨凤莲跟其他伙伴们总算逃过了一劫,就连幼小的凤英也把麦布袋保护的好好的,没被没收了去。事后,每当凤莲、凤英说起这次有趣的经历,都要笑得直不起腰来。
麦收完毕,接着就是播种秋茬庄稼。一连几年都是赶到七八月份发大水。由于水利欠修,一发水,整个庄原都是水汪汪的一片。对于庄户上的人家,这无疑是灾害。可对于孩子们来说,发水也并不都是坏处,比如:可以抓鱼。杨凤莲最是天不怕地不怕少有的勇敢姑娘,她最拿手的就是趟水捉鱼。在大水淹没庄原的几个月里,她捕捉的鱼足有几大缸,这对于食物匮乏年月里的家人来说,这些鱼无疑是最宝贵的食物了。杨凤莲个头高挑,动作麻利,下水捉鱼恰好能够让她一展身手。由于妹妹凤英太小,怕下水有危险,于是凤莲就跟她的伙伴杨红霞成为了捉鱼时最好的搭档。只要一下学,凤莲跟红霞两人就会回到家里,各自带上箩筐去到村东头的小河沟里捉鱼。等两人来到小河沟,就会找一个水流急湍的居高位置,用泥巴垒在水流的两端,只留下一个口子放置好箩筐。这样一来,两三个小时,两人就能捉半箩筐的鱼。等两人分了鱼,各自回到家里,家里人就会把鱼一条条的削掉鱼鳞,先用粗盐腌制起来,等吃的时候,或水煮,或烧烤,总算是能够犒劳下一家人饥饿的肚子。
对于捉鱼,凤莲跟杨红霞之间还有个秘密,那就是每当捉好鱼,就先把大鱼分拣出来,留下小的鱼秧再放进河里。这个做法是凤莲想出来的,她说是为了让那些小鱼回归河里,等他们长大了再捉,不然,怕是捉光了小鱼,将来河里就没有大鱼可捉了。杨红霞觉得凤莲的说法是对的,从此,两人捉鱼就只要大鱼,放小鱼。只有一次,两人捉了小鱼。那是因为凤莲的娘亲有一段时间得了病,凤莲听人说,生病的人喝小鱼汤病好得快。于是,她就跟杨红霞一起捉了小鱼。这次捉鱼的时候,凤莲从家里多带了一个物件,那就是瓷碗。等她们捉好鱼,分拣出大鱼,就用瓷碗从箩筐里舀出一碗小鱼,剩下的就再次放回到河里。凤莲娘亲喝了小鱼汤,没几天病就好了。后来,凤莲娘亲听说了自家女儿只捉大鱼放小鱼的情况,逢人就说:“俺闺女心眼儿好,老天爷心疼,才消灾祛病的。”
凤莲的大哥杨学明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由于大人们都要充当劳力干活,照顾小侄子的重任就落在了凤莲身上。大嫂要下田做工分,没有时间照应孩子吃奶,凤莲就要在下学时间,抱着孩子去找大嫂给孩子喂奶。大嫂下田的地点并不稳定,凤莲时常要抱着孩子跑上四五里路去给孩子喂奶。由于是去外庄,凤莲在去给孩子喂奶的路上有时会遇到困难,比如会经过被水淹没的路,她既要一边照顾幼小的孩子,一边又要顾着安全。有两次,凤莲在经过一段水流急湍的道路时,都差点跌倒在水里,还好最后都是有惊无险。不过,有一次的经历却是令凤莲后来越想越后怕的。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凤莲抱着孩子去到三里地开外的蔡庄去给孩子喂奶,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外村的浑小子。这几个小子跟凤莲年纪不相上下,他们见到大上午的一个女孩儿抱着个孩子,在河沿边走路,就起了捉弄她的想法。他们先是冲着凤莲吹口哨,嘴里喊着轻佻的浑话,他们见凤莲并不理睬他们,就变得更为嚣张,他们开始朝凤莲扔土坷垃。这时,凤莲真的被激怒了。她把孩子放在地上,一弯身就捡起坚硬的土坷垃跑向几个浑小子,朝他们的方向使劲扔去。几个少年一看到猛扑来的凤莲像是发了疯似的,于是就忌惮的跑了。可是,倔强的凤莲并不肯就这样放走几个坏小子,她一边一路追赶着这几个小子,一边不时的弯身捡土坷垃,朝他们投掷着,直到见他们进了村子,她才停歇下来。直到这时,累得气喘吁吁的凤莲,才想起被她放在河沿上的孩子。凤莲心里突然害怕起来,万一弄丢了孩子,那就麻烦大了。于是,她又使出浑身的力气跑起来,直到一口气跑到孩子身边,她才松了口气。她抱起孩子,随之说了一句:“谢天谢地,你还在。”等她回到家里,凤莲并没敢把这次经历告诉任何人,虽说,孩子并没有事,可她仔细想了想,认为以后她再也不能把孩子独自留下就走开了。
凤莲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就下了学,这时的凤莲干活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纺花、织布、纳鞋底......可以说女人们做的手工活儿,她已经样样精通。这一点,就连村里做针线最好的女人,也夸赞凤莲心灵手巧来着。尤其是到了冬天农闲时间,凤莲已经完全像个大人似的,可以跟她娘亲整夜熬眼做针线活了。凤莲的爹杨新功在队里做饲养员,专门喂养队里的牲口。凤莲自从下了学,经常走二里地的路去帮着爹喂牲口。说是喂牲口,实则还是为整个家里寻找食物吃。杨新功利用牲口吃剩下的草料中漏下的麦粒,喂下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每过几天,凤莲就会来取母鸡下的鸡蛋,拿回家煮了,给家里人补充营养。然而,就在凤莲十六岁这年,她爹得了肺炎去世了。这一下子,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凤莲也只得充当劳力,下田去挣工分。从这时开始,凤莲白天做工分,晚上做针线,真正地充当成年人在出力了。
凤莲十八岁那年,他二哥杨学成结了婚。第二年春天,杨凤莲嫁到了十里地开外的张庄村。凤莲嫁到的张庄这户人家,是由铁佛寺集市上的熟人介绍的,媒人就是凤莲的丈夫张运昌的姐夫。杨学明跟张运昌的姐夫恰好是打小一起读书的同学,又因为是邻村,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会儿,一般人家都能吃上白面跟杂面混和的窝窝头,不过,对于家里较为贫困的庄户,日子依然很不好过。等到凤莲长成大姑娘时,张运昌的姐夫就撮合了这门亲事。等到凤莲嫁到张庄时,这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嫁给了一家比自家还要穷的人家。
凤莲嫁到张家时,家里除了一口铁锅跟三间茅草屋,是穷的叮当响。张运昌共姐弟三个,两个姐姐,他排行老小。凤莲嫁给他时,家里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公爹也在闹饥荒那会儿饿死,目前家里还有一个婆婆。由于张家较穷,凤莲嫁来时,一日三顿饭都成问题。凤莲婆婆田玉英不是向那家借瓢面,就是向这家借斗粮食,一旦借不来吃的,一家人就只好挨饿。素来勤劳的凤莲没有向贫穷低头,而是一嫁到张家就挑起了主要劳力的大梁。白天下田做工分,晚上纺花、织布做针线,一年过去,家里安置的就有了一般庄户人家的样子。人家眼瞅着张运昌家里的日子慢慢有了起色,都纷纷地议论着,说张运昌这小子走了狗屎运,娶了一个能干的媳妇儿。
田玉英是个性子特别活跃的人,平时对下田劳动不大上心,是宁愿挨饿也不愿出力的主儿。田玉英要么时常串门扯闲话,要么就是十里八村地跑着听小戏、逛**,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爱跑路闲不住的人。村里人都知道,田玉英这个女人家,除了闲逛玩乐,干啥啥不行。其实,田玉英除了下田出力不行,凡是女人们做的针线,她也是既懒得做,也不会做。在凤莲没有嫁来张家之前,只要是裁剪衣裤、纺花织布的活儿,她都是跟村里的女人家换着做,她替人家干活带孩子,好让人家替她做针线。
田玉英性子爱玩爱闹,可饥荒年月,也免不了吃苦。她两个女儿,大女儿素勤因为饥饿出外讨饭而远嫁商丘,嫁到铁佛寺村的二女儿素娟,因为丈夫参加援疆建设,独自一人在家照顾一家老小。在饥荒年月,眼看着二女儿跟几个孩子就要饿死,田玉英白天挖野菜野草,晚上煮了揉成团子连夜送到女儿家,就这样养活了二女儿一家几口人。然而,在田玉英拼了命救二女儿一家人命的时候,她的丈夫张锦堂却丢了性命。张锦堂本是村里的村长,在饥荒年月,家家户户到田里偷粮吃,可顾面子的张锦堂怕挨批斗,是宁愿挨饿,也不愿去偷拿队里的粮食。所以,一等过了夏天,庄户上的草木一被吃干净,就只能干等着挨饿。这一年,一连饿了几个月的张锦堂好不容易挨到了秋收,一等分拨下粮食,就狠狠地吃饱了一回。在他一连吃了五个豆面窝头后,不想竟然被“撑死”了。
张锦堂共兄弟四个,家家都有几个儿子,唯独张锦堂自己只有张运昌一个儿子,所以,血脉单薄的张锦堂很遭近门人瞧不起。再加上张锦堂死后,近门的几家人,都眼馋他祖上留下的几片宅基地,他们时不时的会故意找张运昌的麻烦。特别是张运昌的二大爷,有三个儿子,个个生得心性歹毒。他们欺负张运昌人弱,就想着法地欺压张运昌,好独占张家祖上的宅地。直到杨凤莲嫁给张运昌,家里才真正有了主心骨,一家几口人的日子才算有了点起色。虽说,杨凤莲是个女人家,确是女人中最为坚韧的。自她嫁来张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劳苦,还是遭到了近门人的欺压,她都能默默地一一忍受下来。
凤莲嫁给张运昌的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红兵。而这一年,恰好是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庄原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村庄都升腾起了一股“反地主反坏右”的热潮。文革一开始,张运昌就带领村民,积极响应公社里的号召,领头在村子里破四旧,搞革命。在文革的这几年里,升任红卫兵主席的张运昌,四处奔走,结交了很多周边各村的义兄义弟。一时间,好不风光。可张运昌毕竟心底良善,性情软弱,搞不来批斗人的他,很快就被村里的另一股批私斗富的势力所取代。这股势力以张庄村的张铁三为代表。张铁三笼络了村里一群敢斗敢干的斗争骨干。张运昌二大爷家的大儿子张运龙、三儿子张运虎是拥护张铁三的骨干代表。张铁三一上台,就以狠斗狠批的手腕,斗倒了很多祖上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挨批斗的人中,也不乏是跟张铁三原先关系不和的人,而张运昌就是其中一个。张运昌曾跟张铁三争过文革主席的头衔,就此得罪了张铁三。等张铁三一当上队里的支书,就暗中打压张运昌,以“张运昌搞斗争不彻底”为由,令人取代了张运昌的主席头衔。自从张运昌失去了文革主席的位置,就陷入了暗里被张铁三打压,明里与之斗争的境地。张运昌跟地主成分出身的张锦玉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他做文革主席时,曾多次暗地里帮助张锦玉,让张锦玉多次逃掉了挨批斗的厄运。不想,这恰好成为了张铁三说张运昌包庇地主阶级的理由。自此后,张运昌成为了村子里除了地主富农之外,时常被作为斗争对象的一个。
自从张运昌在村子里落得一败涂地,杨凤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没几年,凤莲又生下了二儿子春生跟三儿子建明。肚子的饥饿,再加上在村子里受冷眼,日子过得是举步维艰。眼看着张运昌一家人丁,马上就要兴旺起来,近门的几户,更是心生妒忌。尤其是近门的几个婶子、大娘,更是视凤莲为眼中丁,时不时的给凤莲脸色看。为此,田玉英跟几个妯娌,大吵了几次。可每次总是在争吵中不了了之。之后,凤莲依然会遭到她们类似于指桑骂槐般的欺负。不过,为了几个幼小的孩子,凤莲学会了忍气吞声,不管遭到怎样的冷眼冷语,她都一笑置之。在凤莲的信念里“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凤莲一直相信老天是有眼的。
张运虎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狠厉角色,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对我张运虎来说,杀人算个**。”可以说,在整个村子里,他除了巴结支书张铁三,其他人他都敢欺负。不管谁家的孩子,他看不顺眼就动手教训;谁家的柴火、鸡鸭,一被他看到,就被他偷的一干二净。有两次,跟村子里的人斗架,他实实在在的举着镢头往人家身上砸,差点要了人家的性命。在村子里,他是被公认的“老虎”。张运昌素来受近门几户人的欺压,再加上支书张铁三暗中挑拨,张运虎眼中头一个容不下的就是张运昌。张运虎不是伙同村里人强占张运昌的宅地,就是暗中跟张铁三勾结,找张运昌的麻烦。比如私自克扣张运昌跟凤莲的工分,把最苦累的活儿派遣给张运昌跟凤莲等等。有一次,田玉英实在忍受不下张运虎对她家人的欺压,就跑到张运虎家里,跟张运虎的娘王金玉大吵了一架。不过,张运虎一知道此事,就不受任何人劝阻地跑到凤莲家里,用镢头把凤莲正在做饭的铁锅给砸了一个窟窿。事后,凤莲怕张运虎伤及几个孩子,就硬是压制着要找张运虎拼命的张运昌,让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想,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凤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信念倒成了真。就在张运虎砸掉凤莲家的铁锅没多久,张运虎的一条腿就成了残废。
那是一个忙碌的麦收时节,村里的所有劳力都下了田。只有张运虎假装肚子不舒服,跟张铁三请了假回了村。在张运虎路过牲口屋时,看到两头驴在斗架。他一时兴起,开始挑逗起两头驴,好让两头驴斗得更狠些。就在这时,两头驴的战斗结束了。只是,张运虎并不尽兴,他上去就抓住了一头驴的尾巴,一边拉扯,一边嘴里喊着:“上,上,上......”不想就在这时,被他抓住尾巴的驴一个转身,在张运虎腿上上来就是一口。被驴咬住腿的张运虎,拼命的想把腿从驴嘴里挣脱出来,可越是挣扎,驴咬得越紧。足足有半个小时,张运虎的身上磨蹭的到处都是鲜血。这时,从田里回家来给孩子吃奶的凤莲,听到了牲口屋子里的声响。她往屋里一看,竟然看到了一身鲜血的张运虎正躺在地上。她看到张运虎的一条腿,被驴紧紧地咬在嘴里。凤莲一时间也着了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凤莲下意识地想到,肯定是这个心歹的恶老虎不使好,才被驴咬住的。这时,凤莲脑子里浮现出了张运虎欺压她跟张运昌的种种事迹,刹那间,她真是想转头走掉。不过,这时凤莲觉得,她不能走,这会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她得救人。凤莲迅敏地朝周围看了看,试图找到类似于棍子之类的东西,好把咬住张运虎一条腿的驴嘴打松开。可是凤莲看着紧紧咬住张运虎一条腿的驴嘴,实在咬得结实,她就想,对驴不能打,也不能急躁,必须慢慢地让驴放松警惕,松开嘴巴。凤莲看到牲口屋里有一草料垛,于是就走到草料垛前,上前抓起一把草料,然后拿到咬着张运虎一条腿的驴嘴旁。她一边口里说着:“驴儿松口,驴儿吃料,驴儿松口,驴儿吃料......”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驴的脖颈。驴好像从凤莲的细声软语跟轻柔的抚触中,感知到了安全,不一会儿,驴就松了口,去嚼草料了。凤莲见驴一松口,就立马跑到张运虎身后,从后背拖起张运虎,将他拉到了一块驴嘴够不着的空地上。她见张运虎的伤势严重,就跟张运虎说:“你先等着,我去叫人......”说着,凤莲就直奔田里喊人去了。
凤莲一路小跑,赶到田里喊来了人。等张运虎的娘王金玉,大哥张运龙,二哥张运青,还有村里几个其他男劳力赶到牲口屋时,只见张运虎一身血污,瘫软在地上。王金玉见儿子伤成如此模样,边将张运虎揽在怀里,边哭喊着:“我的儿,我的儿......”几个男劳力见状,纷纷提议赶紧送医院。
“找张床,捆上棍,抬着上医院吧。”
“看来腿是折了,不上城里,我看弄不成事。”
张运龙听完几个人的提议,紧慌地跑回了家。他从自家堂屋里搬出来一张木板床,在木板床两边绑上木棍,随之就扛着木板床去了牲口屋。几个人将张运虎抬到床上,张运龙说:“公社里没有能接骨头的大夫呀!只有进城了。”张运龙说完,身边的几个人纷纷点头,都说要接骨头只有上县医院了。
几个人抬起张运虎,等走到村街口时,村民们刚好下了田回村来。大家伙看着瘫软在床板上的张运虎,纷纷议论着张运虎腿折的经过。看着张运虎的惨状,有的人说着疼惜同情的话;有的人低声议论着张运虎从小就顽劣,说是栽跟头是迟早的事;还有跟张运虎动过武力的人,看着眼下的张运虎,是嘴上说着这意外很不幸,其实心里头正在暗自幸灾乐祸。这会子,凤莲跟张运昌也在人群里。他们夫妻俩听着村里人议论纷纷,都一语不发地看着。大家伙知道是凤莲先报的信,几个媳妇就纷纷询问她事情的经过。张运昌见状,碍于前些日子刚刚跟张运虎生了场大气,并不愿理会张运虎一家子,于是就转身走出人群,回了家。凤莲被几个媳妇围住,她们不停地对凤莲问东问西,凤莲就把自己发现张运虎被驴咬住腿时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述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凤莲推说家里有事要回家,就离开了人群。凤莲在回家的路上,整个脑子里浮现出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话。她一想到这句话,仿佛胸口淤积了好多年的憋屈,一下子全部的从胸口倾泻了出来。“奶奶的,该!”她吐出了这样一句,瞬间只觉得浑身轻松。不过,她又转念一想,自己跟张运虎这头恶老虎是同一个奶奶,又禁不住噗嗤一声笑了。
村里的几个男壮劳力抬着张运虎去了县城医院。这时县城的医疗条件有限,等县城的大夫给张运虎打了针,用手接了骨,开了药,就说让张运虎回家休养,这就算完事了。只不过接下来,张运虎一连吃药休养了一个多月,断掉的腿非但没有痊愈,反而伤势发展得更为严重了。一个月过去,张运虎的这条伤腿,已经肿胀的不成样子了。张运虎一家子人是想尽了办法,寻找了很多民间治疗骨伤的偏方,可结果就是不见效。这时,村里人就张运虎的腿伤众说不一。有人说,这腿肯定得截了,不然会要命的;有人说,就算找到神医,这腿也是废定了;还有人说,就算找到神医治好了腿,再想像以前一样,整天风风火火的,难了。在整个村里人,对张运虎一条腿的命运,左右拿不定主意时,田玉英远嫁商丘的大女儿素勤回家来了。当她知道近门人张运虎腿受伤的事后,就声称自己听说过婆家那边,有个顶好的骨科大夫,在治疗断胳膊断腿儿上,是一等一的高手。于是,就回到商丘,托她做卖馒头生意的丈夫,找到了这个骨科大夫。不久,就在素勤丈夫袁向学的引荐下,张运虎被家里人送到商丘,看了这个骨科大夫。结果,张运虎在这个骨科大夫的嘱托下,连贴了三个月的膏药,伤腿竟然能下床走路了。
张运虎腿伤虽然好了,可因为没有手术,再加上治疗延迟,也只能落得一条瘸腿。然而,这样的结果,在村里人看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若不是寻得神医,怕是连命早就没有了。按理说,张运虎治好了腿伤,最应该感激的就是他婶子田玉英一家人了。先是凤莲将他从驴口里救下来,再是素勤找大夫治了他的腿。可以说,他欠他婶子家的恩情,恐怕是后半辈子都还不清了。张运虎自能瘸着腿走路以后,并没有特意去感激张运昌一家人,只不过,等他再在村里走动时,先前身上那股子狠戾气不见了。在他能走路后的几个月里,村里人再没见他跟谁家置过气。就在这年秋收后的一天,张运虎在村子里突然不见了。据他母亲王金玉说,儿子是去投奔了一个远方亲戚。可就在张运虎消失后的整个冬天里,人们对他的销声匿迹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张运虎是像南蛮子一样去他乡乞讨去了;有的人说,张运虎瘸了腿,怕今后找不到媳妇,在村里没面子,才远走他乡谋求出路去了;还有人说,张运虎的命是张运昌一家人救回来的,他自个肯定是良心发现,觉得之前的很多行为愧对于张运昌一家人,所以没脸再在张庄待下去,这才出外谋求生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