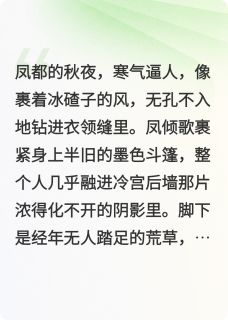---
次日,宣政殿。
巨大的蟠龙金柱支撑着高阔的穹顶,阳光透过精致的雕花窗棂,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却驱不散殿内凝重如铅的空气。朝臣们按品阶肃立两侧,鸦雀无声,只余下皇帝偶尔翻阅奏折时纸张摩擦的细微声响。高踞龙椅之上的凤帝,眉宇间积压着沉沉的倦色和挥之不去的阴霾,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冰冷的龙椅扶手,发出单调而压抑的“笃、笃”声。
兵部侍郎王崇,一个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的中年官员,正唾沫横飞,声音洪亮得几乎能震落梁上的灰尘:“陛下!北境赤狄狼子野心,陈兵十万于雁回关外,其势汹汹!边关八百里加急军报一日三至!此刻唯有与西凉国结下秦晋之好,方能得其强援,共御外侮!此乃社稷存亡之关键啊陛下!”他激动得脸上的肥肉都在颤动,“臣斗胆,请陛下速速下旨,为倾歌公主赐婚西凉三王子!以安边关将士之心,以固我凤朝国本!”
“王侍郎所言极是!”礼部尚书李庸立刻出列附和,山羊胡子一翘一翘,“西凉三王子英武不凡,倾歌公主端庄淑慧,实乃天作之合!和亲之举,古已有之,化干戈为玉帛,功在千秋!”
“臣附议!”
“臣亦附议!”
“请陛下速做决断!”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崇的话像点燃了一串炮仗,主和派、尤其那些与西凉有千丝万缕利益勾连的官员们纷纷出列,躬身附和,声浪几乎要将大殿的屋顶掀翻。他们口中是冠冕堂皇的“社稷”“国本”,眼神里闪烁的却是各自的小算盘——或为家族利益,或为政治投机,或纯粹是惧怕战争。
凤倾歌站在靠近丹陛的公主专属位置上,身姿笔直如青松。她今日穿着正式的宫装,繁复的绣纹和沉重的头饰压在身上,像一副无形的枷锁。宽大的袍袖下,她的手指死死攥紧,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带来尖锐的刺痛,才勉强维持住脸上那副近乎完美的、属于皇家公主的平静面具。胸中却似有岩浆在翻涌,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和亲?棋子?她凤倾歌的命运,岂能由这些人用几句轻飘飘的“社稷为重”就钉死在异国他乡的囚笼里?
那些激昂的陈词,在她听来,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在心上。她强迫自己将目光投向龙椅上的父皇。父皇的眼神疲惫而浑浊,在王崇等人慷慨激昂的陈述下,明显出现了动摇和犹豫。那敲击扶手的手指,节奏似乎更快了些。一股冰冷的绝望,开始从脚底蔓延上来。
就在这山呼海啸般的“附议”声中,一个清朗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懒散的声音,突兀地响起,不高,却奇异地穿透了整个大殿的喧嚣。
“王侍郎此言,请恕夜某不敢苟同。”
如同沸油锅里滴入了一滴冷水,整个宣政殿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的目光,惊愕地、探寻地、带着难以置信的疑惑,齐刷刷地聚焦到声音的源头——大殿角落,那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位置。
夜玄宸。
他依旧穿着那身低调的玄色锦袍,昨夜冷宫墙角的狼狈仿佛只是一场幻梦。他从容不迫地出列,走到大殿中央。阳光落在他身上,勾勒出挺拔颀长的轮廓。他微微躬身,姿态无可挑剔,却自有一股难以言喻的疏离与沉静。
“夜质子?”王崇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涌起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不耐烦,“此乃我凤朝国事,你一介质子,有何资格置喙?”语气中的鄙夷,毫不掩饰。
夜玄宸仿佛没听到那刺耳的“质子”二字,甚至唇角还噙着一丝极淡的笑意,目光平静地扫过王崇涨红的脸:“王侍郎言重了。夜某寄居凤都,受陛下庇护,感念于心。见诸位大人为国事殚精竭虑,夜某不才,也想略尽绵薄,说几句肺腑之言,或可查漏补缺,供陛下与诸位大人参详。”
他声音不疾不徐,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其一,王侍郎言,结亲西凉可得强援。然则,”他话锋一转,目光陡然锐利,“西凉三王子,乃西凉王继后所出,其母族势力单薄,其人在国内根基尚浅,且性情……颇为狂躁,屡有暴虐之名传出。西凉王年事已高,储位之争暗流汹涌。敢问王侍郎,将倾歌公主嫁与此人,是结盟,还是送羊入虎口?一旦西凉内乱,此人自身难保,所谓强援,岂非镜花水月?届时,我凤朝公主安危何在?国体颜面何存?”
王崇脸色一变,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夜玄宸所言,句句切中要害,点出了西凉三王子并非良配的致命缺陷,这正是他们主和派刻意回避或模糊的关键。
夜玄宸不给对方喘息之机,继续道,声音沉稳有力:“其二,王侍郎言,和亲可化干戈为玉帛。然而,赤狄陈兵十万,所求者,无非是岁币、粮草、乃至我凤朝北境膏腴之地!西凉国与赤狄,犬牙交错,多有摩擦,其国力尚不足以单独抗衡赤狄。即便结亲,西凉出兵相助,又能出几何?能解雁回关之围几分?其出兵条件,又需我凤朝付出何等代价?是割地,还是增加岁贡?此所谓援手,只怕代价远超其所得,最终依旧是饮鸩止渴,自损根基!”
他环视一周,目光扫过那些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主和派大臣,言辞越发犀利:“其三,也是最为紧要之处。我凤朝立国百年,以武立国,以文治国,将士用命,百姓归心!今强敌压境,不思整军备战,保家卫国,却将一国安危,系于一女子之身,寄望于他国施舍?此等做法,置我凤朝百万将士于何地?置边关浴血奋战的忠魂于何地?置天下百姓对我凤朝朝廷之信心于何地?!”
最后几句,夜玄宸的声音陡然拔高,字字铿锵,如同金铁交鸣,带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空旷的大殿内轰然回荡!他挺直脊背,玄衣如墨,整个人仿佛一柄骤然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军心民心一旦离散,纵有十次和亲,百次结盟,又能如何?!不过是苟延残喘,坐以待毙罢了!”
掷地有声!
偌大的宣政殿,陷入了一片死寂。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和某些人额角渗出的冷汗。主和派官员们脸色阵青阵白,王崇更是面如死灰,嘴唇哆嗦着,却再也吐不出一个有力的反驳字眼。夜玄宸的分析,剥开了“和亲”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内里**裸的虚弱、代价和耻辱!
龙椅上的凤帝,浑浊的眼睛里猛地爆射出一缕精光,敲击扶手的手指停了下来。他死死盯着大殿中央那个玄色的身影,眼神复杂难明。
凤倾歌站在丹陛旁,只觉得一股汹涌的热流猛地冲上眼眶,又被她死死压住。宽大袖袍下的手,早已松开,指尖却还在微微颤抖。她看着夜玄宸挺直的背影,看着他三言两语便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和亲派驳斥得体无完肤,看着他以质子之身,却敢在凤朝朝堂之上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强音!昨夜冷宫的冰冷算计与此刻朝堂的凛然风骨,在她脑中激烈碰撞。这个夜玄宸……他到底是谁?他想要什么?他为何要帮她?
巨大的困惑和一种难以言喻的震动席卷了她。然而,此刻占据心头的,更多的是绝处逢生的狂喜和一种前所未有的……悸动。他站在那里的样子,像一道撕裂阴霾的光。
朝堂的喧嚣暂时被夜玄宸的惊人之语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凤帝最终没有当场下旨,只沉着脸说了句“此事容后再议”,便宣布退朝。那沉甸甸的“再议”二字,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但至少,斩落的时刻被延迟了。
退朝的钟声敲响,沉闷的余音在殿宇间回荡。凤倾歌随着人流缓缓步出宣政殿高大的门槛,殿外刺目的阳光让她微微眯起了眼。然而,这份短暂的光明并未带来多少暖意,心头依旧压着那块名为“和亲”的巨石。她步履看似从容,实则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之上。
刚走出喧闹人群的包围圈,转入通往自己所居昭阳宫那条相对僻静的宫道,凤倾歌的脚步便下意识地加快了几分。只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地方,好好梳理这纷乱如麻的局面,想想如何应对父皇可能的“再议”。
宫道两旁是高大的朱红宫墙,投下深沉的阴影。阳光被切割成狭长的光带,落在平整的青石板上。就在她即将穿过一道月亮门时,一道颀长的身影如同从墙角的阴影里生长出来一般,悄无声息地挡在了她的正前方。
玄色锦袍,身姿挺拔,不是夜玄宸又是谁?
凤倾歌心头猛地一跳,脚步硬生生刹住,险些撞上去。她倏然抬头,对上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那里面没有了朝堂上的锐利锋芒,也没有了昨夜冷宫的冰冷杀机,只剩下一种近乎戏谑的平静,仿佛在欣赏她瞬间的错愕。
“公主殿下。”夜玄宸微微颔首,唇角勾起一个极浅的弧度,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凤倾歌耳中,“走得这般急,可是昨夜受了惊吓,心神未定?”他刻意加重了“昨夜”二字,目光意有所指地在她脸上逡巡。
凤倾歌只觉得一股热气瞬间涌上脸颊,是窘迫,更是被揭穿、被拿捏的恼怒。她强自镇定,挺直了背脊,冷下脸:“质子殿下何意?本宫听不懂。若无要事,还请让路。”她试图绕过他。
夜玄宸身形微动,再次恰到好处地挡住了她的去路,动作流畅自然得仿佛只是无意。他微微倾身,距离近得凤倾歌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如同雪后松针般的冷香。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却又无比清晰的调侃:“听不懂?那也无妨。只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她紧抿的唇,笑意加深,“朝堂之上,在下费尽唇舌,口干舌燥,替公主挡下了那桩……嗯,‘天作之合’。公主殿下素来明理,这出力之后的报酬,是不是也该结一下了?”
报酬?!
凤倾歌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她瞪着眼前这张俊美却无比可恶的脸,昨夜那坛泼出去的金叶子仿佛又在眼前闪耀,割得她心头滴血。朝堂上那番慷慨陈词,原来在这里等着她!她早该想到的!这个狡诈如狐的男人,怎么可能白白出力!
“报酬?”凤倾歌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冰碴子,“质子殿下想要什么?金银?本宫昨夜‘晒月亮’所得,不是都‘慷慨’地赠予殿下了吗?”她刻意咬重“晒月亮”和“慷慨”几个字,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夜玄宸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低沉悦耳,却听得凤倾歌心头火起。“公主说笑了。昨夜那些‘月光’,不是都拿去照亮侍卫们的眼睛了吗?在下可是一枚也没捡着。”他摇了摇头,一副“我很亏”的表情,随即目光变得幽深,直直地望进凤倾歌眼底,慢悠悠地道:“在下所求不多。只是觉得公主殿下身上……似乎总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比如,深更半夜,冷宫寻宝?”
凤倾歌的心猛地一沉。他果然没忘!而且以此要挟!寒意瞬间取代了怒火。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质子殿下管得太宽了。”她声音冰冷,“本宫行事,自有分寸。昨夜之事,不过是一场误会。至于报酬……”她飞快地在脑中权衡着。给他什么?给多了,显得心虚;给少了,打发了这个无赖?不,他显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电光火石间,凤倾歌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指尖触到一块温润的硬物——那是她一直随身佩戴的凤纹玉佩,羊脂白玉,触手生温,雕工精湛,是母妃留给她的遗物,价值不菲,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公主的身份。
这是她身上此刻最显眼、也最具“价值”的东西。给他?她心中剧痛,万般不舍。但不给,眼前这个握着把柄的男人,会轻易放过她吗?
夜玄宸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她腰间那细微的动作,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和玩味,好整以暇地看着她挣扎。
凤倾歌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中只剩下冰冷的决绝。她猛地抬手,一把扯下腰间的玉佩。动作带着一股狠劲,连带着束腰的丝绦都被扯得一松。
啪嗒。
温润的白玉落在她掌心。她看也不看,仿佛丢弃一件碍眼的垃圾,抬手就将玉佩递到夜玄宸面前。阳光透过镂空的凤纹,在玉佩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也映亮了她眼中压抑的怒火和屈辱。
“这个,够买你闭嘴了吗?”她的声音压得极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水里捞出来,带着刺骨的寒意,死死盯着夜玄宸的眼睛,“拿着它,昨夜之事,朝堂之言,统统给本宫烂在肚子里!若再有多一句废话……”她逼近一步,声音如同淬毒的冰刃,“本宫保证,下次泼出去的,就不只是金叶子了!”
玉佩静静地躺在凤倾歌白皙的掌心,温润的羊脂白玉在宫墙的阴影下,泛着内敛柔和的光泽,那展翅欲飞的凤纹雕工精细得近乎神韵。夜玄宸的目光落在玉佩上,没有立刻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