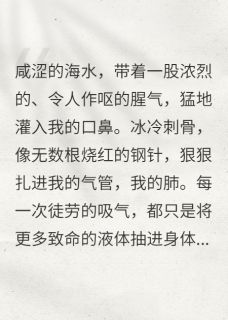咸涩的海水,带着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腥气,猛地灌入我的口鼻。冰冷刺骨,
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我的气管,我的肺。每一次徒劳的吸气,
都只是将更多致命的液体抽进身体深处。窒息。那是比死亡本身更恐怖的酷刑。
身体沉重得如同灌满了铅,被无形的力量拽着,急速地向着无底的深渊沉坠。头顶的光,
那片模糊摇曳的、象征生的光晕,越来越远,越来越暗。刺骨的寒意并非只来自海水,
更源于那只按在我头顶的手——那只曾温柔抚过我脸颊,也曾信誓旦旦许诺一生一世的手。
顾承泽的手。巨大的推力,带着一种冷酷的决绝。他在推我下去。
视野彻底被翻涌的、墨绿色的黑暗吞噬。最后一点意识里,没有愤怒的咆哮,
只有死寂般的冰冷疑问:为什么?黑暗,黏稠得如同凝固的血块,包裹着一切。
“……念慈……沈念慈……”声音断断续续,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
微弱地撞击着我的耳膜。这声音…有些熟悉,
却又带着一种令人不适的、刻意压低的悲伤腔调。是顾承泽。
“……我可怜的妻子……你怎么就……”碎片般的声音顽强地穿透那层厚重的死亡帷幕,
固执地钻进我混沌的意识深处。每一个字都像带着冰渣,刮擦着我仅存的知觉。
巨大的、尖锐的痛苦猛地攫住了我的头颅。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凿子,
正一下下凶狠地劈凿着我的头骨。这剧烈的痛楚像一道撕裂黑暗的闪电,
瞬间劈开了那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混沌。意识,被强行拽了回来。
眼皮沉重得如同压着千钧巨石,每一次试图掀开都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浓密的睫毛颤抖着,
如同濒死的蝶翼。眼前先是一片模糊的光晕,夹杂着晃动的人影轮廓,
像是隔着一层不断晃动的水波。几秒后,那层水幕才艰难地褪去,景象开始缓慢地聚焦。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方垂落下来的、层层叠叠的黑色帷幔。厚重的丝绒,沉甸甸地悬挂着,
吸走了周遭大部分的光线,营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极其浓郁的、甜腻到发齁的花香——是白菊和百合混合的味道,
中间又隐隐透着一丝防腐剂冰冷刺鼻的气息。是灵堂。我自己的灵堂。
这个认知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神经上。心脏在胸腔里猛地一缩,
随即疯狂地擂动起来,几乎要撞碎我的肋骨。血液在四肢百骸里瞬间凝固,
又在下一秒逆流冲上头顶。我回来了。回到了这场为我精心准备的、盛大而虚伪的葬礼现场。
目光艰难地转动,如同锈蚀的齿轮。灵堂正前方,
我的巨幅黑白遗像悬挂在层层叠叠的白色花圈中央。照片上的我,笑容温婉娴静,眼神清澈,
带着一种对世事毫无防备的天真。如今这笑容在缭绕的香烛烟雾里,显得如此空洞而讽刺。
遗像下方,摆放着一口深色的、沉重的棺木。盖子敞开着,里面空空如也——我的“遗体”,
大概还沉睡在冰冷的海底,被鱼虾啃噬。顾承泽对外宣称的,自然是“遗体尚未寻获”。
视线终于捕捉到了声音的来源。顾承泽就站在距离棺木几步之遥的地方。
一身剪裁完美、面料昂贵的黑色西装,衬得他身形挺拔,宽肩窄腰。他微微低着头,
侧脸对着我的方向,线条依旧英俊得无可挑剔。几缕精心打理过的额发垂落,
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一点眉眼,营造出一种深沉的哀恸感。他的肩膀似乎在微微耸动,
像是在极力压抑着巨大的悲伤。他的右手,紧紧握着另一只手。那是一只女人的手。白皙,
纤细,柔弱无骨。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涂着极其淡雅的珍珠色蔻丹。此刻,
那只手正被顾承泽牢牢地包裹在掌心,传递着一种无声的依赖与抚慰。
我的目光顺着那只手往上移。一张脸。一张与我遗像上的面容,几乎有九分相似的脸。
同样精致的眉眼,同样小巧的鼻尖,同样略显单薄的唇形。只是,这张脸上此刻毫无血色,
苍白得像一张细腻的薄纸,透着一股病态的、惹人怜惜的脆弱。
那双和我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长长的睫毛湿漉漉地黏在一起,
随着她细微的抽泣而轻轻颤抖。沈念薇。我那个在十六岁那年,
因为一场意外而“失踪”的双胞胎妹妹。上辈子直到沉入海底,
被无边的黑暗和冰冷彻底吞噬的那一刻,我都不曾知晓这个真相。
顾承泽深藏心底、念念不忘的白月光,那个他偶尔醉酒后才会流露出痛苦思念的人,
竟然就是我这个流落在外、音讯全无的亲妹妹!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而布满尖刺的手狠狠攥住,然后用力地拧绞。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又在下一秒冻结,留下针扎般的刺痛感,从指尖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原来如此!
原来我的存在,我那场耗尽心血的盛大婚礼,我沈念慈作为沈家唯一继承人这个身份本身,
都不过是为沈念薇最终回归铺就的一条光鲜亮丽的红毯!而我的死亡,
就是为这位真正的“公主”腾出位置、扫清障碍的最后一步。多么精巧的棋局!
多么冷酷的算计!指甲深深陷入掌心,那点微薄的刺痛感,像一道微弱的电流,
勉强维系着我摇摇欲坠的理智,阻止我当场发出厉鬼般的尖啸。一股腥甜的气息涌上喉头,
又被我死死地压了回去。“念薇,”顾承泽的声音再次响起,压得极低,
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饱含磁性的沙哑。他微微侧过头,
目光深情而痛楚地落在沈念薇梨花带雨的脸上,“别太难过,
你姐姐……她也不愿看到你这样。”他握着沈念薇的手,极其自然地、安抚性地紧了紧,
拇指在她冰凉的手背上温柔地摩挲了一下。“你身体本来就弱,这几天熬下来,怎么受得了?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心疼,每一个字都像是蘸了蜜糖的毒针,
精准地刺穿我刚刚重生的耳膜,“以后的日子还长,
沈家……还有你姐姐留下的担子……都需要你慢慢扛起来。
”他的话语在这里微妙地停顿了一下,目光从沈念薇脸上移开,
自然地扫过灵堂内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肃穆、明显是沈家元老和信托基金律师模样的人,
最后又落回到沈念薇脸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替她做主的意味:“念薇身体弱,
以后沈家的遗产,就由你代管吧。这也是为了念慈的心血着想。”代管?呵!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代管”!一股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怒火瞬间席卷了我。
它不再是刚才那种撕裂心肺的剧痛,而是一种沉凝的、如同万年玄冰般的杀意。
它冻结了我所有的血液,只留下最清醒、最冷酷的算计。上辈子,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被最信任的丈夫亲手推入地狱,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这一次,我回来了。带着地狱的烙印和滔天的恨意回来了。顾承泽,沈念薇,这场戏,
才刚刚开始。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百倍、千倍的代价。我会亲手,
把你们也拖进那片冰冷绝望的海底深渊。就在顾承泽那句虚伪至极的“代管”话音落下,
沈念薇抬起那张与我酷似的、泪痕斑驳的脸,
正要开口回应这份“深情厚谊”的瞬间——“呃……”一声极其微弱、沙哑,
仿佛濒死之人喉管里挤出的**,突兀地打破了灵堂里庄严肃穆、各怀鬼胎的寂静。
声音的来源,正是那口敞开着、空空如也的棺木后方,那片被巨大黑色帷幔阴影笼罩的角落!
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或真或假的啜泣声、低声的交谈、甚至背景里循环播放的哀乐,
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断了喉咙。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几十道目光,带着难以置信的惊骇、茫然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
齐刷刷地投向声音发出的黑暗角落。站在棺木旁的顾承泽,身体猛地一僵。
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原本精心维持的沉痛面具,在刹那间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
瞳孔骤然收缩,里面清晰地映照出极致的震惊和……一丝来不及掩饰的、深可见骨的恐慌!
他握着沈念薇的那只手,无意识地收紧,力道之大,让沈念薇痛得低呼一声,
下意识地想抽回手。而沈念薇,那张苍白病弱、惹人怜惜的脸,在听到那声**的瞬间,
血色彻底褪尽,连嘴唇都变成了骇人的青灰色。她眼中泫然欲泣的泪水瞬间凝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同见了厉鬼般的、纯粹的、无法控制的惊惧。她像是被抽掉了所有骨头,
身体晃了晃,若不是顾承泽下意识地还死死抓着她的手,几乎就要当场瘫软下去。
“谁…谁在那里?!”一个站在前排的沈家远房长辈,声音发颤地喊道,
带着无法置信的惊疑。黑色的丝绒帷幔,厚重地垂落着,在角落里堆积出更深的阴影。此刻,
那片阴影剧烈地蠕动了一下。紧接着,一只苍白得毫无血色、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的手,
颤巍巍地从帷幔的缝隙里伸了出来!那只手枯瘦、冰冷,皮肤薄得几乎透明,
清晰地映出底下青紫色的血管。它五指张开,无力地搭在冰冷的地板上,指尖微微蜷曲,
似乎想抓住什么,又像是溺水者最后的挣扎。“嗬…嗬……”更为清晰的、艰难喘息的声音,
从帷幔后传了出来。“鬼…鬼啊!”一个胆子稍小的女眷,终于承受不住这诡异的冲击,
发出一声短促刺耳的尖叫,猛地捂住了嘴,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整个灵堂彻底炸开了锅!惊疑、恐惧、难以置信的低语如同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
刚才还肃穆沉重的葬礼现场,瞬间变得混乱不堪。顾承泽脸上的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
他死死地盯着那只从帷幔后伸出的、枯瘦苍白的手,眼神剧烈地闪烁着,惊疑不定,
仿佛在拼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荒谬的幻觉。他握着沈念薇的手,
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带着一种梦呓般的恍惚。就在这时,那只苍白的手猛地用力,抓住了帷幔的边缘!哗啦!
厚重的黑色帷幔被那只枯瘦的手猛地向旁边扯开!阴影散去。一个身影,
蜷缩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一身纯白的丝绸病号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过于瘦削的身体上,
空荡荡的,更显得形销骨立。长长的、湿漉漉的黑发凌乱地黏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
如同海藻般纠缠。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破风箱般的嗬嗬声,
仿佛随时都会再次断绝。当那张脸完全暴露在灵堂惨白的灯光下时——轰!
如同在滚油里泼进了一瓢冰水,灵堂内的空气彻底被点燃、炸裂!“念慈?!
”沈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叔公,猛地拄着拐杖上前一步,浑浊的老眼瞪得滚圆,失声惊呼,
声音都变了调。“天哪!是大**!是沈念慈!”有人尖叫着确认。“她…她没死?!
她还活着?!”难以置信的狂喜瞬间冲垮了部分沈家人的理智。那张脸,
除了极度的苍白和消瘦,除了被海水浸泡过、被生死折磨过的憔悴痕迹,
分明就是遗像上的沈念慈!活生生的沈念慈!顾承泽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巨锤狠狠击中,
高大的身体猛地晃了晃,不由自主地松开了紧握着沈念薇的手,踉跄着后退了半步。
他死死地盯着地上那个蜷缩的身影,英俊的面容扭曲着,
震惊、茫然、恐惧、还有一丝被彻底打乱计划的狂怒,在他眼中疯狂地交织翻滚。
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
沈念薇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在顾承泽松开她的瞬间,她像是失去了唯一的支撑,双腿一软,
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所有力气,软绵绵地瘫倒下去,
幸亏旁边一个同样震惊呆滞的佣人下意识地扶了一把,才没有狼狈地摔在地上。
她瘫在佣人怀里,身体筛糠般剧烈地颤抖,目光死死地锁住地上那个“死而复生”的女人,
眼神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如同看到了从地狱爬回来索命的恶鬼。那眼神深处,除了恐惧,
更有一种精心谋划即将毁于一旦的绝望和怨毒。“救…救我…”地上的人影,艰难地抬起头,
露出一双因为极度虚弱而显得异常空洞茫然的眼睛。
她的目光在混乱的人群中毫无焦点地扫过,最后,
似乎无意识地落在了顾承泽那张写满惊骇的脸上。她的嘴唇翕动着,
发出极其微弱、气若游丝的声音,
个字都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承泽……好冷……海水……好冷……”“承泽”两个字,
如同两道淬了冰的闪电,狠狠劈在顾承泽的心上!他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尽,
连嘴唇都失去了颜色。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紧了他的心脏,几乎让他窒息。
她记得!她记得落海!她记得是他推的她?!这个念头如同最恐怖的魔咒,瞬间攫住了他,
让他浑身冰冷,如坠冰窟。但就在下一秒,地上那女人空洞茫然的目光,又缓缓移开,
仿佛刚才那声呼唤只是濒死时无意识的呓语。她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弱的身体蜷缩得更紧,
像一只被遗弃在寒风中的幼兽,只剩下本能的、对生的微弱渴望。顾承泽紧绷到极限的神经,
因为这茫然的移开,稍稍松动了一丝。那几乎将他淹没的恐惧,
暂时被一种更强烈的、想要掌控局面的本能压下。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
脸上瞬间切换回一个丈夫劫后余生的、混杂着巨大惊喜和悲痛的表情。“念慈!!
”他猛地扑了过去,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他单膝跪在冰冷的地面上,伸出双臂,
似乎想将地上那个瑟瑟发抖、脆弱不堪的身体紧紧拥入怀中。
他的动作带着一种夸张的、劫后余生的激动,声音因为“激动”而哽咽颤抖,“老天!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他的双臂即将碰到我的身体。
那股熟悉的、曾经让我无比眷恋的雪松古龙水味道,
混杂着他身上此刻散发出的、如同困兽般的焦躁气息,扑面而来。令人作呕。
我猛地蜷缩得更紧,身体剧烈地一颤,
喉咙里发出一声惊恐至极的、如同小兽被踩到尾巴般的呜咽。我像是被他的触碰惊吓到,
拼命地向后缩去,后背重重地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那双空洞的眼睛里,
瞬间盈满了泪水,充满了纯粹的、巨大的、仿佛面对洪水猛兽般的恐惧。“别…别过来!
”我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哭腔和无法抑制的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是谁?离我远点!走开!”我的身体抖得如同秋风中的最后一片枯叶,
眼神惊恐地扫过他,又飞快地扫过周围所有试图靠近的人,最后,
目光茫然无措地定格在灵堂中央那幅巨大的、属于我自己的黑白遗像上。“那…那是谁?
”我的声音带着孩童般的懵懂和巨大的困惑,指着遗像,
泪水大颗大颗地从空洞的眼眶里滚落,砸在冰冷的地板上,“她…她怎么和我长得一样?
她死了吗?你们…你们是谁?这里…是哪里?”我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
侧躺在冰冷的地板上,长发散乱,遮住了小半张脸,
也遮住了我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冰冷刺骨的讥诮。失忆。一个被丈夫亲手推入深海,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被冰冷海水和濒死恐惧彻底摧毁了记忆的可怜女人。顾承泽伸出的双臂,
僵在了半空中。他脸上的“狂喜”和“悲痛”瞬间凝固,像是戴上了一副劣质的石膏面具。
那双深邃的、曾经让我沉溺其中的眼睛,此刻清晰地倒映着我惊恐万状、茫然无助的脸。
他眼底翻涌的情绪极其复杂——有被当众拒绝的难堪,有面对这“意外”局面的措手不及,
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松弛,以及一丝迅速升腾起的、冰冷的算计。失忆?
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眼前的迷雾,瞬间照亮了另一条路。
一条或许比直接处理掉一个“恢复记忆”的沈念慈,更为便捷、更少风险的路。
他僵硬的表情只持续了一瞬。下一秒,
那英俊的脸上便迅速堆砌起更深的、足以令人心碎的痛惜和自责。
他缓缓地收回僵在半空的手,改为轻柔地、小心翼翼地虚护在我身前,
仿佛怕惊吓到我这只受惊的鸟雀。他的声音刻意放得极其温柔,
心颤的沙哑和哽咽:“念慈…念慈别怕…是我…我是承泽啊…我是你的丈夫…”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一种饱含深情的、痛苦万分的眼神望着我,
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他这些天所承受的“巨大折磨”。
“你受了惊吓…坠海…一定是伤到头了…”他语气沉痛,每一个字都像是浸透了泪水,
“别怕,一切都过去了,我会保护你,我会找最好的医生…你会好起来的…”他抬起头,
目光扫过周围惊疑不定、议论纷纷的沈家族人和宾客,
脸上带着一种沉痛而坚定的、属于一家之主的责任感:“快!叫救护车!不,
立刻联系陈院长,请他亲自带医疗团队到家里来!快!”他对着身边的助理厉声吩咐,
语气急促,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助理如梦初醒,慌忙掏出手机去安排。顾承泽的视线,
看似不经意地,越过混乱的人群,
落在了依旧瘫软在佣人怀里、脸色惨白如纸、眼神空洞涣散的沈念薇身上。
他的眼神极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带着一丝警告和安抚的意味,快得几乎让人无法捕捉。
随即,他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是对着我,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灵堂:“念薇,
你也别担心了,你姐姐福大命大,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
”他刻意加重了“福大命大”和“喜事”几个字,像是在提醒沈念薇,
也像是在安抚那些心思各异的沈家人,“快过来看看你姐姐!”沈念薇的身体猛地一颤。
顾承泽那看似温和、实则暗藏命令的眼神,像一根冰冷的针,
刺破了她因过度恐惧而麻木的外壳。她猛地回过神,那双酷似我的眼睛里,
残留的惊惧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
被一种更加复杂、更加汹涌的情绪取代——那是极度的不甘,是计划被打乱的焦躁,
是面对我这“死而复生”正主时无法掩饰的怨毒!她死死地咬着下唇,力道之大,
几乎要咬出血来。指甲深深掐进扶着她那个佣人的手臂,惹得佣人吃痛地瑟缩了一下。
她强撑着几乎虚脱的身体,在佣人的搀扶下,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每一步,
都走得无比沉重。每一步,都像是在走向她最不愿面对的噩梦。终于,
她停在了距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她的身体依旧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脸色比身上的黑色丧服还要惨白。她垂下眼睑,浓密的睫毛剧烈地颤抖着,
遮住了眼底翻腾的恨意。再次抬起眼时,那双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劫后余生的狂喜和激动。“姐…姐姐?”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颤抖得厉害,伸出一只同样苍白纤细的手,似乎想要触碰我,
又因为我的“惊恐”而怯怯地停在半空。她的表演堪称完美,
将一个饱受打击、骤然见到至亲生还而激动到不知所措的妹妹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姐姐!真的是你!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她的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滚滚而落,
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她说着,身体晃了晃,
似乎又要晕倒,旁边的佣人连忙用力扶住她。我蜷缩在冰冷的墙角,身体依旧在瑟瑟发抖,
像一只被遗弃在暴风雨中的幼猫。面对沈念薇那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呼唤和泪水,
我空洞的眼神只是茫然地扫过她那张与我酷似的脸,没有任何聚焦,也没有丝毫触动。
仿佛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的目光掠过她伸出的、想要触碰我的手,最后,
却像被什么吸引住似的,停留在了她的右手上。她的无名指。那里,戴着一枚戒指。
戒指的款式极其简约,却奢华内敛。指环是纯净度极高的铂金,被打磨成柔和的曲线,
完美贴合指根。戒托的设计更是别具匠心,并非传统的爪镶,
而是用极其细密精致的铂金丝线,如同藤蔓般温柔地缠绕包裹着中央那颗主石。
那主石在灵堂惨白的灯光下,
折射出令人心悸的光芒——一颗纯净无暇、切割完美、足足超过五克拉的椭圆形蓝钻!
深邃、浓郁的矢车菊蓝,像凝固了最神秘海域的一滴海水。那蓝色之中,
仿佛蕴藏着星辰与深渊,随着光线的流转,时而静谧幽深,时而迸发出璀璨夺目的火彩。
它的光芒太过独特,太过耀眼,以至于周围那些吊唁宾客佩戴的、原本也算价值不菲的珠宝,
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沦为了可笑的陪衬。那是“海洋之心”。
我母亲——沈家上一代真正的掌权者,
商界叱咤风云、手腕强硬得令无数男人都为之折服的传奇女性——留给我最珍贵的遗物之一。
也是我沈念慈身份的象征。它本该戴在我的无名指上,作为我新婚的见证。可现在,
它却如此刺眼地、堂而皇之地,戴在了沈念薇的手指上!
在我尸骨未寒(至少在他们认知里是如此)的葬礼上!
一股冰冷的、带着血腥味的怒火瞬间冲上我的头顶,几乎要冲破我精心维持的“失忆”外壳!
指甲再次深深陷入掌心,那点刺痛让我勉强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我猛地抬起头,
空洞茫然的眼神死死地钉在那枚璀璨夺目的蓝钻戒指上。我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困兽般的急促喘息。我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
似乎在努力地想要表达什么,却又因为极度的“混乱”和“恐惧”而组织不起语言。
“那…那个……”我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孩童发现新奇事物般的、纯粹的困惑和执拗。
我颤抖地抬起枯瘦的手指,直直地指向沈念薇无名指上那枚光芒四射的“海洋之心”。
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无法理解的茫然,眉头紧紧皱起,
像是在拼命回忆着什么极其重要的、却又被迷雾笼罩的东西。“戒指……”我喃喃地重复着,
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好亮……好蓝……像海……”“海……”这个字眼像是一把钥匙,
猛地捅开了我记忆深处某个混乱的闸门。我的眼神骤然变得极度惊恐,
仿佛看到了最可怕的景象。身体猛地向后蜷缩,后背重重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海!
水!好冷!”我失声尖叫起来,声音尖利刺耳,充满了纯粹的、濒死的恐惧,“推我!
有人推我!好黑!好冷!”我的尖叫如同最锋利的刀子,
瞬间划破了灵堂里刚刚因为“失忆”而稍稍平复的诡异气氛!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充满了惊疑和探究。顾承泽的脸色在听到“推我”两个字时,
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如同被泼了一层青灰色的油漆。他的眼神锐利如刀,死死地盯着我,
试图从我脸上那混乱惊恐的表情中分辨出真假。他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指节捏得发白。
沈念薇更是如同被一道惊雷劈中!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连嘴唇都失去了最后一丝颜色。她戴着“海洋之心”的那只手,像是被烙铁烫到一般,
猛地缩了回去,下意识地藏到了身后!她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如果不是佣人死死搀扶,
几乎又要瘫倒。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极致的惊恐和心虚,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随时会揭穿她所有伪装的恶魔。“念慈!念慈别怕!别怕!”顾承泽反应极快,
立刻扑上来,试图再次安抚我。这一次,他不敢再贸然触碰我,只是半跪在我身前,
张开双臂做出保护的姿态,声音急促而带着一种强压下的慌乱,“没有人推你!是意外!
是船上的意外!风浪太大,你不小心掉下去的!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你看,你现在安全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严厉地示意旁边的佣人和医护人员,“快!大**情绪太激动了!
镇定剂!先让大**安静下来!”混乱之中,
我被他那刻意拔高的声音和周围涌上的人影包围。在他们试图按住我注射镇定剂之前,
我的目光,透过人群的缝隙,再次精准地、如同淬毒的冰锥般,
刺向沈念薇那只藏在身后的手。我的嘴唇无声地翕动了几下,用只有我自己能听清的气音,
吐出几个字:“我的戒指……”随即,在针头刺入皮肤的冰冷触感传来,
意识被强行拖入黑暗的瞬间,我对着沈念薇那张写满惊惧的脸,
嘴角极其缓慢地、极其微弱地向上扯动了一下。那是一个空洞茫然表情下,
一闪而逝的、冰冷到骨髓深处的微笑。消毒水的味道浓烈刺鼻,霸道地占据着每一寸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