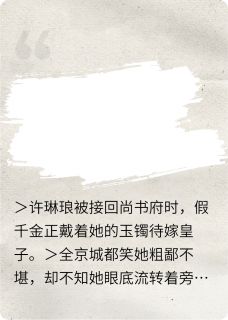>许琳琅被接回尚书府时,假千金正戴着她的玉镯待嫁皇子。>全京城都笑她粗鄙不堪,
却不知她眼底流转着旁人看不见的金芒——>那玉镯在吸食全族气运供养假千金。>“妹妹,
这福气送你。”她含笑捏碎邪器。>假千金当场吐血昏迷,未婚夫连夜退婚。
>许琳琅转身撞进九皇叔怀里,瞥见他眉间将死的灰气。>“王爷,想活命吗?
”她指尖划过男人滚动的喉结,“拿正妃之位来换。”>后来九皇叔踏着血路登基那日,
却跪在她裙边轻咬耳垂:>“琳琅,这龙椅烫得慌...你给朕生个太子暖暖?
”---夺我气运?反手虐哭假千金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砸在青石板上,
溅起浑浊的水花,也溅湿了许琳琅脚上那双露了脚趾的破草鞋。她没撑伞,
只裹着一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旧衣,
孤零零地站在尚书府那两扇紧闭的、朱漆剥落的角门前。风又冷又硬,
卷着雨丝直往她单薄的领口里钻,她下意识地抱紧了双臂,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一个穿着体面绸缎、梳着油光水滑发髻的管事婆子从旁边的小门里探出半个身子,
脸上堆着笑,眼底却没什么温度,声音像掺了沙子:“哎哟,大**,您可算到了!
快请进快请进,老爷夫人都在花厅等着呢!这雨大的,可别淋坏了身子骨。
”她嘴上说着关切的话,身子却没挪动半分,
眼神像探照灯似的在许琳琅身上那身粗陋的衣裳和沾满泥泞的鞋子上来回扫了好几遍,
嘴角几不可察地往下瞥了瞥,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轻蔑。许琳琅没应声,
只沉默地跟在她后面。雨水顺着她湿透的鬓发滑下来,流过她苍白瘦削的脸颊,
带来冰冷的刺痛。角门后面是一条狭窄的甬道,
空气里弥漫着雨水混合着青苔和某种陈年木头腐朽的气息。甬道的尽头,豁然开朗,
眼前是一个气派非凡的大院落。抄手游廊曲折蜿蜒,雕梁画栋在雨幕中依然透出奢靡的轮廓。
几个穿着鲜艳绸裙的丫鬟抱着东西匆匆走过,裙角翻飞,带起一阵香风。
她们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许琳琅,随即又飞快地移开,彼此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
嘴角挂着无声的讥诮。“啧,真是…一股子泥腥味儿。
”一个梳着双丫髻的小丫鬟用帕子掩着鼻子,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许琳琅听见。
“快走快走,别沾了晦气。”另一个赶紧拉着她快步走开。那些细碎的议论和鄙夷的目光,
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许琳琅身上。她只是垂下眼睫,
盯着自己沾满泥水的脚尖,一步一步,踏在光洁得能照出人影的青砖地上。那砖地真凉啊,
寒气透过湿透的草鞋底,直往骨头缝里钻。花厅里暖意融融,熏笼里燃着上好的银丝炭,
散发出甜腻的暖香。主位上端坐着尚书许文远和他的夫人柳氏。许文远穿着深色锦袍,
面容严肃,眉头微蹙,看着走进来的许琳琅,眼神复杂,有审视,有疏离,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柳氏保养得宜的脸上堆着笑容,但那笑意只浮在表面,
眼底深处是冰凉的打量,甚至还带着点挑剔的不耐烦。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少女,
那就是许明珠。许明珠穿着时下最名贵的云锦裁成的衣裙,
水粉色的料子上用金线绣着大朵大朵的海棠,华贵得晃眼。她生得极美,肌肤胜雪,
眉眼精致如画,尤其是眉心一点天生的胭脂痣,更添了几分楚楚可怜的风韵。
此刻她依在柳氏身边,姿态亲昵自然,仿佛天生就该是这个位置的主人。她的手腕上,
一只翠绿欲滴、水头极足的玉镯随着她轻轻摩挲柳氏衣袖的动作微微晃动,
那镯子通透得几乎毫无杂质,在暖黄的灯光下流转着温润而神秘的光泽。许琳琅的目光,
在接触到那只玉镯的刹那,猛地一凝。旁人看不见,但在她的眼底深处,
倏然亮起两点细碎的金芒,如同暗夜里骤然点燃的星火。刹那间,世界在她眼中变了模样。
一层粘稠、污浊、如同活物般缓缓蠕动的黑灰色雾气,沉沉地笼罩在整个花厅之上,
压得人喘不过气。这雾气仿佛有生命,丝丝缕缕,正源源不断地从端坐的许文远、柳氏,
以及厅内侍立着的几个心腹仆妇身上被抽离出来。许文远头顶的雾气颜色最深,
带着一种沉沉的暮气;柳氏身上的则显得浮华而脆弱;仆妇们身上的则稀薄些,
但同样带着劳碌的灰败。所有的雾气,都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
疯狂地汇聚向同一个地方——许明珠腕间那只翠绿通透的玉镯!
那玉镯在她眼中不再是温润的饰品,它像一个贪婪的漩涡,一个无底的深渊,
正疯狂地吞噬着、转化着那些象征着健康、寿命、福泽乃至家族根基的“气”。
被它吞噬的灰黑雾气,在镯体内部流转一圈,
竟被淬炼成一种妖异的、带着不祥血色的淡红光芒,丝丝缕缕,又反过来注入许明珠的身体。
许明珠整个人,在她那双能窥破虚妄的眼中,
正被一层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刺眼的血红色光晕包裹着。那红光映衬着她娇美的脸庞,
却透出一种令人心悸的邪异。她头顶的气运之柱,粗壮得如同实质,红得发紫,紫中带黑,
散发着掠夺而来的、令人作呕的“强盛”。而与之形成惨烈对比的,
是许文远头顶那根气运柱,原本应有的代表官运的深紫色已黯淡无光,
柱体上布满了蛛网般的灰黑色裂纹,仿佛随时会崩塌碎裂,透出浓重的衰败死气。
柳氏的更是虚浮不定,摇摇欲坠。许琳琅的心,如同被一只冰冷的铁手狠狠攥住,
几乎无法跳动。原来如此!这就是她从小被弃于乡野,受尽欺凌的真相?
这就是许家近年来屡遭打击、门庭渐颓的根源?她这所谓的“家”,
早已成了这鸠占鹊巢的假货和她手腕上那邪物的养料场!“琳琅?
”柳氏带着一丝刻意的温和开口,打断了许琳琅死寂的凝视,“快过来,让母亲好好看看你。
可怜见的,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她伸出手,作势要拉许琳琅。许琳琅却像没听见,
也没看见那只伸过来的手。她的目光,沉沉地落在许明珠脸上,
那双刚刚流转过金芒的眼眸此刻深如寒潭,里面没有任何初见的激动或怯懦,
只有一片冻彻骨髓的冰冷。许明珠被她看得心头莫名一悸,那眼神让她极其不舒服,
仿佛自己所有隐藏的污秽都被瞬间看穿。她下意识地抚摸着腕上的玉镯,
那冰凉的触感给了她一丝底气。她扬起一个带着明显优越感的、甚至带着点怜悯的笑容,
声音娇柔得能滴出水来:“这就是姐姐吧?一路辛苦了。姐姐别拘束,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她站起身,姿态优雅地朝许琳琅走来,仿佛要展现姐妹情深,
“妹妹给你倒杯热茶暖暖身子。”她莲步轻移,走到许琳琅面前,手里端着一个白瓷茶杯,
热气袅袅。就在她要将茶杯递过来的瞬间,手腕却极其突兀地一抖,那滚烫的茶水连同杯子,
直直地朝着许琳琅的手泼了过去!“啊——!”许明珠自己先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
身体同时像失去重心般猛地向后倒去,姿态柔弱无助,仿佛被一股大力狠狠推搡。“小心!
”柳氏失声尖叫,猛地站了起来。“明珠!”许文远也脸色一变。
滚烫的茶水大半泼在了许琳琅下意识抬起来格挡的手背上。一阵钻心的剧痛袭来,
皮肤瞬间变得通红,**辣地疼。茶杯“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碎瓷片四溅。
许明珠则“柔弱”地跌坐在地,捂着胸口,眼圈瞬间就红了,泪水说来就来,
悬在长长的睫毛上欲落未落,显得无比委屈和惊恐。她抬起泪眼朦胧的脸,
看向许文远和柳氏,声音带着颤抖的哭腔:“爹,娘……姐姐她……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只是想给她倒杯茶……她,她为何要推我?”她一边说,
一边有意无意地将那只戴着玉镯的手腕露在显眼处,翠色映着泪光,更显得她楚楚可怜,
而许琳琅则像个粗野妒忌的恶人。“你!”柳氏立刻心疼得不行,几步冲过去扶起许明珠,
转头对着许琳琅,方才那点虚假的温和荡然无存,只剩下严厉的斥责,“许琳琅!
你好大的胆子!刚进家门就敢对明珠动手?果然是乡野之地养出来的粗鄙性子!
还不快给明珠道歉!”许文远看着许琳琅手背上那片刺目的红肿,
又看看哭得梨花带雨的许明珠,眉头锁得更紧,眼神里的失望和不耐几乎要溢出来:“琳琅,
你太不懂事了!明珠是**妹,好心待你,你怎能如此不知好歹?还不跪下认错!
”花厅里侍立的几个丫鬟仆妇也纷纷投来鄙夷和谴责的目光,窃窃私语声嗡嗡响起。“天哪,
刚回来就欺负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二**多善良啊!”“啧啧,看她那样子,
活该在乡下待着!”手背上的灼痛一阵阵袭来,许琳琅却感觉不到似的。她慢慢抬起头,
视线掠过一脸怒容的柳氏,掠过满眼失望的许文远,
最后定格在许明珠那张挂着泪珠、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得意和恶毒的脸上。
那层笼罩着许明珠的血色光晕,似乎因为她这拙劣的陷害成功而兴奋地波动了一下,
玉镯贪婪的吸力也仿佛更强了几分。许琳琅的嘴角,在无人看见的角度,
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而像冰封的湖面裂开一道缝隙,
透出底下刺骨的寒流。她缓缓抬起那只被烫伤的手,红肿狰狞,
与许明珠那吹弹可破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道歉?”她的声音很轻,带着雨水的湿冷气,
却清晰地穿透了那些嗡嗡的议论声,落在每个人耳中。她看着许明珠,眼神平静无波,
像在看一个死物。“好。”她上前一步。就在众人以为她要屈服认错时,
许琳琅那只被烫伤的手,却快如闪电般伸出,目标明确,
精准无比地——一把攥住了许明珠那只戴着玉镯的手腕!“啊——!”这一次,
许明珠的尖叫是真实的、充满惊恐的。她感觉手腕像是被一只烧红的铁钳狠狠夹住,
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冷刺骨的力量瞬间从对方的手指透入她的皮肤,直刺骨髓!
更让她魂飞魄散的是,她清晰地感觉到,
腕间那与她血脉相连、带给她无限好运和力量的玉镯,猛地一烫,随即剧烈地震颤起来!
仿佛遇到了天敌克星!“你干什么!放开明珠!”柳氏尖叫着扑上来。“孽障!反了你了!
”许文远也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许琳琅对周围的混乱充耳不闻。
她的手指死死扣着许明珠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对方的骨头。她眼底深处,
那两点金芒再次炽烈地燃烧起来,如同两点永不熄灭的炼狱之火。在那双能洞穿虚妄的眼中,
玉镯不再是翠绿的饰物,
它内部的结构纤毫毕现——无数细密如蛛网的血色符文在翠玉深处疯狂扭动、闪烁,
构成一个精密而邪恶的掠夺法阵。此刻,
这个法阵正因为她指尖透入的、带着破灭气息的力量而剧烈动荡,
那些血色符文如同被投入沸水的活虫,痛苦地挣扎、扭曲,发出无声的尖啸!“妹妹,
”许琳琅的唇凑近许明珠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耳畔,声音低得如同九幽寒风,
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温柔,“这镯子……戴久了,不累吗?”话音落下的瞬间,
她攥住玉镯的手指猛地发力!一股沛然莫御、带着绝对湮灭意志的无形力量,顺着她的指尖,
如同狂暴的雷霆,狠狠轰入那玉镯的核心!“咔嚓——!
”一声极其轻微、却清晰得如同在每个人灵魂深处响起的脆裂声,骤然响起!
那只水头十足、翠绿欲滴、被许明珠视若性命、也吸尽了许家气运的玉镯,
在许明珠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在许文远和柳氏难以置信的注视下,
毫无征兆地——从内部爆开无数道细密的裂纹!翠绿色的光泽瞬间黯淡下去,
如同生命被瞬间抽离。那些在许琳琅眼中疯狂扭动的血色符文,如同被烧尽的纸灰,
无声地溃散、湮灭。笼罩整个花厅的粘稠灰黑雾气猛地一滞,随即像是失去了核心引力,
开始混乱地逸散。玉镯内那股妖异的血色能量,如同被戳破的气球,
狂乱地倒灌回许明珠的身体!“噗——!”许明珠身体猛地一僵,双眼骤然凸出,
充满了血丝,脸上得意的表情瞬间凝固,随即被极致的痛苦和难以置信所取代。
她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大口粘稠的、颜色暗沉得发黑的血块猛地从她口中狂喷而出,
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挤压了内脏!鲜血溅落在她华贵精美的衣裙上,
也溅落在光洁的青砖地上,刺目惊心。“呃……”许明珠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眼白上翻,
身体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软软地瘫倒下去,重重砸在地上,溅起一片血花。
她浑身剧烈地抽搐着,脸色在瞬间褪尽所有血色,变得如同死人般灰败,
只有嘴角还在不断涌出暗红的血沫。死寂。绝对的死寂笼罩了整个花厅。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熏笼里的炭火噼啪一声轻响,成了这死寂中唯一突兀的声音。
柳氏伸出去想要推开许琳琅的手僵在半空,
脸上的怒容被一种巨大的、无法理解的惊骇所取代,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许文远拍案而起的身形也僵在原地,双目圆睁,死死盯着地上抽搐吐血、人事不省的许明珠,
又猛地转向站在那里、手背红肿、却面无表情、眼神冷得如同万载玄冰的许琳琅。
他脸上的愤怒和威严彻底碎裂,只剩下一种见了鬼似的、深入骨髓的恐惧。
那些方才还在鄙夷议论的丫鬟仆妇,此刻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个个脸色煞白,抖如筛糠,
看向许琳琅的眼神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如同在看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索命恶鬼!
花厅里弥漫开浓郁的血腥味和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威压。许琳琅缓缓松开手。
那只彻底碎裂、失去所有光泽、变成一块布满裂纹的灰绿色石头的玉镯碎片,
从许明珠软塌塌的手腕上滑落,“叮叮当当”地掉在血泊里。
她看也没看地上如同破布娃娃般的许明珠,
目光平静地扫过魂飞魄散的柳氏和面无人色的许文远,
仿佛刚才只是拂去了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手背上的灼痛感依然清晰,但她毫不在意。
“看来,”她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像冰锥一样刺入在场每个人的心脏,“这府里的茶,太烫。
我消受不起。”她不再理会身后的一片狼藉和死寂,转身,挺直了那曾被生活压弯的脊背,
一步一步,踩着冰冷的地砖,走向花厅外那依旧未停的、冰冷的雨幕。
湿透的粗布衣衫贴在身上,勾勒出她过分瘦削却异常挺拔的身影,
消失在廊檐下浓重的阴影里,留下身后一室的惊怖、混乱和浓得化不开的血腥。雨势渐歇,
只剩下屋檐滴水的嗒嗒声,敲打着尚书府死寂的夜。许琳琅被领进一个偏僻的小院,
名唤“听竹轩”。院子倒不算小,只是久无人居,透着股陈腐的霉味。
几竿瘦竹在夜风里瑟瑟作响,更添凄凉。领路的婆子放下一个半旧的灯笼,话都没留一句,
逃也似的走了,仿佛她是什么瘟神。屋里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一床、一桌、一椅,
连个妆台都没有。唯一的亮色是桌上放着的一个小包袱,里面是几件同样半旧的粗布衣裙。
许琳琅脱下湿透的外衣,借着昏暗的油灯光,看着自己手背上那片狰狞的红肿,
有些地方已经起了水泡。她走到角落一个积了灰尘的水盆边,舀起冰冷的井水,
慢慢淋在伤处。刺骨的寒意暂时压下了灼痛。她走到窗边,推开吱呀作响的窗棂。
冷风夹杂着残余的雨丝扑面而来。她望着远处主院方向依旧亮着的灯火,
还有隐约传来的慌乱人声,眼底一片漠然。许明珠?不过是个被邪气反噬的可怜虫罢了。
真正的毒瘤,是那只镯子背后的东西。她缓缓抬起左手,
下意识地抚摸着空荡荡的手腕内侧——那里,本该也有一只镯子的印记。
一丝极其微弱、几乎难以察觉的暖流,却悄然从她心口处传来,
带着一种古老而坚韧的守护意味。她微微闭了闭眼。夜更深,喧嚣终于渐渐平息。
许琳琅和衣躺在冰冷的硬板床上,手背的刺痛和身下的寒意让她难以入眠。
就在意识朦胧之际,一丝极其微弱、如同冰冷毒蛇吐信般的窥视感,
毫无征兆地爬上她的脊背!她猛地睁开眼,锐利的目光瞬间刺破黑暗,
精准地投向窗外庭院中那丛浓密的、在风中摇曳的修竹深处!一道身影,
如同融入夜色的幽灵,不知何时已悄然立在那里。身量极高,
穿着一身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的玄色锦袍,袍角用极细的银线绣着繁复的暗纹,
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下偶尔闪过一道冰冷的流光。他背对着她的窗口,身姿挺拔如孤峰寒松,
带着一种沉凝如山岳、却又隐含着无尽锋锐与寂灭的气息。夜风吹动他未束的几缕墨发,
拂过线条冷硬的下颌。他并未回头,似乎只是在院中驻足。但许琳琅眼底深处那两点金芒,
却在她看清那人的瞬间,不受控制地、前所未有地灼亮起来!仿佛受到了某种强烈的牵引!
在旁人眼中只是寻常的黑暗,在她此刻的视野里却被彻底剥离。她清晰地看到,
一股浓郁得化不开、如同实质般的灰黑色死气,正从那人身上源源不断地弥漫出来!
那死气并非寻常病弱之人的衰败,而是带着一种霸道的、仿佛能吞噬一切生机的诅咒之力,
如同无数条冰冷的锁链,死死缠绕着那人挺拔的身躯,
甚至隐隐勾勒出一条狰狞的、盘踞在他心脉之上的**虚影!那死气之浓烈,
几乎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灰黑的雾霭里,透不出一丝属于活人的生气。
这是……命不久矣、药石罔效的绝死之相!而且绝非寻常病症!更让许琳琅心神剧震的是,
就在这浓得令人绝望的死气核心——那人的眉心印堂之处,
竟有一点极其微弱、却顽强无比的金色光芒,如同风中之烛,在灰黑的死气狂潮中明灭不定,
死死守护着最后一点生机灵光,不让那诅咒彻底吞噬他的神魂!
金芒与灰黑死气在他体内疯狂地拉锯、撕扯、搏杀!每一次金芒的明灭,
都伴随着那人身体极其细微、却无法完全抑制的轻颤。就在这时,
那人似乎再也压不住体内翻腾的冲突,猛地抬手掩唇,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呛咳!
“咳…咳咳咳——!”压抑的、沉闷的咳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带着一种强行抑制却无法压制的痛苦。他宽阔的肩膀在剧烈的咳嗽中微微耸动。
借着廊下灯笼极其微弱的光线,许琳琅清晰地看到——几缕刺目的、粘稠的暗红色血丝,
正从那人掩着唇的指缝间,蜿蜒渗出!血腥味,混杂着庭院中湿冷的竹叶气息,
幽幽地飘了过来。是他!许琳琅的心跳,在那一瞬间似乎漏跳了一拍。那个名字,
那个代表着无上权柄、铁血手腕,也代表着无尽凶戾和死亡阴影的名字,
几乎要脱口而出——九皇叔,萧执寒!这个立于帝国权力巅峰,
却如同行走在深渊边缘、随时可能被自身诅咒吞噬的男人,为何会在这样一个冰冷的雨夜,
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她这个刚刚归家、声名狼藉的“真千金”的破败小院外?是巧合?
还是……她的目光再次落在他眉间那点顽强挣扎的金芒上,
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堪称疯狂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入她的脑海!机会!
一个绝无仅有的、能让她彻底摆脱这泥潭、甚至一步登天的机会!
一个与虎谋皮、在刀尖上起舞的机会!就在萧执寒咳声稍歇,似乎要转身离开的刹那,
许琳琅动了。她没有点灯,没有发出任何脚步声,如同暗夜中的一缕轻烟,
悄无声息地拉开了房门,身影一闪,便已站在了湿冷的廊檐下。
冰冷的石板透过薄薄的鞋底传来寒意,夜风吹起她单薄的衣衫,
勾勒出纤细却异常挺直的轮廓。萧执寒的脚步顿住了。他似乎早就察觉了她的存在,
缓缓地、带着一种无形的巨大压迫感,转过身来。廊下灯笼的光线太过昏暗,
只能勉强勾勒出他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高挺的鼻梁,紧抿的薄唇,如同刀削斧凿。
那双隐在阴影中的眼睛,如同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渊,
冰冷、锐利、带着审视万物的漠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他周身弥漫的那股浓烈的死气和血腥味,仿佛在他转身的瞬间凝成了实质的寒冰,
沉沉地向许琳琅压来,足以让任何心智不坚的人瞬间崩溃跪倒。许琳琅却站得笔直,
迎着他那足以冻结灵魂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手背的灼痛和院中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