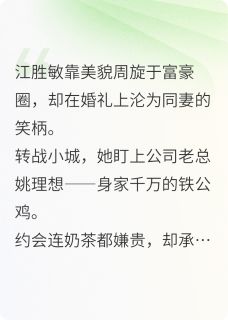江胜敏推开办公室门的一刹那,脊背就窜上一股难以名状的寒意。空气凝滞得如同胶水,
黏糊糊地糊在皮肤上。明明空调开得很足,冷风呼呼地吹着后颈,她却觉得闷热难当,
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巨大蒸笼里,四面八方都是看不见的、带着窥探温度的视线。啪!
巨大的声响在骤然寂静的空间里炸开,带着一股无处发泄的邪火。
那只花了她大半个月工资、用来撑场面的轻奢链条包,被她狠狠掼在光洁的办公桌上,
金属搭扣与桌面撞击,发出刺耳的哀鸣。邻桌的方兰被这动静惊得猛地抬起头。
她的目光撞上江胜敏的,那眼神里没有往日的刻意亲热,也没有丁点好奇或关切,
只有一种……一种极力压抑却终究没能藏住的古怪。方兰的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
视线仅仅在江胜敏脸上停留了一秒,或许更短,便像被烫到般飞快地垂了下去。然而,
就在那低头的一瞬间,
江胜敏眼角的余光分明捕捉到方兰单薄的肩膀在极其轻微地、一耸一耸地抖动。她在笑。
这个认知像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扎进江胜敏的神经末梢。她猛地站直身体,目光锐利如刀,
扫向四周。格子间像一片片沉默的墓碑,
那些平时或热情、或敷衍、或带着几分讨好跟她打招呼的同事们,此刻都深深地埋着头,
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动作快得有些刻意。有人捂着嘴,
肩膀可疑地抽动;有人盯着电脑屏幕,嘴角却不受控制地向上咧开;还有人端着水杯,
假装喝水,杯沿后露出的眼睛里却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他们在笑什么?
一股混杂着不安、羞恼和隐隐恐惧的情绪,在她心底疯狂滋长,
像无数冰冷的藤蔓缠绕住心脏,越收越紧。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胸腔里翻涌的躁郁,
指甲却深深掐进了掌心。就在这时,人事部那个永远板着脸、声音刻板得像机器人的小李,
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江胜敏,”小李的声音毫无波澜,平铺直叙,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死水,
“姚总让你现在去一趟人事经理办公室。”他甚至没像往常一样加个“请”字。
一股冰冷的麻痹感瞬间从脚底直冲头顶。开始发憷?不,
那感觉更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喉咙,让她几乎窒息。姚理想?他找她?
而且是去人事经理办公室?不是他的总经理室?无数个不祥的念头在脑中疯狂闪回,
最后定格在早上办公室里那些诡异憋笑的脸孔上。她强作镇定,挺直背脊,
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砖上,发出清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虚浮的回响,
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推开人事经理办公室厚重的木门,
一股更加压抑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人事经理姓王,
一个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女人,此刻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眼神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公式化的审视。“坐。”王经理抬了抬下巴,指向桌前的椅子。
江胜敏依言坐下,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根绷紧的弦。她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却悄悄攥紧了裙摆。王经理没说话,只是从桌上一摞文件里抽出一张纸,
两根手指捏着,面无表情地推到她面前。那动作随意得像在推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
江胜敏的目光落在那张A4纸上。只一眼,血液仿佛瞬间逆流,冲上头顶,
又在下一秒被彻底抽干!耳朵里“嗡”的一声巨响,如同千万只蜂群同时炸开,
眼前的世界剧烈摇晃、模糊、发黑,办公室奢华的吊顶灯扭曲成一片刺眼的光斑。
她猛地用手撑住桌沿,才勉强稳住身体,没让自己一头栽倒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白纸黑字,
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她的眼球:**保证书**本人姚理想,因一时糊涂,
未能坚守道德底线,
以极其主动、露骨、不道德之言语及肢体动作引诱、纠缠……后面那些更加不堪入目的字眼,
如同蠕动的蛆虫爬满了纸面,每一个字都在疯狂地扭曲、放大,
嘲笑着她所有的精心谋划和自以为是的魅力。姚理想用最恶毒、最下作的词汇,
将她描绘成一个不知廉耻、主动投怀送抱的“狐狸精”,
而他则成了被妖法迷惑、无辜受害的“正人君子”。落款处,
是姚理想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龙飞凤舞的签名,还有鲜红的指印。日期——赫然是昨天!
昨天!就在她还在为那条廉价项链“感动”落泪,以为金龟婿终于上钩,
豪门梦近在咫尺的时候,这个男人,这个吝啬又虚伪的男人,已经在妻子的威压下,
写下了这封将她钉上耻辱柱的“罪己诏”!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又猛地撕开,
剧烈的绞痛让她几乎无法呼吸。所有的算计,所有的伪装,所有豁出去的尊严,
在这一纸荒唐又可怖的“保证书”面前,被撕得粉碎,
暴露在人事经理那冰冷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下,暴露在全公司那些憋笑的同事面前,**裸,
鲜血淋漓。“这……”江胜敏的喉咙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声音嘶哑破碎,“这……是诬蔑!
王经理,这是诬蔑!”她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声音却因为巨大的屈辱和愤怒而剧烈颤抖,
听起来毫无说服力。王经理的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下撇了一下,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表情,
却比任何嘲讽都更刺人。“是不是诬蔑,姚总签字按了手印,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她的声音依旧平板,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宣判意味,“公司高层的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公司形象和管理层声誉。姚总今天不会来公司了,
他明确表示,在你离职手续办完之前,他不会出现在公司。”她顿了顿,目光像冰冷的探针,
在江胜敏惨白的脸上扫过:“公司念在你之前的工作表现尚可,就不追究其他了。
但你必须立刻、马上办理离职手续,收拾个人物品离开公司。这是对你,对公司,
最好的处理方式。多停留一分钟,对所有人都是负担。
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离职申请表》和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推到那份“保证书”旁边,
语气不容置喙,“签个字吧,江**。体面点。”“体面?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江胜敏心上。她猛地抬起头,眼圈泛红,
死死盯着王经理那张毫无波澜的脸,“他姚理想做出这种事,写这种东西贴出去,让我体面?
你们凭什么让我走?我要见姚总!我要他当面说清楚!”最后一句几乎是嘶喊出来,
带着孤注一掷的绝望。王经理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像是看着一只在玻璃瓶里徒劳冲撞的飞虫,混合着淡淡的厌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姚总不会见你的。”她斩钉截铁,“他昨天下午就被他太太叫回家了。这份保证书,
是姚太太昨天晚上亲自送到公司,让保安贴在大门口的。今天一早,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
”她微微倾身,声音压低,却字字如冰锥,“江**,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些话不用说得太透。姚总家什么情况,你不会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吧?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踢到了最硬的铁板。姚太太没亲自来找你,已经是给你留了最大的‘体面’了。”姚太太!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彻底劈碎了江胜敏最后一丝幻想和挣扎的力气。
原来那个从未露面、在她想象中或许是个黄脸婆或者蠢钝富家女的原配,才是真正执棋的手。
她甚至不屑于亲自来撕扯,只是轻飘飘地让丈夫写下这份屈辱的保证书,
再贴在公司大门上昭告天下。这比任何谩骂殴打都狠毒百倍,是精准无比的公开处刑,
彻底碾碎了她在这个地方、甚至在这个小城可能立足的根基。原来,
自己精心设计的每一步棋,自以为是的魅力与手段,在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眼中,
不过是一场拙劣又可笑的小丑表演。对方甚至懒得下场,只用丈夫的手,
就轻易将她钉死在了耻辱柱上。所有的力气瞬间被抽空。江胜敏的身体晃了晃,
支撑着桌沿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她死死咬着下唇,尝到了一丝腥甜的铁锈味。
《离职申请表》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那份刺眼的“保证书”上,
无声地宣告着她彻底的失败。她还能说什么?还能争什么?去找姚理想?
那个懦夫此刻恐怕正跪在妻子面前摇尾乞怜。去找姚太太理论?
那只会招致更彻底的羞辱和毁灭。办公室里的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
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清晰得如同倒计时。“……好。
”一个沙哑破碎的音节,艰难地从江胜敏喉咙里挤出来。她拿起笔,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
笔尖在纸张上划过,留下几道歪歪扭扭、力透纸背的划痕。她甚至没看清签的是什么,
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在需要签名的地方潦草地划下自己的名字,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
放下笔,她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噪音。她看也没看王经理一眼,
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只剩下仓皇和虚浮,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炭火上。推开人事经理办公室的门,
外面格子间那种刻意营造的忙碌假象似乎凝滞了一瞬。无数道目光,
带着毫不掩饰的探究、嘲讽、鄙夷、幸灾乐祸,如同实质的针,从四面八方射来,
密密麻麻地扎在她身上。那些憋了一早上的嗤笑声、议论声,此刻如同找到了宣泄的闸门,
虽然刻意压低了,却像毒蛇的嘶嘶声,清晰无比地钻进她的耳朵。“……活该,
真以为自己能当老板娘了?”“啧啧,
保证书里写得多难听啊……”“平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今天怎么蔫了?
”“姚总也真是……不过也怪她自己不要脸……”“快看,收拾东西滚蛋了!
”窃窃私语如同无数细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没有一个人上前,
没有一句哪怕虚伪的安慰。只有曾经被她颐指气使、支使得团团转的实习生小张,
在江胜敏路过他的格子间时,飞快地抬眼瞥了她一下,眼神复杂,有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