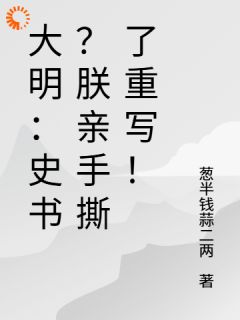朱由校笑了笑:
“去吧,难道还要朕下道旨?”
王朝辅一听,连忙应道:
“奴婢不敢,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朱由校坐下来,翻开了几本奏疏,都是辽东那边送来的。熊廷弼接连上书,不是要粮饷,就是说明辽东形势艰难,只能守城,请求朝廷理解。
他轻轻叹了口气,心里明白,自己远在京城,想帮他也无能为力。若不先把朝中局势理顺,拨下去的银子还没出城,怕是就被人贪掉一半。
眼下也只能以皇帝的名义给予支持,希望熊廷弼能撑住这三面压力,等到自己腾出手来的那一天。
小太监站在后边,见朱由校正低头沉思,忍不住抬头打了个哈欠。一抬头,却看见帘子后头露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他吓得大喊:
“有刺客!快护驾!”
另外三个小太监一听,立刻围到朱由校身前,把他挡得严严实实。
外头值守的锦衣卫隐约听到动静,又听到皇帝喊“锦衣卫”,立刻冲进殿,掀开帘子,将躲在后面的客八八和李进忠一把揪了出来。
客八八惊慌失措地喊道:
“陛下,是奴婢啊!”
朱由校听到声音,眯眼一瞧,认出果然是她,无奈地说:
“放开客奶妈。”
“奶妈大半夜来乾清宫做什么?这个又是谁?”
他打量着客八八身旁的小太监,这人面生得很,显然不是自己身边的人。
“陛下,他是奴婢的对食,求陛下饶他一命。”
客八八跪在地上,声音都在发抖。
对食?那就是魏忠贤了。朱由校走近两步,细细打量这位日后权倾朝野的大太监。这人与王振、刘瑾齐名,被后人称作“明朝三大宦官”。
正因为有皇帝的默许,他们才能翻云覆雨、一手遮天。朱由校正需要这样一个人替自己办事,也替自己挡事。
“你叫什么名字?”
他淡淡地问。
“回皇爷,奴婢叫李进忠,属御马监的。”
此时的魏忠贤还未改名,原姓魏,入宫后改姓李,名进忠。
“你可知道擅闯乾清宫是什么罪?”
朱由校盯着他问。
“奴婢知罪,求皇爷开恩!”
李进忠立刻跪地叩头,额头都快磕出血了。
客八八也跟着跪下求情:
“陛下,是奴婢带他来的,要罚就罚奴婢。”
朱由校假装沉吟片刻。他当然不想这么早就处置魏忠贤,这种人,是极好用的一把刀。
“既然奶妈开口了,朕也不能不给面子。死罪免了,活罪难逃。拖出去,杖责二十。”
说完,他朝王朝辅使了个眼色。王朝辅立刻会意……这顿打,别真把人打残了。
“奶妈起来吧,给朕按按肩膀。”
朱由校靠在龙椅上,心里盘算着,这把刀该怎么用才顺手。
……
“咻……”
箭矢破空而出,正中靶心。
“皇爷这箭法真是神了!”
王朝辅在一旁夸道。
只见朱由校左手执弓,目光坚定,嘴角挂着笑意。他登基之后,不光练马术,也苦练弓箭与剑术。站姿必须稳,出手必须准。十箭里至少要中八箭,臂力也得练上来。这些都是为将来马上骑射做准备。
他每天抽出两到三个时辰练箭,之后便回宫批阅奏章。夜深人静时,还会研读兵法,并翻阅从战国到万历年间所有赫赫有名的将领资料。最近,他正专注研究卫青与霍去病的骑兵战术。
要想亲自领兵打仗,至少得下两年苦功。当年武宗皇帝能在应州一战击败达延汗,正是因为他从小就把达延汗当作劲敌来研究。多年的准备没有白费,那一战直接让鞑靼部十年不敢南侵。
“今日就到此为止,回宫。”
朱由校说完,便朝乾清宫走去。
回到宫中,客氏早已备好一碗姜汤。练完箭后喝一碗,早已成了他的习惯。
“奶妈熬的汤,越发有滋味了。”
他笑着说道。
客氏听后很高兴,皇帝喜欢她熬的汤,自然是件好事。
“那个李进忠,现在如何了?”
朱由校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陛下,他已经没事了,多亏陛下手下留情。”
客氏自然明白,那一顿板子虽是二十下,但若下手重些,足以让人卧床半月。如今能正常行走,已是天大的恩典。
“宣他进宫见朕。”
“奶妈,给朕按按肩膀。”
练箭实在太累,手臂与肩膀酸痛难忍。他现在不过才拉开四十斤的弓,离理想状态还差得远。真正能在马上拉开六十斤弓、在地面拉开八十斤弓,才算达标。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五十步**穿建奴重甲兵的铠甲。那些精锐士兵通常穿着三层甲:最内层是皮甲,中间是锁子甲,外层则是铁甲,真正做到了全副武装。
后世有人总说大清靠骑射打天下,这话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建奴是渔猎民族,不是游牧民族,若真比骑射,怎能胜过蒙古人?那个时代的骑射之王,非蒙古莫属。
建奴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们的重甲骑兵。这些士兵都配有战马,平时由骡马驮运盔甲,作战时穿上重甲冲锋陷阵。虽然骑射不如蒙古人,但比起腐朽的明军,已是绰绰有余。
等到皇太极收服蒙古各部,孔有德带着火炮投诚,满清的军队才真正成为当时最强的部队。他们既有蒙古八旗的骑兵,又有汉军旗的火器部队,加上自身无敌的重甲兵,可谓一时无两。
在那个年代,除了火炮,其他火铳、火枪几乎无法穿透建奴重甲兵的护具,除非在二十步之内。弓箭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为何蒙古各部被建奴压制,纷纷归附的原因。
“李进忠,传闻你原是姓魏?”
朱由校一边享受着客氏的**,一边随意问道。
“回皇爷,奴婢的确原姓魏。”
李进忠低头恭敬回应。
“那你从今日起便恢复原姓,朕赐你新名,今后你便叫魏忠贤。”
李进忠听后大喜,连忙叩首谢恩:
“奴婢叩谢皇爷隆恩!”
朱由校微微一笑,又道:
“王伴伴,拟旨,魏忠贤即日起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
此言一出,魏忠贤愣住,连客氏也愣在原地。她万万没想到,自家这位居然因祸得福,一跃成了东厂提督。
王朝辅更是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是唯一能随时在皇爷身边伺候的人,怎料这么重要的职位竟然与他无关?
“怎么,没听明白?”
朱由校语气一沉。
魏忠贤立刻再次叩谢。
王朝辅虽不甘心,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写旨意。
“你拿着旨意立刻前往东厂,替朕查清楚那些与外臣勾结、忘了自己的主子是谁的人。”
“若人手不够,可去北镇抚司找许显纯,让他调人给你。”
“朕给你三天时间,大朝会之前务必处理妥当,听明白了吗?”
朱由校目光凌厉地盯着他。
“奴婢明白,定不辱使命。”
魏忠贤低声应道。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牢记,谁才是你的主子。朕最讨厌三心二意之人。”
这是朱由校对他的特别提醒。他怕魏忠贤骤然得势,忘了自己该站的位置。
只要魏忠贤听话,能替朕背锅、办事,便是好狗。
“去吧!”
朱由校目送他离开,继续思索着大局,如今只差最后一步。
……
乾清宫
许显纯前来复命。这几日他竭尽全力,已查出十几位大臣的罪证,第一时间将名单呈报给皇帝。
“这些都有确凿证据?”
朱由校翻完名单后沉声问道。
他虽早有准备,知道这些文官不会太干净,但看到具体罪行时,依旧令人震惊。
“回陛下,每一条皆属实,臣已掌握全部证据。”
许显纯疲惫不堪,手下缇骑也几乎累垮,他已经两天未曾合眼。
朱由校看在眼里。
“王伴伴,所有参与此事的锦衣卫每人赏银二十两,许显纯赐飞鱼服一套、绣春刀一柄。”
“你回去好好歇息,让手下也休整半天。那些文官今后要盯紧了,明早准时进宫。”
许显纯感激叩谢,慢慢退出殿外。
朱由校略一沉思,又道:
“杨寰,去请郑皇贵妃和李选侍来乾清宫。”
杨寰站在一旁大声说道:
“臣领命!”
话音刚落,一名小太监匆匆走入殿内,向皇帝禀报:
“陛下,张世泽率五百羽林军已抵达宫门外。”
朱由校听后立刻起身,快步向外走去。
……
值房内
一群文官正围坐一堂,讨论次日早朝该如何向皇帝施压。
在场的有:
内阁次辅刘一燝、内阁辅臣韩爌、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户部尚书汪应蛟、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杨涟、冯三元,刑科都给事中毛士龙、中书舍人汪文言等,大多为东林一系,共计三十余人。
杨涟率先开口:
“明日早朝,我先带头参劾方从哲,诸位同僚务必齐声响应,先把此人赶出京城,如此齐、楚、浙三党便无依附之人,随后再一齐请陛下说明出宫之事。”
汪文言随即点头附议:
“杨公所言极是,必须先除掉方从哲,否则三党仍会暗中支持皇上。”
张鹤鸣也插话道:
“待方从哲走后,我们再联手弹劾熊廷弼,将他调离辽东,让袁公接任经略使,届时朝政归于东林清流之手,辽东局势必有转机,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他早就不满熊廷弼无视兵部指令,这次若能扳倒方从哲,熊廷弼失势,正好可以一雪前耻。
魏大中笑着说道:
“张公真乃国之栋梁,若真能如此发展,诸位日后必定青史留名。”
众人听后纷纷称颂,场面一时热闹非凡。
这便是万历以后文官们的常态,事还未办,先自庆功,仿佛只要动了念头,便已成定局。
沉醉于自我幻想之中。
……
皇宫外
朱由校望着眼前的五百羽林军,神情满意。
经过这些日子的整训,军队已初现锋芒。
队列整齐,人人精神抖擞,面色红润,一看便知是经过严格操练之兵。
为了打造这支精锐,朱由校不惜重金投入,每人每月二两银子俸禄,每日三餐供应,午间必有肉食。
训练强度也不低,所有士兵必须精通刀枪棍棒,每天都要进行实战演练,三日一次混战,每人必须能拉开六十斤弓,这是羽林军最基本的门槛。
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负重训练,就是为了筛选出能如建奴般身披重甲作战的猛士。
在如今这个时代,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的重甲步兵,几乎可称无敌。
想打败敌人,首先得有一支比他们更强的重甲骑兵。
有人提出来用火器对抗,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