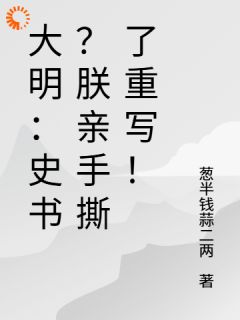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四十八年。
皇宫深处。
朱由校站在乾清宫外,神情恍惚。刚刚被册立为皇太孙的他,此刻正等待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皇长子朱常洛与内阁重臣早已进入宫中,大门紧闭,时间仿佛停滞。宫中那位执掌江山四十八载的万历皇帝,已至生命尽头。而朱由校,正在等待属于自己的篇章开启。
他来自另一个时空。现代的一名本科生,自少年起便痴迷历史,尤对明末风云颇有涉猎。他知道,大明王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乾清宫门缓缓开启,司礼监太监王安声音颤抖地高喊:“皇帝驾崩!”一声哀鸣,惊破寂静。宫内外宦官宫女纷纷跪地哭嚎,朱由校也缓缓跪下。他是大行皇帝的长孙,是刚刚被确立的皇太孙,帝国未来的掌舵者。
后人对万历皇帝多有苛责,仿佛他的统治全是昏聩与怠惰。甚至有人说,“大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但朱由校知道,历史并不像书上写的那样简单。万历皇帝的确多年不临朝,但那是因为他身患腿疾,两腿长短不一,年纪越大越严重,行走极为不便。他连正常生活都艰难,更别提日日上朝。晚年的他,几乎足不出宫门,乾清宫成了他的囚笼。
此时,乾清宫内已乱作一团。皇帝驾崩,举国震动。朱由校心中清楚,再过一个月,他便将迎来自己的时代。他要成为真正的主角,亲手改写那段屈辱的历史,阻止甲申之变再次上演。
宫内,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正与朱常洛商议国事。皇位更替,礼仪繁重。众人决定,新帝于八月初一登基。在此之前,需为先帝守灵。
八月初一。
朱常洛在奉天殿正式即位,年号泰昌。他登基后第一道诏令,便是废除矿税,召回各地镇守太监。同时拨出内库白银二百万两,用于犒赏边军,尤其是辽东将士。此外,他迅速填补朝野空缺官职,恢复政令运转。诏书一出,百官振奋,百姓称颂,皆称圣君临朝,大明中兴可期。
登基典礼结束,朱由校回到自己的寝宫,随手翻开太祖皇帝留下的《皇明祖训》,开始细细品读。这些天他几乎未曾踏出房门,自从为万历皇帝守孝之后,除了今日前往奉天殿参加登基大典外,其余时间他都待在床上研读这部祖训。他深知这个时代的文官习气,唯有依仗太祖留下的祖制,才能真正整顿官场。
亥时。
朱由校走到窗前,望向乾清宫方向,随口问身旁小太监:“今日宫中可有新鲜事?”
小太监恭敬答道:“回殿下,宫中今日并无大事,只是听闻郑皇贵妃精选了十名美貌女子送入乾清宫。”
朱由校闭目沉思。他的父皇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这些美人的日夜陪伴。他那位便宜老爹,在万历皇帝在世时还懂得收敛,一登基便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只当了二十八天皇帝,就一命呜呼。
这段时间,他正好安排自己登基后的布局。
“你们退下吧。”朱由校对身旁两名太监说道。
房门关上后,他从角落里取出一只自制木箱,打开后取出一本小册子。这本册子是他根据前世记忆整理出的“大明中兴可用之才”,上面第一个名字,是后世赫赫有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
在他看来,要整顿京城的混乱局面,必须先掌握一支忠于自己的力量,必须树立权威,不动雷霆手段,难以震慑天下。
熊廷弼便是他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辽东绝不能重蹈前世覆辙,任由努尔哈赤步步紧逼,必须全力支持此人。
朱由校紧紧握着那本册子,目光坚定。
八月十一日。
朱由校已得知,他的父皇泰昌皇帝病重不起。这些日子乾清宫格外热闹,简直称得上是大明近几十年来最“鼎盛”的几天。他那位便宜老爹沉迷女色,日日与郑贵妃送来的十名侍女玩乐至深夜,精力不济便靠药物支撑,如今身子已被掏空,回天乏术。
“殿下,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求见。”
王安快步进来禀报:“殿下,皇爷请您前往乾清宫。”
朱由校踏入乾清宫,见泰昌皇帝虚弱地躺在床上。
“儿臣拜见父皇圣躬安。”
朱由校跪地叩首。
“朕安。”
“皇儿平身。”
“谢父皇。”
朱由校起身,站于一旁。
“皇儿近日可有读书?”泰昌皇帝虚弱地问道。
“回父皇,儿臣近日研读《大学》与《尚书》。”
朱由校这些日子一直在翻阅《皇明祖训》,默默琢磨太祖皇帝当年治理天下的种种手段,但他从不对外透露分毫。
“这几日朕身子有些不适,御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恐怕命不久矣,这江山的重担,只能托付给你了。”朱常洛语气低沉。
“父皇请安心休养,不过是些小恙,过几日自然就会好转。”朱由校低头回应。
父子二人在乾清宫密谈了一个时辰有余。朱常洛心里清楚自己病从何来,但他早已无力改变,历史早已写下结局。
回到寝宫后,朱由校翻开一本小册子,盯着上面的人名发怔。他知道,时机快要到了,改变一切的机会就在眼前。
八月二十八日
这一日,注定载入史册。红丸案在此日发生,成为明末三大案之一。泰昌帝因对御医失望,转而听信内侍崔文升,误服其开出的药方,导致上吐下泻,一夜之间竟腹泻三十余次,原本虚弱的身子更是一落千丈。他病急乱投医,又听信李可灼献上的“仙丹”,起初服用一颗尚无大碍,两日后竟又迫不及待服下第二颗,结果命丧黄泉。
而此刻,朱由校正在屋中写纸条。一张递给英国公张维贤,另两张分别交给锦衣卫千户许显纯与田尔耕。
他将这些纸条藏于怀中,静候泰昌帝驾崩的消息。他之所以下这些手令,是为了阻止那“移宫案”的再度上演,他不能让历史重演。
九月初一
朱由校天未亮便起身,正端坐床沿沉思。他面前跪着三名太监,是他在宫中亲信之人。经过月余观察,他觉得这三人尚可一用,他们的前程,就看今日如何表现。
“殿下,王安来了。”
“这三张纸条,你们各持一张,等我一走,立刻出宫送去,务必亲手交到名单上之人手中,绝不容有失。”朱由校目光冷峻地叮嘱。
“是!”三人齐声应道。
“殿下,皇上病重,急召您前往乾清宫。”王安一见朱由校便急急禀报。
“我知道了,王伴伴,我们速去。”朱由校面色凝重,快步而出。
乾清宫内
“皇儿到了吗?”朱常洛卧于榻上,气息微弱地问。
他已感到大限将至,迫切想见儿子一面,尚有要事未交代清楚。
门外小太监低声禀报:“皇爷,殿下到了。”
“快让太子进来,你们都出去。”
乾清宫内,朱常洛对着一众太监下令。
朱由校刚踏入宫门,殿中便只剩下皇帝、太子与两名宫女。
还未跪下行礼,朱由校便听见朱常洛道:“免礼,过来些。”
“你父皇就要去见列祖列宗了,大明中兴的担子,从此落在你肩上。”
朱由校急道:“父皇安心静养,莫要讲这些话。”
朱常洛继续说道:“你还年轻,遇事不决时,要多听东林重臣的意见。”
朱由校眉头微蹙,未料到生死关头,父皇仍对那些文臣如此信任。
“儿臣明白。”
朱常洛刚欲再言,胸中一滞,一口气提不上来,便猝然倒下。
朱由校失声大喊:“父皇!”
门外的李选侍听闻死讯,怒气冲冲地闯入殿中。她看着已逝的朱常洛,心中一片焦躁……她还未被册封为皇贵妃,怎就撒手人寰了?
她转头看见朱由校,心头一转,知道自己今后的立足之地,全靠眼前这个十六岁的皇长子。
她冷冷下令:“没有我的允许,皇长子不得离开乾清宫半步。”
又对王安道:“陛下殡天的消息,不得外传。”
“娘娘放心。”王安点头应下,脸上浮起一丝冷笑。
朱由校依旧在哭,但他在等,等英国公和锦衣卫。
……
内阁。
三位阁臣皆面色凝重。
皇帝即位不过一月,竟突然病重,朝野未稳,辽东又战火连连。近日辽东奏报频频,努尔哈赤大肆攻城掠地,屠杀**,局势危急。
方从哲开口道:“二位,熊廷弼上疏,请求补发往年积欠粮饷,户部可酌情拨付。”
韩爌立即反驳:“上月陛下才拨银二百万两充作军饷,怎可能一月未过,又再要粮?元辅难道忘了?”
刘一燝附和:“熊廷弼自经略辽东以来,整日要饷要械,却从未与敌交锋,一味避战,空耗国力,可曾立下寸功?”
方从哲无言以对。虽知熊廷弼为人耿直,属楚党一脉,而他虽为齐浙楚三党之首,却在朝堂上难以压制东林党。
无奈之下,他只得道:“那就奏请陛下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