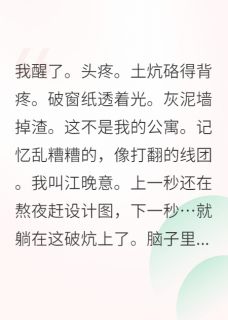冰凉的布条碰到伤口,沈砚舟的身体猛地绷紧,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
“忍…忍一下…”我手抖得更厉害了,尽量放轻动作。泉水擦过的地方,血似乎流得没那么凶了?是我的错觉吗?
我顾不上多想,用沾了泉水的布条紧紧压住伤口上方一点的位置,然后飞快地用剩余的布条一圈圈缠紧,打了个死结。
简陋的包扎完成。血暂时被压住了,但布条很快又渗出血色。
沈砚舟靠在草堆上,闭着眼,胸膛微微起伏。喝了泉水,又止了血,他的脸色似乎没那么吓人了。
“你…”他忽然睁开眼,看向我,眼神复杂,“为什么帮我?”
我被他看得有点慌,低下头:“总不能…看着你流血不管吧。”
“那些人说的黑市…”他声音低沉,带着审视,“你听到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果然!他记得我!也知道我听到了!
“我…我什么都没听到!”我立刻否认,声音有点发飘,“我就是…就是碰巧路过!”
他看着我,没说话。那眼神,像能穿透人心。
瓜棚里一片死寂。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半晌,他扯了扯嘴角,像是想笑,又因为疼痛扭曲了一下。“江家屯的…江晚意,是吧?”
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我惊愕地抬头看他。
“胆子不小。”他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鬼市卖粮的是你。今天…也是你。”
完了。他什么都知道了!
我手脚冰凉,感觉血液都凝固了。他会不会去举报我?或者以此要挟我?
“我…”我想辩解,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放心。”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恐惧,声音平淡,却奇异地带着一丝安抚,“我沈砚舟,不是恩将仇报的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因为紧张而攥紧的衣角,还有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
“你救我一次。我欠你一条命。”他语气郑重,“以后…在黑市,或者别的地方,遇到麻烦,可以报我的名字。”
报他的名字?沈砚舟?这名字在公社,似乎…不太好使吧?反而更像麻烦?
我心里嘀咕,面上却不敢表露,只能胡乱点点头。
“还有,”他看着我,眼神很深,“你那个‘凉白开’,味道不错。”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察觉到泉水的不寻常了?
“就…就是普通井水…”**巴巴地说。
他没再追问,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
“你走吧。”他重新闭上眼,靠着草堆,显得有些疲惫,“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对谁都别说。”
“那你的伤…”
“死不了。”他打断我,“我有地方去。你在这里待久了,对你没好处。”
我知道他说得对。瓜棚虽然偏僻,但保不齐有人路过。一个姑娘家和一个受伤的男人待在一起,传出去,我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那…你保重。”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他腿上渗血的布条,心里沉甸甸的。转身跑出了瓜棚。
跑出去很远,我才敢回头。荒废的瓜棚孤零零地立在晨光里,像一个沉默的秘密。
回到家,果然迟了。王翠花堵在门口,叉着腰,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死哪去了?!交个公粮人都能丢?是不是又去偷懒了?还是去会野男人了?啊?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
我低着头,任她骂。心里却在想着沈砚舟腿上的伤,还有他那句“欠你一条命”。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干活,挨骂,偷偷种粮,偶尔去趟鬼市,每次都提心吊胆。
只是,再去鬼市时,我下意识地,会留意那个角落。那个沈砚舟曾经出现过的角落。但他再也没出现过。
空间里的粮食越堆越多。钱票也攒下了一小卷。可怎么分家,还是个死结。江红梅像条毒蛇,盯我盯得更紧了。
转机出现在初冬。
一天傍晚,我从自留地拔萝卜回来,路过村口那棵大槐树。树下围着一群歇工回来的社员,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老沈家那个沈砚舟,出息了!”
“咋回事?”
“公社那个新办的机修厂,知道不?缺技术工!人家沈砚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本事,愣是通过了考核,当上正式工了!还是技术骨干!听说工资老高了!”
“真的假的?他不是…”
“嘘!成分是成分,人家有真本事!厂里领导都器重他!听说还给他分了间单身宿舍呢!”
“啧啧,真是人不可貌相…”
沈砚舟?机修厂正式工?技术骨干?
我愣住了。那个在鬼市神秘莫测,打架不要命,腿上被捅一刀还能硬撑的男人,摇身一变,成了吃公家饭的技术工人?
这身份转变,也太大了!
但不知为何,我心里隐隐松了口气。他有正经去处就好。那伤…应该没事了吧?
这个消息,像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在江家屯也泛起了涟漪。
几天后,我在地里干活,听到隔壁垄的婶子们闲聊。
“哎,老沈家这下可算熬出头了!砚舟那孩子有本事!”
“谁说不是呢!以前都说他野,不着调,看走眼喽!”
“就是…听说他跟他后娘那边彻底闹掰了?连他爹都不认了?”
“闹掰了才好!那后娘一家子,以前怎么磋磨他的?活该!他现在吃公粮,住宿舍,一个人自在!”
“不过啊,一个大老爷们,自己过也不像样。听说厂里领导都关心他个人问题呢…”
“个人问题?就他那成分…好姑娘谁敢嫁?再说他那脾气…”
婶子们压低声音,后面的话听不清了。
我默默听着,手里的锄头没停。沈砚舟…原来也有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难怪身上总带着股生人勿近的戾气。
只是,“个人问题”这个词,像根小刺,莫名扎了我一下。我摇摇头,把这荒谬的念头甩开。关我什么事。
入冬后,活儿少了些。大伯江建国被队里派去修水库,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
家里只剩下王翠花、江宝山、江红梅和我。
王翠花的气焰更嚣张了。江宝山整天游手好闲。江红梅则把盯我的任务执行得更彻底。
这天傍晚,我喂完猪,准备去河边洗把脸。刚走到屋后柴火垛附近,就听见江红梅压低的声音。
“妈!我跟你说的你还不信?那死丫头绝对有问题!”
是王翠花的声音:“能有什么问题?她还能飞上天?”
“真的!我观察她好久了!”江红梅语气急切,“你看她,以前瘦得跟麻杆似的,风一吹就倒。现在呢?脸上有肉了!干活也有力气了!这正常吗?”
“这…”王翠花迟疑了。
“还有!”江红梅声音更低,“我上次亲眼看见,她偷偷摸摸从柴火堆里拿东西!用布包着!神神秘秘的!肯定是藏了好吃的!说不定…就是偷了咱家的!”
“什么?!”王翠花声音拔高,“死丫头!敢偷东西?”
“妈!咱去翻翻!肯定有猫腻!”江红梅怂恿道,“趁我爸不在家,咱好好治治她!把她那点家当都翻出来!看她以后还敢不敢!”
脚步声朝着柴火垛这边来了!
我躲在屋角,心瞬间沉到谷底!她们要搜柴火垛!我藏在最里面的那点土豆红薯,还有上次卖粮剩下的几毛钱,全在那里!
怎么办?
冲出去阻止?她们更会认定我心虚!
跑?能跑哪去?
眼看着王翠花和江红梅已经走到柴火垛边,开始动手扒拉了!
情急之下,我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绝不能让她们发现!
几乎是本能地,我集中意念,死死盯着柴火垛深处那个藏着东西的角落!
收进去!收进空间!
念头刚起,我感觉脑子像被针扎了一下,猛地一抽!眼前发黑,差点晕倒。
与此同时,扒拉着柴火的王翠花突然“咦”了一声。
“红梅,你来看看!这…这地方刚才是不是有东西?怎么…怎么好像空了一块?”
江红梅凑过去:“没有啊妈?这不都是柴火吗?你是不是眼花了?”
“奇怪…刚才明明感觉这里有点鼓…”王翠花疑惑地扒拉了几下,除了枯枝烂叶,什么也没有。
**着冰冷的土墙,大口喘气,冷汗浸透了内衣。刚才那一下,几乎耗光了我所有力气。但…成功了?东西收进空间了?
“妈!你看!什么都没有!我就说你看花眼了!”江红梅抱怨,“那死丫头精着呢,肯定藏别的地方了!”
“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王翠花气哼哼地直起身,“走!回屋!等那死丫头回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听着她们骂骂咧咧地回屋,我才敢滑坐在地上,浑身脱力。
好险…差点就完了。
空间,不仅能种东西,还能当储物柜?而且…似乎能隔空收物?这个发现让我又惊又喜。但这能力,好像极其消耗精神。
危机暂时解除。但王翠花和江红梅已经彻底盯上我了。这个家,一天也不能多待。
分家!必须立刻分家!
可江建国不在家,王翠花不可能同意。等江建国回来?还要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谁知道王翠花母女会做出什么事?
我该怎么办?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起来干活。王翠花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江红梅则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中午做饭时,王翠花故意只做了她和江红梅、江宝山的份,没给我留。
“干活磨磨蹭蹭,还想吃饭?饿着吧!”她摔摔打打。
我没吭声,默默去后院拔了点野菜。躲进小屋,心念一动,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热乎乎的大红薯。泉水浇灌、黑土地种出来的红薯,又香又甜。
吃着红薯,心里那股憋屈和愤怒却越来越盛。不能再忍了。
下午,我借口去自留地摘菜,溜出了门。没去自留地,而是绕了个大圈,朝着公社的方向走去。
一个大胆的、近乎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成型。
我要去找沈砚舟!
他现在是机修厂的正式工,有身份。他欠我一条命。或许…他能帮我?
我不知道这想法有多荒谬,多冒险。但被逼到绝境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也会当成救命的浮木。
公社机修厂在镇子西头。几排红砖厂房,一个大烟囱冒着黑烟。门口有传达室。
我在厂门口不远处的大树后站了很久,看着穿着蓝色工装、进进出出的工人,心跳得像打鼓。
怎么找他?直接去门卫问?人家会搭理我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从厂里走出来。人群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沈砚舟!
他穿着崭新的蓝色工装,戴着帽子,身姿挺拔。脸上的伤早就好了,只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他正侧头和旁边一个工友说着什么,神情专注沉稳,跟鬼市那个狠戾的男人判若两人。
领导坐上一辆绿色吉普车走了。人群散去。
沈砚舟也转身,朝厂旁边的宿舍区走去。
机会!
我鼓起勇气,从树后跑出来,几步追上去,压低声音喊:“沈…沈同志!”
沈砚舟脚步一顿,转过身。看到是我,他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讶异,随即是警惕。他迅速扫了一眼周围。
“是你?”他眉头微皱,“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我…”我被他严肃的眼神看得有点慌,准备好的话都堵在喉咙里,“我…我有急事找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说话?”
沈砚舟盯着我看了几秒,大概看我确实一脸焦急,不像作假。他指了指宿舍区旁边一条僻静的小路。
“那边说。”
走到小路深处,没什么人了。沈砚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什么事?快说。”
他语气很淡,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和鬼市、瓜棚里那个他完全不同。
我深吸一口气,豁出去了。
“沈同志,我…我想分家!从大伯家分出去单过!但我大伯不在家,我大伯娘和堂姐…她们容不下我,要害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语速飞快,尽量把事情说清楚,包括江红梅的怀疑和王翠花的刻薄,还有昨天差点被搜出东西的惊险。当然,隐去了空间和粮食来源,只说怀疑我偷东西。
沈砚舟安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神深处,似乎掠过一丝波动。
“分家?”他听完,眉头拧得更紧,“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户口在你大伯名下,想单独分出去立户?难。”
我的心凉了半截。
“不过…”他话锋一转,“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我猛地抬头看他。
“关键在你大伯江建国身上。”沈砚舟分析得很冷静,“你大伯娘和堂姐再闹腾,这个家,真正做主的是你大伯。只要他同意分,队里那边,就好办。”
“可我大伯…他听我大伯娘的…”我沮丧地说。
“未必。”沈砚舟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带着点嘲讽的弧度,“男人,尤其是一家之主,最看重什么?脸面,利益,还有…怕麻烦。”
他看着我的眼睛:“你现在处境危险,你大伯娘和堂姐步步紧逼。如果你‘出事’,比如被你大伯娘逼得寻死觅活,或者闹出什么偷盗的丑闻,你大伯作为户主,脸上无光,在队里也抬不起头,甚至可能被连累。”
我眼睛一亮!对啊!江建国最爱面子!
“所以,你不能忍。要闹。”沈砚舟声音低沉,“闹得越大越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那个家活不下去了。让你大伯觉得,留下你,是个更大的麻烦。”
“怎么闹?”我急切地问。
“等江建国回来。”沈砚舟目光锐利,“在他回来的那天,当着他的面,跟你大伯娘她们彻底撕破脸。把她们怎么苛待你,怎么污蔑你,怎么逼得你活不下去,当着邻居、队干部的面,全抖出来!哭,要大声哭!闹,要豁出去闹!最好…闹到要死要活的地步。”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这也太激烈了!完全打败了我之前小心翼翼、忍气吞声的生存之道。
“怕了?”沈砚舟挑眉看我,那眼神,又带上了点鬼市里熟悉的锐气,“不敢?那就继续回去受着,等着她们哪天把你生吞活剥了。”
想到王翠花的刻薄嘴脸,江红梅阴毒的眼神,还有那种随时可能被发现秘密的窒息感…
一股狠劲儿冲上头顶!
“我敢!”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我听你的!”
沈砚舟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意外,眼中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赞许。
“光闹还不够。”他补充道,“你要让你大伯看到,分家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好处?”
“你分出去,不用再吃他家的粮,他省了一份口粮。你承诺分家后,该孝敬他的,不会少,逢年过节该有的礼数,你记得。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让他觉得你分出去后,能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再回头拖累他。”
“我能!”我立刻说,“我…我能干活!我什么都能干!”
“口说无凭。”沈砚舟看着我,“你需要一个‘靠山’。一个让他们忌惮,不敢轻易再找你麻烦的‘靠山’。”
靠山?我茫然地看着他。我一个孤女,哪来的靠山?
沈砚舟沉默了几秒,似乎在做一个决定。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分家那天,我会去。”
我愣住了。
“以你…”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以你对象的身份。”
轰!
我的脑子像被炸开了!对象?!他在说什么?!
“别误会。”沈砚舟似乎看出我的震惊,语气依旧平淡,“只是权宜之计。我出面,代表你有‘依靠’,不再是任人拿捏的孤女。你大伯那种人,欺软怕硬。我一个吃公家粮的工人站出来,他会掂量掂量。分家条件,也好谈。”
原来是这样…演戏。
我砰砰乱跳的心慢慢落回实处,但脸上却控制不住地发烫。对象…虽然是假的,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这…这对你名声…”我嗫嚅着。他刚在厂里站稳脚跟,传出这种“绯闻”,好吗?
“我的名声?”沈砚舟嗤笑一声,带着点自嘲,“本来就那样。不在乎多这一笔。”他看着我的眼睛,“关键是你。想清楚。一旦我出面,坐实了这个‘对象’的名头,以后…可能会有麻烦。你想分家,这是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做不做,你自己选。”
麻烦?无非是名声。在这个年代,一个姑娘家跟男人扯上关系,名声肯定受损。但比起被王翠花母女逼死,名声算什么?
“我做!”我斩钉截铁,“沈同志,谢谢你!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沈砚舟看着我决绝的样子,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等你大伯回来那天,提前想办法递个信给我。机修厂,找沈砚舟。”他交代完,看了看天色,“回去吧。路上小心。”
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宿舍楼门口,攥紧了拳头。胸腔里,第一次燃起名为“希望”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