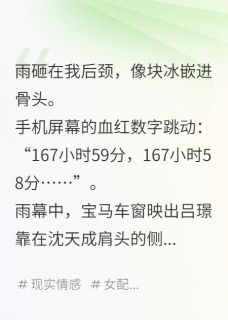雨砸在我后颈,像块冰嵌进骨头。手机屏幕的血红数字跳动:“167小时59分,
167小时58分……”。雨幕中,
宝马车窗映出吕璟靠在沈天成肩头的侧影——那曾是我的妻子,此刻正抱着香奈儿包,
笑靥如花。我蹲在市一医院的台阶上,跛脚的左腿在泥里蹭出个深色印子,破夹克裹着身子,
还是冷得发抖。七天够我撕碎这对狗男女的假面吗?1、雨水砸在手机屏幕上,
我忽然想起三年前的冬天——“小六科技”办公室的暖气开得很足,我却穿着三件毛衣,
还是冷。沈天成举着张皱巴巴的A4纸,红着眼眶闯进来,纸角戳着我的下巴:“小六,
你挪用了公司三百万!我把你当兄弟,璟璟还怀着你的孩子!”吕璟哭着扑过来,
指甲掐进我胳膊,眼泪砸在我手背上:“赵小六,你说过会陪我拍婚纱照的!沈哥给我看了,
你和那个女人在酒店的照片!”我盯着她的肚子——上周她还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会像我,
眼睛大大的。可现在,她的指甲掐得我胳膊生疼,嘴角的泪都冻成了冰。沈天成站在她后面,
手藏在西装裤口袋里。我瞥见他指节攥得发白,
口袋里露出来个棕色药瓶——是医院的堕胎药,我前天刚给吕璟买过保胎药,
瓶身的标签还是我贴的。“小六,你说话啊!”吕璟摇着我的胳膊,我却像被冻住了。
沈天成的眼睛里藏着阴狠,像上学时他偷拿我零花钱,被我抓住时的眼神。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两个警察举着证件:“赵小六,涉嫌挪用公款,跟我们走一趟。
”沈天成赶紧抱住吕璟,拍着她的背:“璟璟,别怕,我会照顾你的。
”吕璟的哭声越来越大,我被警察架着走出办公室,
回头看了一眼——沈天成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药瓶不见了。那天的风很大,
吹得我脖子发疼。我想起早上出门时,吕璟给我煮的豆浆,还热着,放在办公桌上。可现在,
什么都没了。2、我抹了把脸上的雨,刚要起身,就听见有人叫我——“赵哥!
”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点颤。我回头,看见个穿黑框眼镜的姑娘,缩着肩膀站在雨里,
手里攥着个粉色的包,像株被风吹歪的狗尾草。“林夏?”我认出她,
是研发部当年那个沉默的实习生,总坐在角落改代码。我记得当年我还帮她改过几次代码,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只是当年我眼里只有吕璟,忽视了她。她赶紧跑过来,
雨水打湿了她的刘海,眼镜片上蒙了层雾。她从包里掏出个银色优盘,还有张银行卡,
塞进我手里:“赵哥,这是沈天成伪造的签字原件,
融资方的贿赂录音……还有璟璟流产的真相。”我攥着优盘,指尖碰到她的手,
冰得像块石头。她的手在抖,指甲盖都泛着白:“我查了三年,
沈天成当年给璟璟吃的不是保胎药,是堕胎药。他骗璟璟说你出轨,
还把药说成是补身体的……”“为什么帮我?”我打断她,声音哑得像砂纸。她低头,
从口袋里摸出张皱巴巴的收据,边角都磨破了,上面写着“住院费:5800元”,
签名是我。“三年前,我妈住院,没钱交医药费,是你从抽屉里摸出银行卡,
说‘先用我的’。她抬起头,眼睛里带着点泪,“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沈天成他……他脏了你的公司,害了你和璟璟。”我盯着那张收据,
忽然想起三年前的下午——林夏红着眼眶站在我办公室门口,手里攥着缴费单,
说“我妈明天要停药了”。我没多想,从抽屉里拿出银行卡,塞给她:“先去交,
不够再找我。”没想到她记了这么久。“这张卡是我这些年存的,有十万块,够你用。
”林夏把银行卡往我手里塞了塞,“优盘里的证据我备份了三份,就算沈天成毁了这个,
还有备份。”我捏着优盘,感受着塑料壳的温度。雨还在下,但我忽然觉得胸口有团火,
烧得我喉咙发疼。“谢了。”我把优盘放进夹克口袋,看着她,“你不怕沈天成找你麻烦?
”她抹了把脸上的雨,笑了笑:“我妈去年走了,我没什么好怕的。再说……”她顿了顿,
声音轻了点,“你当年帮过我,我……很喜欢你,该帮你。”风卷着雨刮过来,
她缩了缩脖子。我把身上的破夹克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别感冒了。”她愣了愣,
刚要说话,我已经转身往巷口走。口袋里的优盘硌着我的腰,像块烧红的炭。我知道,
接下来的7天,会比这三年更难。但我不怕——因为我终于有了一把刀,
能捅进沈天成的心脏。而吕璟……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诊断书,嘴角扯出个冷笑。
等我做完该做的事,再告诉她真相。雨还在下,但我脚步比刚才稳了。
3、我抱着电脑坐在出租屋的破沙发上,
屏幕里循环播放着沈天成的录音——融资方王总的声音像根针:“老沈,
那三百万我打你私人账户了,够你和璟璟过好日子了。”忽然喉咙里像塞了把碎玻璃,
我弯着腰咳嗽,手捂在嘴上,指缝里渗出血丝。茶几上的诊断书被风刮得翻了页,
血珠砸在“剩余寿命7天”的字样上,晕开个暗红的印子。我抬头看墙上的旧挂钟,
指针指向十点半,下面贴的便签纸歪歪扭扭写着:“距离死亡:150小时30分”。
数字像块烧红的铁,烫得我眼睛发疼。伸手摸茶几上的药瓶,是林夏早上塞给我的,
瓶身还带着她的体温。我拧开瓶盖,倒出两粒白色药片,
就着冷水咽下去——喉咙里的疼慢慢退了,像有人把碎玻璃拔了出来。
耳边忽然想起林夏的话,是昨天在医院门口,她帮我拍掉肩膀上的雨:“赵哥,疼了就吃,
别硬撑。”她的手指碰到我的肩膀,像片温柔的叶子。我把诊断书翻过来,
背面写着林夏的手机号,字迹工整,是她的风格。
昨天她塞给我时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电脑里的录音还在播,
沈天成的声音越来越刺耳:“小六那家伙,根本不懂什么叫生意,早晚得栽在女人手里。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紧palm,疼得清醒。低头看诊断书,血印子已经干了,
变成深褐色。还有150个小时,够我把沈天成的面具撕下来,
够我告诉吕璟真相——够我在死之前,把属于我的一切,都夺回来。窗外的雨还在下,
打在出租屋的铁皮屋顶上,像有人在敲鼓。我盯着电脑屏幕,手指放在鼠标上,
把录音倒回开头,再听一遍。这次,我没再咳嗽。4、吕璟站在试衣间镜子前,
白纱裹着身子,化妆师举着粉饼说“璟姐笑个,这婚纱显气质”,她扯了扯嘴角,
笑容像张被揉皱的纸。手指不自觉摸向脖子——那串银小鱼项链还挂着,
是赵小六当年用**攒的钱买的,他说“璟璟,你像鱼,我养你一辈子”。门被推开,
沈天成进来,手里攥着个棕色药瓶,塞进她手里:“璟璟,国外带的补身体的,每天一粒,
别忘。”吕璟盯着药瓶标签,字迹有点眼熟——和三年前沈天成给她的“保胎药”一模一样。
她忽然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沈天成把同样的药放在她手里,说“璟璟,这是保胎的,
得好好吃”,可后来她流产了,医生说“胎儿发育不良”。“怎么了?
”沈天成伸手要摸她的脸,吕璟躲开,手指攥紧药瓶:“没、没什么,就是觉得药有点眼熟。
”沈天成的眼神闪了一下,很快笑出声:“傻丫头,新换的包装,和以前不一样。
”他把药瓶往她手里按了按,“赶紧试,宾客都等着看新娘呢。
”吕璟看着他走出试衣间的背影,手指摩挲着项链上的小鱼。化妆师过来调整头纱,她抬头,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有点红——想起赵小六当年蹲在路边摊前,给她挑烤串的样子,
他说“璟璟,等我赚了钱,给你买最大的钻戒”。“璟姐,好了吗?”化妆师提醒她。
她吸了吸鼻子,把药瓶放进婚纱口袋,扯出个比刚才真点的笑容:“好了,出去吧。
”镜子里的白纱很亮,可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像赵小六当年给她系鞋带时,
5、我蹲在沈天成公司楼下的墙角,怀里揣着林夏给的监听器,耳机里传来电流杂音,
像蚊子在耳边叫。公司大楼的灯只剩几盏,风卷着落叶打在腿上,
冷得刺骨——林夏说这监听器能收三公里内的信号,我从晚上十点等到十二点,腿都麻了。
忽然,杂音停了。耳机里传来沈天成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王总,那笔钱藏在郊区仓库,
门牌号是18号,等订婚宴后我亲自去转移。”“老沈,你可得藏好,
别让小六那家伙发现——”融资方王总的声音刚响,就被沈天成打断:“放心,
他现在就是条丧家犬,翻不起浪。”我攥紧监听器,指节发白。郊区仓库18号,
我记在手心——那是三年前我们一起租的仓库,用来放研发器材,沈天成居然把钱藏在那。
摸出手机,屏幕亮度调到最低,给林夏发消息:“明天中午,郊区仓库18号见。
”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我听见大楼里传来脚步声——沈天成的秘书从电梯里出来,
往停车场走。我赶紧缩了缩脖子,把监听器塞进怀里。秘书走过墙角时,
我听见她打电话:“沈总,明天的订婚宴流程已经核对过了……”声音越来越远,
直到消失在夜色里。我抬头看了眼沈天成的办公室,窗户还亮着灯。他不知道,明天中午,
我会把他藏在仓库里的钱、还有他的秘密,都挖出来——就像他当年挖我的心一样。
风又吹过来,我裹了裹身上的夹克,转身往巷口走。手机里传来林夏的回复:“好,
我带工具。”我笑了笑,手指摸着怀里的监听器。复仇的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
6、我和林夏刚迈出仓库18号的门,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
指甲掐进我皮肤里——疼得我一哆嗦。“有人跟着。”她声音发颤,眼睛盯着我身后。
我回头,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站在仓库门口的路灯下,帽檐压得低,手里攥着棍子。
其中一个我认识,是沈天成的司机,去年跟着他去谈过融资,眼神像条饿狗。“跑!
”林夏拉着我的手,往旁边的巷子里钻。我的跛脚刚迈出一步,
就传来钻心的疼——三年前被狱霸打折的骨头,至今还没长好。但我不敢停,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棍子戳在墙上的声音像敲在我心上。“往这边!
”林夏拽着我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路边堆着几个垃圾桶。我咬着牙,抬起左腿,
狠狠地踹向最上面的那个垃圾桶——塑料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垃圾撒了一地,
挡住了巷子口。“啊——”身后传来一声惨叫。我回头,看见林夏举着个小瓶子,
正对着带头的黑衣人喷。辣椒水的味道飘过来,那男人捂着眼睛,蹲在地上直打滚。“快跑!
”林夏拉着我继续往前跑,直到转过三个弯,看见巷口的路灯,才停下来喘气。我扶着墙,
咳嗽得厉害,手捂在嘴上,指缝里渗出血丝——刚才跑太急,喉咙里的血又出来了。
林夏赶紧从包里掏出纸巾,递过来:“赵哥,你没事吧?”我摇头,接过纸巾擦了擦嘴。
她的手还在抖,手里攥着那个辣椒水瓶子,瓶身印着“防狼喷雾”的字样。
我想起昨天她给我药的时候,说“我带了点工具,以防万一”——原来她早有准备。
“他们是沈天成的人。”林夏喘着气,“刚才在仓库里,我看见有人拍我们的照片,
应该是给沈天成报信了。”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镜片上蒙了层雾,
却透着股狠劲——不像三年前那个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实习生了。“没事。
”我把纸巾攥成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反正我们已经拿到了仓库的地址,
还有他藏钱的证据。”林夏点头,把辣椒水放进包里:“明天我去查仓库的监控,
看看里面有没有更多证据。”我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只露出一点光。
身后的巷子里,还能听见那两个黑衣人的骂声。我摸了摸怀里的监听器,
想起沈天成的声音——“他现在就是条丧家犬,翻不起浪。”“走。”我拽住林夏的胳膊,
往巷口走,“去吃点东西,明天还有得忙。”她嗯了一声,跟在我后面。
风卷着辣椒水的味道吹过来,我忽然觉得,这味道比任何药都管用——因为它让我清醒,
让我知道,我不是丧家犬,我是条要咬人的狼。而沈天成,很快就会尝到被狼咬的滋味。
7、我们靠在巷子墙根喘气,林夏的眼镜片沾着辣椒水痕,她抹了把脸,
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赵哥,你看这个。”她声音轻得像落在纸上的笔,
手指抖着抽出张照片——边角磨得发白,上面是我扶着个老太太,林夏跟在旁边,
眼睛红得像兔子。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2022年3月15日,妈妈住院,
赵哥帮我扶她去医院。”我盯着照片,鼻尖忽然发酸。
那天的事像潮水涌过来——林夏冲进我办公室,眼泪砸在我桌上,说“我妈晕倒在楼梯口,
我扶不动”。我抓起外套就跑,老太太体重不轻,我扶着她走了半条街,衬衫后背全汗透了,
她跟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说“谢谢赵哥”。“我妈那时候肺气肿犯得厉害,
医生说再晚十分钟就没救了。”林夏手指摩挲着照片上的老太太,声音哽咽,
“她走之前还抓着我的手说,‘夏夏,要记得那个赵哥,他是个好人’。”我看着她,
她的耳尖红得快滴血,眼镜后面的眼睛湿漉漉的。忽然想起当年,她总坐在研发部角落,
我路过时,她会赶紧低头改代码,耳朵红得像番茄。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吕璟的婚纱、公司的融资,从来没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里,除了感激,
还有点藏得很深的……在意。“林夏,”我轻声说,“当年就是举手之劳,不用记这么久。
”“不是举手之劳。”她抬头,眼睛里带着股子固执,“对我来说,那是救命的恩。
沈天成毁了你的公司,骗了璟姐,我一定要帮你把真相扒出来——就算……就算被他报复。
”风卷着碎纸吹过来,我把身上的外套往她身上裹了裹。她愣了愣,赶紧退回来:“赵哥,
我不冷。”“穿上。”我语气有点硬,像当年她加班时,我把自己的外套扔给她,
“别感冒了,明天还要去查仓库监控。”她低头笑了笑,把外套裹紧,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喉咙里的疼轻了点——这三年,我以为自己是条被抛弃的狗,可其实,
有个姑娘,一直蹲在我身边,陪着我,记着我的好。巷口的路灯亮了,照在她脸上,
眼镜片反射出光,像星星。我摸了摸怀里的监听器,想起沈天成说的“丧家犬”,忽然觉得,
我不是。因为我有同伴了。而同伴,比什么都重要。8、吕璟推开书房门时,
沈天成正在楼下打电话。
她本来是找他明天要戴的领带——订婚宴的流程表上写着“新郎穿藏青西装,配酒红领带”,
可翻遍衣柜都没找到。书房的台灯亮着,最下面的抽屉半掩着,露出个铁盒的边角。
她走过去,拉开抽屉,铁盒上落着层灰,打开一看,
里面塞着张皱巴巴的说明书——“堕胎药使用指南”几个黑字像针,扎得她眼睛疼。
她的手开始抖,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沈天成把同样包装的药放在她手里,说“璟璟,
这是保胎的,得按时吃”。可后来她流产了,医生说“胎儿发育不良”,
她哭着给赵小六打电话,却只听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铁盒里还有张照片,
沈天成和王总勾肩搭背,站在“小六科技”的招牌下,
背面用钢笔写着:“2022年11月,三百万到账。”王总她认识,
是当年给公司融资的人,沈天成说他“被赵小六骗了钱”,可现在看来,
分明是他们一起骗了赵小六。“啪”的一声,照片掉在地上。吕璟蹲下来,
手指划过背面的字,指甲掐进掌心——三年前沈天成说赵小六“挪用公款”“出轨”,
原来都是假的!他给她吃堕胎药,杀了她和赵小六的孩子,还把赵小六送进监狱,
占了他的公司,占了他的女人。她摸了摸脖子上的银小鱼项链,
那是赵小六当年用**攒了三个月的钱买的,他说“璟璟,你像鱼,我养你一辈子”。
可她却信了沈天成的话,把他的微信拉黑,把他的照片烧了,甚至在他出狱那天,
躲在沈天成的怀里,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窗外的月亮躲在云里,
吕璟抓起照片和说明书,往门口跑。手机里的时间显示十一点半,
离订婚宴还有十二个小时——她要找到赵小六,告诉他真相,就算他恨她,就算他不想见她,
她也要说。她跑到楼下,沈天成刚好挂电话,看见她手里的东西,脸色一下子变了:“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