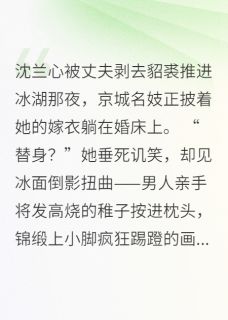沈兰心被丈夫剥去貂裘推进冰湖那夜,京城名妓正披着她的嫁衣躺在婚床上。“替身?
”她垂死讥笑,却见冰面倒影扭曲——男人亲手将发高烧的稚子按进枕头,
锦缎上小脚疯狂踢蹬的画面烫穿魂魄。再睁眼,她指尖抠着冰缝爬回人间:“戏唱完了,
该我登场了。”1骨节分明的手攥着白貂裘的领口,力道狠得像要勒断她颈骨。“脱。
”陈绍桓的声音比腊月寒风更砭人。他身后,西府海棠雕花窗棂漏出暖黄的光,
隐约有苏绣屏风上金线鸳鸯的浮光,更衬得回廊下像个冰窟窿。
红梅积雪被风卷着扑在沈兰心脸上,针尖似的疼。她单薄的月白绫子夹袄裹在发抖的身子上,
冻得发青的指尖死死抠着最后一点貂绒,喉头涌上铁锈味:“绍桓,
这是……母亲赏的……”“你也配?”男人唇角挑出一抹讥诮的弧度,
眼底映着正厅里通明的灯火和隐约的戏腔,毫无温度。他猛地用力,
“哧啦”一声锦帛裂响!白貂裘被粗暴地拽下,甩在铺了薄雪的青砖地上,
泥污瞬间玷污了那刺目的雪白。沈兰心一个踉跄,手肘重重磕在冰冷的石阶上,钻心地疼。
“这裘衣,只有晚晴那样的可人儿才配。”陈绍桓轻描淡写地弹了弹袖口并不存在的灰尘,
像拂去什么脏东西,目光掠过她惨白的脸,“至于你?挡道的石头罢了。
”冰冷的手钳住她纤细腕骨,粗暴地拖拽。寒彻骨髓的风猛地灌入口鼻!“噗通——!
”死水般的黑被硬生生砸破!裂痛从四肢百骸炸开,厚重的棉夹袄吸饱了冰水,
瞬间变成千斤巨石,拖着沈兰心往下坠。她像被浸入一锅腥臭污秽的浓墨。
零星的碎冰块锋利如刀,刮过脸颊脖颈。刺骨的冷,顺着每一个毛孔往骨头缝里钻,
肺里的空气被急剧压缩,**辣地疼。“救……”破碎的气音被腥冷的水堵回喉咙,
绝望的水草般绞缠上来。挣扎着仰起头。透过破碎冰面与浑浊水流,
回廊下的景象被切割得扭曲变形——陈绍桓挺拔的身影冷漠地转身,
那扇隔开两个世界的雕花门开了又合。暖光一闪而逝的刹那,
屏风后转出一角极其刺目的、华丽到诡异的大红。金线刺绣的繁复鸾凤,
在灯火通明处流光溢彩。那本该是她的嫁衣!三年前,她从沈家抬入陈府时,
百十个苏绣娘子熬了整年才缝出的心血,却被一个“请来唱堂会”的戏子披着!
冰水灌入鼻腔口腔,窒息感疯狂涌上。意识抽离的瞬间,
凄厉的念头穿透混沌:晚晴……那个名动京华的尤物……原来不过是个披了她旧嫁衣的戏子?
那她这正头夫人又算什么?眼角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滚落,混进冰水里,分不清是水还是泪。
黑沉的冰水像无数只鬼手,死死将她往更深处拖拽。最后的模糊视线里,
头顶那片禁锢她的、布满蛛网般裂纹的灰白冰面,倒映出下方沉沦的自己,
还有……画面猛地扭曲!撕裂!滚烫的温度瞬间灼穿意识!
冰窟的寒与那股熔岩般的滚烫撕扯着她的魂魄!不再是陈府幽冷的后园冰湖。锦缎!
上好的、流光溢彩的松江三棱缎!素白的料子,本该是喜气吉祥的,
此刻却铺陈在紫檀木云纹拔步床上,像一片刺目的雪域。一只绵软无力的小手,
五指挣扎着张开,徒劳地去抓那冰冷的缎面。指尖圆润,还带着点婴儿的肉乎。小手之上!
一只骨节异常分明、属于成年男人的大手!手背上绷起的青筋蜿蜒如毒蛇,
蕴含着冷酷的、压倒性的力量!
死死地、不容抗拒地、摁着一个被裹在同样素白锦缎里的小小身体!那身体在剧烈挣扎!
薄薄的、柔软的身板在男人山峦般的压制下,无助地扭曲着。
身上小小的寝衣也绣着缠枝莲纹。两只穿着虎头软鞋的小脚,像被抛上岸垂死的鱼尾,
疯狂地、急促地、无声地踢蹬着身下昂贵的锦缎!小小的虎头鞋面上那双憨态可掬的眼睛,
在此刻只有惊惶欲裂的死寂!“唔……唔……”闷在枕头里挣扎的声音,
被一层层柔软丝絮堵死,变成绝望破败的呜咽。枕头!
是那只绣着麒麟送子图案的彩缎枕头!男人的巨掌连带着这厚厚的屏障,像铁盖般捂下去!
枕头边缘的缝隙里,爆出一双眼睛!属于一个稚龄男童的眼睛!
瞳孔因为极致的恐惧和高热而烧得通红滚烫,眼白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血丝!
此刻它们死死地、绝望地向上翻起,直勾勾地瞪着——压在枕头之上那张俯视的脸!
冰冷的、轮廓深刻的一张脸。眼神里没有疯狂,没有暴戾,
只有一片令人血液冻结的死水微澜,像是在……碾死一只扰人清梦的虫子。
那张脸……陈绍桓!“……晟儿……娘在这里啊晟儿——!
”沈兰心破碎的魂灵发出无声的惨嚎!那撕心裂肺的痛楚比冰湖的窒息更猛千万倍!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她痴缠了一生换来剜心刺骨的结局!她的晟儿!她三岁夭折的儿子!
那不是风寒!是被生父亲手捂死的!冰窟黑暗深处的沈兰心,猛地睁开了一双眼睛!
那眼神不再是哀戚的绝望,不再是凄惶的柔弱。瞳孔深处,有东西死去了,有东西在焚烧,
最后凝固成极地万年不化的寒冰!
眼底映着那片扭曲冰面上最后的倒影:大红嫁衣刺目的流光,儿子疯狂踢蹬的小脚。
“咯吱……”几乎被冻僵的指尖,不知从哪爆出惊人的力量,
狠狠抠进冰面那蛛网般裂开的最薄弱缝隙!戏?好戏才开场!
2暗红色的、粘稠的药汁沿着白瓷碗壁往下流,蜿蜒如同干涸的血泪,
倒映着金丝楠木拔步床边守着的两张焦灼的脸。
周大夫两根枯瘦的手指搭在沈兰心冰凉的手腕上,眉头拧成个死结,额角一层薄汗。
旁边垂手侍立的赵管家,脸上惯有的精明稳重不见了,眼袋浮肿发青,
细小的汗珠顺着松弛的脸颊往下淌。他手里死死攥着一方上好的云锦汗巾,指节捏得发白,
却忘了擦。塌上的人一丝生气也无,只心口还微微有那么一点温热,像风雨飘摇里的残烛,
随时会熄灭。“周老……您可得……”赵管家喉咙干得像烧过的炭,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周大夫重重地、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口气沉甸甸地压在死寂的卧房里。“寒气透骨,
脏腑皆损……药石罔顾啊!赵管事,老朽已是……尽人事,听天命。”他摇了摇头,
开始慢吞吞地收拾药箱,
那响动像是给这位守了陈家几十年的老管家心里钉上最后一枚棺材钉。赵管家眼前一阵发黑,
腿肚子微微打颤。
要是死在府里……那位今日“大喜”的爷回来……光是想一想陈绍桓得知此事后可能的反应,
一股寒气就从脚底板直冲上天灵盖!比回廊外的冰风更刺骨!“砰”一声闷响!
内室那扇沉重的紫檀雕花隔扇门被一股大力猛地震开!撞在两边铺满缠枝莲纹锦褥的矮榻上,
发出一声痛楚的**!一股浓烈得化不开的血腥气混着凛冽刺骨的寒霜气浪,
瞬间冲散了室内苦涩的药味!赵管家和周大夫骇然回头!门口逆着廊下惨淡灯笼的光影,
站着一个瘦伶伶的影子。头发湿透,一缕缕纠结着贴在惨白泛青的脸颊和脖颈上,
往下淌着浑浊的冰水,在脚下昂贵的手织波斯地毯上晕开一小滩肮脏深色。
身上月白色的绫子夹袄吸饱了冰水,紧紧裹在身上,冻成了半硬的壳子,不断往下滴着水。
一只**的脚冻得青紫肿胀,踩在冰冷的砖地上。
另一只脚上还趿着半只同样湿透了的软底绣鞋,沾满了污泥枯叶。是沈兰心!
可她哪里还是平日那个温顺低微、无声无息犹如一张陈旧屏风的沈兰心?!
那双微微抬起的眼!寒冰淬过,火油浸透,深潭里浸了十年又烧了十年!
眼白上蛛网般的血丝红得刺目,中间嵌着的两点瞳仁,却黑得没有一点光,
像两口不见底的枯井!直直地、毫无波澜地撞上周大夫和赵管家惊骇欲绝的视线!她的唇角,
甚至还极其缓慢、极其僵硬地向上扯了一下!那弧度没有半点暖意,只有刻骨的冷,
像是棺中女尸被生硬地吊起的嘴角,阴气森森。“咳咳……”一声短促浑浊的呛咳,
从她青紫色的嘴唇溢出,带出一小股混着污血的水沫子。
她的身体开始无法抑制地、筛糠般剧烈抖动,皮肤下僵冷的血像是刚刚开始解冻回流,
激起一阵濒死般的痉挛剧痛。赵管家魂飞魄散!喉头咯咯作响,一个音节也发不出!
是人是鬼?!周大夫老脸煞白,踉跄着后退半步,手里的药箱差点脱手砸在脚上!
他看着沈兰心那张死气弥漫的脸,那分明是……回光返照的凶兆!命数已尽,
凶戾之气倒灌入体,才撑起这一口气!这样的病人……是阎王爷都不收的厉鬼!
沈兰心却不再看他们。那两道渗人的目光,死死定在赵管家攥得死紧的汗巾上!
那是前年冬她顶着高烧亲手绣了月余,送给陈绍桓的生辰礼!
陈绍桓嫌弃这“寒酸玩意儿”上不得台面,转手就丢给了管家!她的眼睛,一眨不眨,
钉子般钉着那块汗巾,像是要穿透那细密的针脚,烧出两个洞来。突然!
瘦骨嶙峋的手指抬了起来,
直直指向拔步床后那面紫檀嵌理石花鸟纹立屏后摆着的黄杨木雕海棠花罩的多宝阁顶端!
“拿……那个……”声音像是两片钝铁在摩擦,嘶哑粗糙得不成样子,
每一个音节都像用尽了她肺里最后一点浑浊的气,
“……红木描金海棠纹……盒……”赵管家浑身一激灵!
顺着那指甲开裂、冻得乌青却带着不可违拗之势的手指看过去。那盒子?
里面装着沈兰心压箱底的几件陪嫁,一些早被遗忘的零碎首饰。这关头……她竟要看这些?!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抗拒,喉咙发干:“少、少奶奶……您刚脱险,
保重身子要紧……”话音未落。那双枯井般的眼睛倏地转向他!冷!无边的冷,
夹杂着一股蛮兽垂死也要反咬猎物喉咙的狠厉!“拿。”只有一个字。
砸在死寂的空气里,比外面的冰渣子更硬更沉。赵管家头皮瞬间炸开!膝盖莫名一软,
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窜上来!周大夫早已吓得退到墙角,低着头,
恨不得将自己缩进那描金彩绘的博古架里!再不敢多言半句!
赵管家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扑到那多宝阁前,抖着手,踮着脚尖,
小心翼翼地将顶上一个蒙了些微灰尘的、约莫一尺见方的描金海棠红木盒子捧了下来。
盒子很沉。他弯着腰,双手微微发颤地捧着它,一步一步挪到榻前。不敢直接递过去,
只弯腰放在榻边的乌木小几上。沈兰心的眼珠,像是被无形的丝线牵引,
死死随着那盒子移动。直到盒子落定。她用尽全身力气,将僵硬冰冷的手臂抬起一寸,
痉挛的手指颤抖着摸索着盒子正面那小小的、嵌着绿松石花瓣的如意头铜锁扣。“咔哒”。
清脆的机簧弹开声。盒子掀开。一层柔软褪色的明黄缎子下,赫然躺着一只点翠头面!
云鬓轻挽的点翠!却不是整套。只孤零零一只。繁复精细到了极致!
金丝掐成的累丝凤鸟,翼展翩然欲飞,点缀其上的点翠羽毛并非整片,
而是用了失传的“弹毛点翠”古法——羽毛小如粟米,一羽一针,点嵌在金丝胎体之上!
那蓝色,深如子夜雨后初晴的远空,又带着虹鸟尾羽般变幻的幽魅光泽!
凤鸟嘴里衔着三缕细金链垂下的水滴状红宝流苏,此刻在摇曳烛火下,
映着沈兰心死水般的眼睛,猩红得像凝固的血珠!寂静。只有沈兰心粗重如风箱的喘息,
混着她指尖抚过点翠羽毛微凉光滑的触感,带来一点诡异的真实。
“嗬……”又是一声模糊嘶哑的气音从她喉咙里挤出。
在赵管家和周大夫惊疑不定、如芒在背的目光里,
沈兰心那只冻得乌紫开裂、指甲缝里嵌着冰渣泥垢的手,像是寻到了支撑的藤蔓,
竟颤巍巍、却无比坚定地伸向那只华美得不合时宜的点翠!冰到刺骨的手指,
终于触碰到了那幽蓝冷硬的翅膀边缘!用力!攥紧!
“叮…铃…”水滴红宝流苏撞在金丝凤羽上,发出极轻微、带着某种玉石俱焚寒意的脆响,
在死寂的卧房里回荡开来。3“咔哒。”描金海棠纹盒子盖上,沉闷的一声钝响,
掐灭了那幽蓝点翠最后一丝冷光。沈兰心攥着那点翠金翅的手垂放在身侧锦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