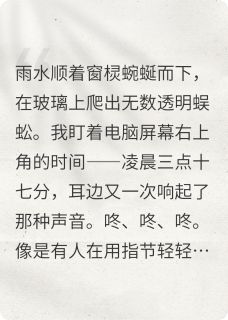雨水顺着窗棂蜿蜒而下,在玻璃上爬出无数透明蜈蚣。
我盯着电脑屏幕右上角的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耳边又一次响起了那种声音。
咚、咚、咚。像是有人在用指节轻轻叩击石膏板,节奏精准得如同心跳。我放下马克杯,
杯底与桌面碰撞的声响立刻引来了墙壁里更急促的回应,
力度大得让挂在墙上的画框微微震颤。"又来了..."我搓了搓泛起鸡皮疙瘩的手臂,
抓起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这是搬进这间公寓的第七天,
也是我第三次在深夜记录这种诡异声响。前两次的录音在白天回放时只剩沙沙的电流杂音,
仿佛那些敲击从未存在过。窗外的雨更大了。我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
小心翼翼地将耳朵贴在发出声响的墙壁上。霉味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腥气钻入鼻腔,
墙纸下隐约可见一片不规则的暗黄色水渍,形状像极了侧卧的人形。"黎**?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我几乎跳起来。回头看见门缝下塞着一张对折的纸条,
边缘被雨水渗出锯齿状痕迹。我打开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对面房间的门轻轻晃动,
门牌上积着厚厚的灰尘。纸条上用颤抖的字迹写着:"别回应墙里的声音——张阿婆"。
我并不认识这位老人,只有前天在楼梯间遇见过一次。她看我的眼神活像在看一个将死之人。
"这栋楼不干净。"她当时用漏风的声音说,"特别是你住的307,
上一个租客..."话没说完就被她儿子拽回了屋里。手机突然震动,主编发来消息催稿。
我回到电脑前,发现文档里多出一行不在我记忆中的文字:"她正在学你打字的样子"。
寒意顺着脊背爬上后颈。我猛地合上笔记本,转身时瞥见浴室镜子里自己的倒影。
那个"我"的嘴角正以不正常的角度缓缓上扬,而我分明绷紧着脸。咚、咚、咚。
敲击声再次响起,这次来自浴室墙壁。我颤抖着打开水龙头,水流冲散了镜面上的雾气,
却冲不散那个逐渐清晰的的灰白面孔。它正贴在“我”的后背上,
将腐烂的手指搭在"我"的肩上,而镜外的我肩上空空如也。外面突然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
接着是瓷器碎裂的声音。我冲出门时,正看见张阿婆的儿子抱着个褪色的骨灰盒仓皇逃离。
雨水打湿的楼梯上,散落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每张照片里都有一堵墙,
墙上隐约浮现着不同的人脸。而最上面那张照片,
背面用褪色的血渍写着日期——正好是二十年前的今天。1雨水浸透了老旧的木质楼梯,
我光着脚踩上去,冰冷的触感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蹲下身,
指尖颤抖地触碰那些被泡得发软的旧照片。最上面那张已经卷边,翻过来,
背面是用早已干涸发黑的血渍写下的日期——二十年前的今天。心脏猛地一缩。
我一张张捡起来,水珠顺着照片边缘滴落,像是它们在流泪。十几张照片,
拍摄的地点全都是我住的307房间。不同年份,不同租客,但背景里那面墙始终没变。
墙纸剥落,霉斑蔓延,每一张照片里,那片暗黄色的水渍都在。只是,水渍里浮现的人脸,
各不相同。有老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他们都在无声地看着镜头。我的呼吸凝滞了,
直到看见最后一张。那是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粉色的公主裙,站在我父母中间。
我们笑得很开心。那是我最珍爱的一张全家福,一直放在我老家的相册里。
它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强迫自己仔细看。照片里的我,肩膀上搭着一只手。惨白、浮肿,
那是不属于我们三个人中任何一个的手。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几乎要把昨晚的速食面吐出来。我慌乱地翻找口袋,
摸出张阿婆儿子逃跑时掉落的那张皱巴巴的名片。“王立强,货运服务”。
我哆哆嗦嗦地按下那一串数字。“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冰冷的机械女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响,格外刺耳。我挂断电话,准备将名片撕碎。
手机屏幕却突然亮起。
】发件人:+8613…(就是我刚刚拨打的那个空号)我的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我点开彩信。照片里,一个女人正狼狈地蹲在阴暗的楼梯上,手指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个女人,是我。照片的视角,来自楼梯的拐角阴影处。照片下方,跟着一行字。
“我知道你在找我。”“哎呀,黎**,怎么坐地上啦?这楼梯刚下过雨,又湿又脏的,
快起来快起来。”一个过分热情的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是房东。他脸上堆着笑,
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还是……房子有什么问题?”他一边说,
一边伸出手想拉我。我猛地向后一缩,躲开了他的手。“我没事。”我攥紧手里的照片,
站起身。“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看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别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有事尽管跟叔说,千万别客气。”他搓着手,视线状似无意地扫过我手里的照片,
又落在我房间那面墙的方向。“对了,黎**,你之前不是说墙壁有点渗水吗?我找了师傅,
明天就可以过来帮你免费重新粉刷一遍,保证弄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
”他笑得更灿烂了。“免费的,就当是叔送你的乔迁礼物了。”我死死盯着他。
他那双热情伸出的手,指甲缝里,残留着和墙上水渍一模一样的暗黄色污垢。
像是刚用手抠过那面发霉的墙。2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离了那栋公寓,打车直奔我父母家。
那是我最后的避风港。“爸,妈!”我一脚踹开门,
把湿透的照片和手机一股脑地拍在餐桌上。“这房子有问题!有鬼!它在跟着我!
”我语无伦次,把照片上的鬼手、诡异的彩信还有房东的事情全都吼了出来。
父亲的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放下手里的报纸。母亲端着一盘水果从厨房出来,
脸上带着责备。“黎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多大的人了,还这么疯疯癫癫的。
”“我没有疯!你们看!看这张照片!”我把那张童年合影推到他们面前。父亲拿起照片,
扶了扶老花镜,看了半天。“这不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吗?哪有什么鬼的手?”“怎么可能!
”我抢过照片,那只惨白的手明明就搭在我的肩膀上,那么清晰,那么刺眼。
可在我父母的脸上,我只看到了困惑和不耐。母亲叹了口气,把水果盘重重地放在桌上。
“黎黎,我知道你最近写稿子压力大,但也不能这么自己吓自己。是不是又熬夜了?
”“我没有!我说的是真的!”“够了!”父亲猛地一拍桌子。“我看你就是魔怔了!
什么鬼神,都是假的!为了你好,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哪儿也别去。
手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先替你保管!”他不由分说地收走了我的手机和那些照片。
“爸!你不能这样!”“我们都是为你好!等你什么时候清醒了,再把东西还给你!
”我被他们强行推进了我童年的卧室,门在外面被反锁了。无力感淹没了我。
我环顾这个曾经带给我无数安全感的房间,粉色的墙纸,贴着星星的天花板。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想找点慰藉。那个我珍藏了十几年的,
装满了我所有童年秘密的蓝色音乐盒,不见了。我发疯似的拍打着房门。“妈!
我的音乐盒呢!我的音乐盒去哪了?”门外传来母亲轻描淡写的回答。“哦,那个啊。
前几天邻居张阿姨带她孙子过来玩,那孩子瞧着喜欢,哭着闹着要,我就送给他们了。
一个破盒子而已,你都多大了,还留着干嘛。”“那不是破盒子!”我感觉血液冲上了头顶。
趁着他们开门送晚饭的间隙,我猛地冲了出去,直奔对门邻居家。张阿姨开了门,一脸不悦。
“干什么啊?火急火燎的。”“阿姨,我妈送给你孙子的音乐盒呢?请你还给我!
”“一个破玩意儿,至于吗?给你给你!”她不耐烦地把音乐盒塞进我怀里。我冲回楼道,
颤抖着打开音乐盒。里面空空如也。
我小时候放进去的玻璃弹珠、第一颗乳牙、写着暗恋对象名字的纸条……全都不见了。
只有一张被折叠起来的,新的小纸条,躺在盒子底部。我展开它。上面是陌生的笔迹,
却写着无比熟悉的话。“你的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深夜,我被反锁在卧室内,心如死灰。
万籁俱寂中,客厅里隐约传来了笑声。是我父母的笑声。我爬下床,趴在门上,
透过猫眼向外看。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我的父母,还有……另一个“我”。
那个“我”穿着我最喜欢的睡衣,正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后来啊,
我就偷偷把爸爸的烟藏起来了,结果害他找了一整天,妈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
你这孩子,从小就调皮。”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亲昵地拍了拍“我”的头。
父亲也在一旁哈哈大笑,满脸宠溺。他们正在聊着我童年的糗事,
那些只属于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而那个窃取了我的一切的“我”,在故事的间隙,
缓缓抬起头,隔着遥远的距离,精准地对上了猫眼。“它”冲着我的方向,
露出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灿烂的微笑。3我用一把生锈的美工刀撬开了卧室的门锁,
在凌晨四点逃离了那个已经不再是“家”的地方。我住进了一家匿名的快捷酒店,
用现金付了款。我需要喘息,哪怕只有片刻。我把自己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强迫自己入睡。睡前,我点了一份牛肉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半,把餐盘放在了门口。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刺眼的阳光弄醒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餐盘。
里面是另一份牛肉炒饭,同样的热气腾腾,同样被吃了一半。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我冲到前台,问他们为什么送了两次餐。前台的女孩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我们的系统显示,您昨晚只点了一次餐,而且记录是在晚上十点。之后没有任何点餐记录。
”“不可能!那这个是谁送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要不,您看看监控?”我逃离了酒店。
那东西,已经不是局限于某个地点了,它像病毒一样,附着在了我的身上。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像个孤魂野鬼。酒店大堂里,
一个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突然停下脚步,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然后猛地拽住他妈妈的衣角,
用尽全身力气尖叫起来。“妈妈!妈妈你看!那个阿姨身上有两个人叠在一起!
”他的声音又尖又利,整个大堂的人都朝我看了过来。他妈妈一把捂住他的嘴,
尴尬地对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胡说八道。”她说完,
拖着还在挣扎的孩子飞快地跑了。我冲进一家咖啡馆,想找个角落躲起来。
我必须联系我唯一还信任的朋友,告诉她一切。我刚选好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一个三口之家就径直走了过来,未经询问就坐在了我的对面。“你好,这里没人吧?
我们拼个桌。”那个男人理所当然地开口。他妻子则不停地抱怨。“挤死了,
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吗?你看这桌子小的,待会儿东西都放不下。”他们的孩子,
一个看起来五六岁的男孩,正拿着一杯满当当的冰水,
好奇地打量着我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别乱动!”我下意识地把电脑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孩子的母亲立刻不高兴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儿子碰一下怎么了?
你的电脑是金子做的啊?这么宝贝?”“就是,看你穿得穷酸样,
这破电脑估计也就值个一两千块钱吧?碰坏了我们赔得起!”男人在一旁帮腔。
我不想和他们争吵,只想快点联系朋友。就在我打开电脑,输入密码的瞬间,
那个孩子突然咧嘴一笑,猛地将手里的那杯冰水泼在了我的键盘上。滋滋啦啦。
一阵电火花闪过,屏幕瞬间黑了下去。“哎呀!你这孩子!”女人夸张地叫了一声,
却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反而拉着孩子的手,用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说。“你看你,
把阿姨的电脑弄坏了吧?快跟阿姨说对不起。”男人则掏出钱包,
抽出几张百元大钞扔在桌上。“行了,别演了。不就一台破电脑吗?这点钱够你再买一台了。
我们走!”他们一家三口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在电脑屏幕彻底熄灭前的最后一秒,
我从黑色的镜面反光里,清晰地看到。一个灰白色的轮廓,正紧紧贴在我的身后。
“它”对着屏幕里的我,露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微笑。4我失去了所有。
手机、电脑、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我像一个被世界剔除的错误代码,
游荡在冰冷的城市里。记忆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知道真相的人,那个张阿婆的儿子,
王立强。我凭着名片上那个模糊的货运公司地址,在城中村的迷宫里找了整整一天,
才在一个散发着酸臭味的筒子楼里找到了他。他打开门,看到我的瞬间,
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你……你怎么找来的!”他想关门,
我用身体死死抵住。“你妈到底知道了什么?墙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必须告诉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快走!快走!”他惊恐地推搡着我,像是我是什么瘟疫。“你不说,
我就报警!我说你母亲的死有蹊疑,警察第一个就查你!”这句话似乎击中了他的软肋。
他浑身一颤,停止了挣扎,绝望地看着我。几秒钟后,他冲回屋内,
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像是甩一个烫手山芋一样,狠狠地扔到我怀里。“真相!
你要的真相全在里面!拿了它,赶紧滚!永远别再来找我!”他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抱着冰冷的铁盒,坐在肮脏的楼梯上,颤抖着打开了锁扣。
他嘶哑的仿佛从地狱里传来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二十年前,
这栋公寓楼还不是公寓楼,是一家黑诊所,专门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妈……你妈当年怀的是双胞胎。”铁盒里没有我想象中的照片或信件。
只有两份官方文件。一份,是我的出生证明。黎夏,女,出生日期……一切都对得上。
另一份,是一张死亡证明。死者姓名那一栏,赫然写着另一个名字。黎秋。
死亡原因:新生儿畸形,先天孱弱,器官衰竭。死亡日期,和我的出生日期,是同一天。
王立强的话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他们和诊所达成了协议,用一点钱,
处理掉这个‘残次品’,只带走健康的那个。”“她的尸体,被诊所的医生混进水泥里,
砌进了307房间那面墙。”“她恨你偷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父母的爱,健康的身体,
二十年的人生。”“她是回来讨债的!她要拿回她的人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活在她的影子里,被她的怨恨追逐。我拿起那两份证明,想把它们撕碎。
指尖却在触碰到纸张的瞬间,僵住了。不对,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死死盯着那两份文件,
逐字逐句地看。出生证明上,婴儿体重:2.1kg。死亡证明上,婴儿体重:3.5kg。
我的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向我炫耀,说我出生时白白胖胖,足有七斤重。一个念头,
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我的灵魂。我颤抖着,将两份文件并排放在地上。出生证明上,
“黎夏”的名字旁边,有一栏“体貌特征”,上面潦草地写着:左手六指。
我猛地看向我的左手。五根健全的手指。我的人生,从没有过第六根手指。
而那张死亡证明上,“黎秋”的“体貌特征”一栏,写着:一切正常。我明白了,
我全都明白了。我才是那个被记录在死亡证明上的“黎秋”。而墙里的那个,
她才是“黎夏”。我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从我姐姐那里“借”来的。5我以为我会崩溃,
会被那个真相彻底碾碎,然后被墙里的姐姐吞噬。可我没有。在我灵魂被掏空的那个瞬间,
我感觉到那股一直萦绕在我身边的阴冷怨气,突然犹豫了。它在我身边盘旋,
带着一种嫌恶和失望。我突然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明白了,它看不上我。
我这具被常年熬夜、焦虑、垃圾食品和不规律作息掏空了的身体,
根本不是它想要的那个“完美”容器。它要拿回的是它二十年前那个健康完美的人生,
而不是我这个被生活折磨得一塌糊涂的残次品。它需要一个更好的。这个认知,像一把刀,
给了我最后一击,却也让我从极致的绝望中,找到了一丝活下去的缝隙。房东。
那个热情得过分的男人。他为什么要免费粉刷墙壁?为什么要掩盖真相?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我脑海里。他在为我姐姐寻找新的身体。他以低价出租为诱饵,
吸引那些年轻健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女孩住进去。这他妈就是一个邪恶的“水滴筹”,
筹集的不是钱,是鲜活的生命和完美的躯壳!我必须回去,我跌跌撞撞地跑回那栋公寓。
天色已晚,楼道里却灯火通明。房东正在大张旗鼓地指挥着几个工人,
在楼道里挂上红色的灯笼和彩带。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房东,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反而笑呵呵地走过来。“黎**回来啦?
这不是快到咱们这楼拆迁二十周年纪念日了嘛,大喜的日子,我寻思着好好庆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