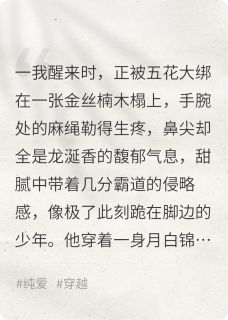一我醒来时,正被五花大绑在一张金丝楠木榻上,手腕处的麻绳勒得生疼,
鼻尖却全是龙涎香的馥郁气息,甜腻中带着几分霸道的侵略感,像极了此刻跪在脚边的少年。
他穿着一身月白锦袍,墨发用玉簪松松挽着,眉眼本是清俊得像幅水墨画,
此刻却覆着层化不开的阴鸷。眼尾泛着不正常的绯红,像是极力压抑着什么,
声音发颤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戾:“师兄,你若再逃一次,我便挑断你的脚筋。
”我当场宕机——这台词、这场景、这少年眼底翻涌的偏执,我太熟了。
正是那本让我吐槽了三天三夜的狗血古早文《折玉》里的经典病娇桥段。而我,好巧不巧,
穿成了那个被病娇师弟囚之笼中、最后下场凄惨的炮灰大师兄——沈折玉。原著里,
沈折玉骨头硬得很,被囚三年,愣是策划了九次逃跑。每一次被抓回来,
等待他的都是更严密的禁锢和更深的绝望,最后双腿被生生打断,成了个废人。饶是如此,
他还在大结局里为了成全主角攻受的“旷世绝恋”,拖着残躯冲进漫天风雪里,
自刎在了那棵他们初遇的梨树下。我下意识动了动脚趾,感受着双腿传来的知觉,
默默算了算时间线:看师弟这副刚经历过“抓逃”的模样,现在正是第一次逃跑失败后。
也就是说,按照情节走,接下来还有八次惊心动魄的大逃杀,
以及一次为他人作嫁衣的悲壮自杀在等我。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脚边少年那双写满“你敢逃我就毁了你”的眼睛,果断选择摆烂。什么主角光环,
什么情节走向,保命要紧。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无害,
甚至带了点刚睡醒的慵懒:“不逃了,师弟。”少年猛地抬头,
眸底的阴鸷像被投入石子的深潭,瞬间激起层层涟漪。我再接再厉,
带着点示弱的委屈:“真不逃了,你看,被绑了这么久,我腿都麻了,能不能先松开?
”少年彻底愣住了,握着麻绳的手指微微收紧,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翻涌的偏执与阴鸷,
竟真的化开了一点点,露出几分难以置信的茫然,像是没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
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松开手,动作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小心翼翼,
替我解开了手腕和脚踝上的绳子。麻绳褪去的瞬间,手腕上留下几道红痕,
他盯着那痕迹看了半晌,忽然转身,不多时便捧来一碗桂花糖蒸栗粉糕。
白瓷碗里的粉糕冒着热气,撒着细碎的桂花,甜香混着龙涎香飘过来,竟意外和谐。
我也不客气,接过碗就吃了起来。软糯的栗粉糕在舌尖化开,桂花的清甜漫开来,
熨帖了五脏六腑。我吃得心安理得,心想:只要我不作死,不主动触发逃跑情节,
那该死的情节线就绝对追不上我。少年就坐在榻边,一瞬不瞬地看着我,
眸子里的阴云渐渐散去,露出点像小兽般的温顺来。二摆烂第一条:远离主角。
我把自己关在后山那片茂密的竹林里,寻了处临溪的竹屋住下。
每日天刚亮就搬张竹凳坐在溪边钓鱼,鱼竿是随手削的竹枝,鱼饵是挖来的红蚯蚓,
钓不钓得到鱼全看天意。日头升到头顶便挪到竹林深处的青石上晒太阳,
看光斑透过竹叶在衣襟上晃悠,偶尔给停在肩头的山雀起些“灰灰”“点点”之类的俗名。
如此逍遥了七日,终究还是没能躲过情节的引力。那天午后,我正眯着眼数竹节,
就听见一阵轻快的脚步声穿过竹林,伴随着少年清朗的嗓音:“师兄,我来给你送午饭啦。
”我睁开眼,就见谢遥提着个竹篮站在竹屋门口,一身浅碧色的短打,衬得他愈发面如冠玉,
正是那本《折玉》里颠倒众生的主角受。他几步走到我面前,笑着掀开竹篮盖子,
顿时香气扑鼻——胭脂鹅脯油光锃亮,松瓤酥层层起酥,还有清清爽爽的玉笋蕨菜,
全是原著里沈折玉最爱的几样。谢遥笑得乖巧,眉眼弯成了月牙,
声音软得像棉花糖:“师兄这几日清减了许多,我想着亲手做些你爱吃的,尝尝?
”我心里门儿清,原著里谢遥此刻早已对我那病娇师弟情根深种,这趟送饭哪是真心惦记我,
分明是替他那位偏执师弟来探我的口风,看看我是否还存着逃跑的念头。按情节走,
我该故作冷淡地应一句“师弟待我极好”,谢遥回去定会对着病娇师弟哭红了眼,
暗叹自己爱而不得,然后两人的感情在误会与试探中愈发纠缠,
情节便会踩着我的炮灰人生继续狂奔。我偏不。谢遥把碗筷摆好,期待地看着我。
我夹了一筷子胭脂鹅脯放进嘴里,细细嚼了嚼,然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搁,
一本正经道:“你盐放重了,齁得慌,下次少放一勺。”谢遥脸上的笑容僵住,
像是没料到会得到这样的评价,长长的睫毛颤了颤,耳尖却慢慢红了,
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颈。他低下头,小声说:“是我疏忽了……那……我明日少放一勺。
”第二日,他果然准时提着竹篮来,饭菜里的盐味恰到好处。不仅如此,
竹篮里还多了一罐玫瑰卤,琥珀色的卤汁里浮着整朵的玫瑰,看着就让人舒心。
我舀了一勺拌进米饭,依旧挑三拣四:“玫瑰卤甜了些,该多搁点陈皮压一压。
”他认真点头,次日送来的玫瑰卤便多了几分清苦的回甘。如此过了半月,
谢遥的菜越做越合我口味,从火候到调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也从最初的“挑剔师兄”,
渐渐成了他口中“最懂滋味”的试菜大师。有时他新学了点心样式,
会巴巴地跑来看我尝第一口;有时我随口提一句“想吃溪水煮的鲜笋”,
第二日竹篮里就会躺着带泥的新笋。竹林里开始流传些闲言碎语,说后山那位沈师兄,
嘴比淬了冰的剑还毒,挑刺的本事无人能及,可那颗心呐,
却比刚点的豆腐还要软——不然怎会日日等着谢师弟送饭,
还把人家做的点心吃得一点不剩呢?三摆烂第二条:不搞事业。
宗门大比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我正坐在竹屋前逗那只名叫“灰灰”的山雀。
长老拄着拐杖找上门来,胡须翘得老高:“折玉,此次大比你修为最深,理当带队参赛,
莫要坠了咱们凌霄峰的名头。”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段情节我记得清楚。原著里,
沈折玉为了护着刚入门的谢遥,在大比中被人暗算,硬是凭着一股蛮力强行突破境界,
结果落得个经脉寸断的下场,从此修为尽废,成了病娇师弟眼中更“好掌控”的存在。
我当即往后缩了缩肩膀,捂着心口轻咳两声,脸上挤出几分虚弱:“长老恕罪,
弟子近来总觉体虚气短,怕是连剑都提不动,实在难当此任。”长老被我气得吹胡子瞪眼,
拐杖在地上笃笃敲了好几下:“没出息的东西!带队不行,那便去藏经阁抄经养性!
抄不满百卷,不准出来!”我连忙作揖,欣然领命:“弟子遵令。”藏经阁果然清净,
三层高的楼阁里堆满了泛黄的古籍,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进来,落在积着薄尘的书架上,
有种岁月静好的安稳感。我每日挑本顺眼的经书,慢悠悠抄上两页,困了就直接趴在案几上,
枕着《清静经》呼呼大睡,日子过得比在竹林里还惬意。直到某夜,
我正梦见自己钓上一条三尺长的大鱼,鼻尖忽然钻进一缕熟悉的龙涎香。紧接着,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抽走了我枕着的经书。我迷迷糊糊睁开眼,
就见病娇师弟站在窗前的月光里,玄色衣袍上落着细碎的银辉,墨发垂在肩头,
眸色沉沉得像化不开的夜。他盯着我,
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委屈:“师兄宁愿对着这些冰冷的书页抄经,也不愿看我一眼?
”我困得眼皮打架,脑子都转不动,随口就来:“你好看,经书也好看,我都爱看。
”他像是被这句话烫了一下,呼吸猛地一滞,眸底翻涌的情绪忽然定住。半晌,
他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点释然,又有点藏不住的雀跃:“那师兄以后日日看着我,
可好?”我实在太困了,含糊地应了一声“嗯”,翻了个身就又沉沉睡了过去,
压根没听清他后面说的什么。第二日醒来时,天光已经大亮。我伸了个懒腰,
手腕处忽然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低头一看,不知何时多了一串细银链,
链身打磨得光滑温润,末端坠着一块小小的白玉牌,上面用篆文刻着一个“昭”字。
那是师弟的名字,凌昭。我晃了晃手腕,银链碰撞着发出叮当作响的清脆声音,
心里忍不住嘀咕:这算什么?病娇专属的牵引绳?也罢。我捻着那块温凉的玉牌想,
戴着它也好,至少能让凌昭安心些,省得他总疑神疑鬼,动不动就觉得我要逃跑。这么想着,
我把银链往手腕里收了收,继续拿起笔,在宣纸上慢悠悠地抄写“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四摆烂第三条:不抢男人。宗门新收的弟子里,有个叫顾雪庭的,
生得一副惊为天人的好样貌。一袭白衣胜雪,腰间悬着柄古朴长剑,站在人群里,
自带一股“千山鸟飞绝”的清冷气场。听说他剑术卓绝,
初入山门便在演武场挑落了三位内门弟子,端的是“一剑霜寒十四州”的架势。
我隔着老远瞥了一眼,心里门儿清——这不就是《折玉》里的正牌攻吗?原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