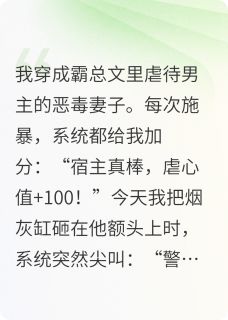我穿成霸总文里虐待男主的恶毒妻子。每次施暴,系统都给我加分:“宿主真棒,
虐心值+100!”今天我把烟灰缸砸在他额头上时,系统突然尖叫:“警告!世界线崩溃!
”再睁眼,我成了病床上植物人状态的霸总丈夫。而我的身体里,住着刚苏醒的他。
他捏着我的下巴冷笑:“这具身体,感觉如何?”后来我替他签下百亿订单,
他穿着我的裙子学跳女团舞。系统突然提示:“故障修复完成,是否解除身体绑定?
”我们同时按住了对方的手。——“同步率100%”。---浓稠的黑暗里,
只有水晶烟灰缸划过空气的破风声格外刺耳。“咚!”沉闷的撞击声,
伴随着一声压抑的闷哼,在过分空旷的卧室里荡开一圈令人牙酸的回音。林砚倒在地上,
昂贵的丝绒地毯吸走了大部分冲击力,但他额角绽开的那道口子却异常醒目。
鲜红的血珠争先恐后地涌出来,迅速蜿蜒而下,滑过他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颊,
最后滴落,在浅灰色的地毯上洇开一小团暗色污迹。他蜷缩着身体,
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身体因剧痛而微微痉挛,
那双总是沉静如古井的眼睛此刻死死盯着我,里面翻涌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火焰,
将我焚烧殆尽。冰冷的电子音在我脑中毫无波澜地响起:【检测到有效伤害,
虐心值+100。宿主,请再接再厉。】再接再厉?我扯动嘴角,
一个扭曲的笑容不受控制地爬上我的脸。很好,又是100点。
距离系统承诺的“攒够10000点虐心值就能回家”的目标,又近了一小步。
这具身体——苏晚,
这个顶着豪门贵妇光环、内里却腐烂发臭的灵魂——似乎天生就擅长制造痛苦。
每一次将林砚踩在脚下,看着他骄傲的脊梁被迫弯曲,看着他眼中压抑的屈辱和恨火,
我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深处传来一丝诡异的、近乎病态的满足感。
那是原主残存的疯狂执念在作祟,而系统冰冷的加分提示,更是不断为这疯狂添柴加火。
林砚挣扎着想撑起身,沾着血迹的手在地毯上留下模糊的印痕。他的呼吸粗重而急促,
每一次吸气都牵动着额角狰狞的伤口。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脚尖毫不留情地碾上他试图支撑的手背。“林总,”我的声音刻意放得又轻又慢,
带着淬毒的甜腻,模仿着记忆中苏晚那种令人作呕的腔调,“不是骨头很硬吗?
不是瞧不上我这个‘低贱’的女人吗?怎么,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脚底用力,
满意地听到他指骨发出不堪重负的轻响。他猛地抬头,血污衬得他眼神愈发凶狠噬人,
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他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
嘶哑的声音从齿缝里挤出:“苏晚…你最好…祈祷我永远爬不起来…”“呵,”我嗤笑一声,
脚尖的力道更重,“那你就继续趴着吧,像条狗一样。我等着看你林大总裁,
怎么让我‘后悔’。”我弯下腰,
伸手想去拍他那张被血污弄脏、却依然俊美得惊心动魄的脸,带着十足的羞辱意味。
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他皮肤的刹那——【警告!警告!世界线核心锚点遭受未知冲击!
错误!严重错误!】脑海里尖锐的警报声如同无数把钢针瞬间刺入,
比我听过的任何一次系统提示都要刺耳百倍!那冰冷的电子音扭曲变形,
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慌失措。【数据流紊乱…逻辑链断裂…无法解析…尝试紧急修复…失败!
重复,紧急修复失败!】【世界线稳定性…崩溃!崩溃!崩溃!】最后那三个“崩溃”,
带着一种末日降临般的绝望,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我的意识深处。眼前的一切,
奢华的水晶吊灯,昂贵的波斯地毯,
林砚染血的脸和他眼中刻骨的恨意…所有景象都开始疯狂地旋转、扭曲、拉伸变形!
墙壁像融化的蜡一样流淌下来,色彩混杂交融,发出无声的尖叫。
一股无法抗拒的、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猛地攫住了我,
仿佛整个存在都要被这股狂暴的乱流彻底撕碎、碾成齑粉!黑暗吞噬了所有感知。
意识像是沉入了冰冷粘稠的深海,没有光,没有声音,只有无边无际的沉重和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也许是永恒,一丝微弱的感觉艰难地刺破黑暗,传递进来。
冷。刺骨的冷意,沿着脊椎蛇一般向上蔓延。这冷意并非来自外界,
更像是从这具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一种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枯寂。眼皮沉重得如同灌了铅。
我调动了全身的力气,才勉强掀开一条缝隙。视野是模糊的,
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布满水汽的毛玻璃。光影在眼前晃动、重叠,
只能勉强分辨出头顶是一片单调的、毫无生气的白色天花板。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混合着消毒水和某种药物苦涩气味的冰冷气息。医院。
这个认知像冰水一样浇遍全身。我…我在哪里?我不是在别墅里,
刚刚才用烟灰缸砸破了林砚的头吗?那该死的系统崩溃的警报…难道…难道我真的死了?
还是…?混乱的念头在脑中疯狂冲撞。我试图转动眼珠,想看清周围。
脖子僵硬得如同生了锈的铁块,
每一次细微的移动都伴随着骨骼摩擦的艰涩感和难以忍受的酸痛。
视线艰难地、极其缓慢地向右偏移。模糊的视野边缘,捕捉到了一抹突兀的色彩。
那似乎是…一束花?插在床头柜的花瓶里。颜色很鲜亮,大概是俗气的康乃馨或者百合?
花瓣的边缘在视野里微微颤动。紧接着,一个身影闯入了我极其有限的视野范围。一个女人。
她背对着我,站在离床不远的地方。身形很熟悉,高挑,
穿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米白色羊绒连衣裙,勾勒出姣好的曲线。微卷的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
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那是…我的身体!我认得那条裙子,认得那个发型!那是苏晚的身体!
巨大的惊骇瞬间攫住了我,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停止跳动。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站在那里?!
那…那现在躺在这张冰冷病床上、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困难的人…是谁?!
极度的恐惧催生出一股蛮力。我猛地吸了一口气,肺部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嘶哑难听的抽气声。这声音惊动了床边的人。
那个背对着我的身影——那个占据着“苏晚”身体的存在——猛地转过了身。
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那张脸,毫无疑问,是我每天在镜子里看到的那张属于苏晚的脸。
精致,美丽,带着一丝被金钱和纵容滋养出的骄矜。然而,此刻镶嵌在这张脸上的一双眼睛,
却是我从未在苏晚脸上见过的眼神。冰冷,幽深,如同千年不化的寒潭。
里面翻涌着浓得化不开的、沉淀了太久太久的恨意,像淬了毒的冰棱,直直地刺向我。
那眼神…那眼神是林砚的!“苏晚”…不,是占据了苏晚身体的林砚,他抬步走了过来。
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缓慢,高跟鞋踩在冰冷坚硬的地砖上,
发出清脆又规律的“嗒…嗒…嗒…”声,在这死寂的病房里,如同丧钟敲在我的神经上。
他停在了床边。居高临下。那张属于我的、此刻却充满了林砚灵魂的脸庞缓缓俯低,靠近。
冰冷的、带着淡淡香水味的气息拂过我的脸颊。他伸出了手。那只手,纤细,白皙,
涂着淡粉色的精致指甲。那是苏晚的手,此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属于林砚的强势力量,
狠狠地攫住了我的下巴!剧痛传来,下颌骨仿佛要被捏碎。他强迫我抬起头,
对上他那双寒冰般的眼睛。“醒了?”属于苏晚的声线,
吐出的却是林砚那特有的、低沉而充满磁性的腔调,
只是此刻这腔调里浸满了令人骨髓发凉的讥诮和刻毒,“这具身体…感觉如何?林、太、太?
”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针,扎进我的耳膜。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恐惧瞬间将我淹没。
我的灵魂…在苏晚的身体里?
而现在这个用苏晚的身体捏着我的下巴、眼神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男人…是林砚?!他醒了?
!他用着我的身体?!我…我成了林砚?!
成了那个被我亲手砸破额头、踩在脚下的植物人丈夫?!喉咙里发出更剧烈的“嗬嗬”声,
我拼命地想摇头,想挣脱那只铁钳般的手,想大声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无论我怎么用力,这具属于林砚的身体都沉重得像一座大山,纹丝不动。
只有眼珠因为极度的惊恐和愤怒而剧烈地转动着,死死瞪着眼前这张既熟悉又无比陌生的脸。
他似乎很享受我这副惊恐绝望、任人宰割的模样。捏着我下巴的手指又加重了几分力道,
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里。他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用我的声音,
说着最冰冷的话:“很绝望,是不是?动不了?说不出话?只能像个废物一样躺在这里?
”他凑得更近,
近到我甚至能看清他(或者说“我”)瞳孔中映出的自己此刻狼狈惊恐的倒影,“别急,
苏晚…不,现在该叫你‘林砚’了?我们…有的是时间。”他松开手,我的头失去支撑,
重重地砸回枕头上,眼前一阵发黑。他直起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
眼神如同在看一堆肮脏的垃圾。“好好享受吧,‘林总’。”他最后几个字咬得极重,
带着无尽的嘲讽,“用你自己的身体,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
”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他转身,那抹米白色的身影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一步步走向病房门口,消失在门外刺眼的光线里。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不,
是只剩下“林砚”这具沉重的躯壳,和我被困在里面、疯狂尖叫的灵魂。
冰冷的绝望如同无数细密的毒针,密密麻麻地刺入我的四肢百骸,
将我钉死在这张代表屈辱和囚笼的病床上。身体交换了?系统崩溃了?
回家…彻底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那束鲜亮的康乃馨在模糊的视野里摇曳,
散发着虚假的生机。而我,成了自己亲手打造的囚笼里,唯一的囚徒。
时间在这间充斥着消毒水气味和绝望的病房里,仿佛失去了意义。分不清白天黑夜,
只有护工定时进来,带着职业性的麻木,完成那些擦洗、翻身、喂流食的动作。
每一次吞咽都像咽下滚烫的沙子,每一次被搬动身体都伴随着骨骼摩擦的剧痛。
林砚的身体沉重得像灌了铅,每一次微小的挪动都需要耗尽我所有的意志力。
那个占据着我身体的男人,林砚,成了这间病房最冷酷的“访客”。他每天都来,
穿着昂贵的定制衣裙,踩着优雅的高跟鞋,
带着一身与我(苏晚)身份格格不入的、属于上位者的凛冽气场。他并不总是说话,
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地站在床边,用那双属于苏晚的、却盛满了林砚冰冷恨意的眼睛,
无声地凌迟着我。像在欣赏一件由他亲手打造的、名为“绝望”的艺术品。偶尔,他会开口。
声音是我自己的,腔调却是他的。“今天气色不错,‘林总’。
”他用戴着钻戒的手指(那是我以前最喜欢的鸽子蛋),
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床头那束快要枯萎的花,“看来护工把你伺候得很好。”指尖用力,
一片花瓣被碾碎,暗红色的汁液沾染上他白皙的指尖,如同凝固的血。
“比我当年…躺在这里时,待遇好多了。”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
“毕竟,那时候你连护工都懒得给我请最好的,不是吗?”他的话像淬毒的冰锥,
精准地刺入我记忆中最不堪的角落。是的,原主苏晚为了省钱,也为了更狠地折磨林砚,
确实只请了最便宜、最敷衍的护工。那些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
带来一阵尖锐的羞耻和寒意。更多时候,他带来的是文件。
厚厚的、印着“林氏集团”烫金标志的文件。他优雅地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
慢条斯理地翻开。纸张摩擦的声音在死寂的病房里格外清晰。“这份,
”他用指尖点了点文件,指甲修剪得完美无瑕,“是城西那块地的开发案,董事会催得很紧,
等着你签字。”他抬起眼,眼神锐利如刀,“哦,不对,是等着‘我’签字。毕竟现在,
我才是林砚。”他嘴角噙着一丝残忍的笑意,“可惜啊,‘林总’你现在连笔都握不住。
你说,这价值几十亿的生意,该怎么办呢?”我死死地瞪着他,
喉咙里发出愤怒的“嗬嗬”声,徒劳地试图抬起那只沉重得如同灌了水泥的手臂。
身体背叛了我,纹丝不动。巨大的无力感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合上文件,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恶魔般的诱惑:“求我啊,‘林太太’。
像狗一样求我,或许…我会大发慈悲,替你签了它?”屈辱的火焰瞬间烧遍全身,
烧得我眼睛通红。我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地、死死地瞪着他。如果眼神能杀人,
他早已被我千刀万剐。他看着我眼中燃烧的恨意,反而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在病房里回荡,
冰冷又刺耳。“真硬气。”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摆,居高临下地睥睨着我,
“那就…继续躺着吧。看看你的林氏集团,在你的‘无能’下,还能撑多久。
”他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离开,留下那叠沉重的文件和更加沉重的绝望,沉沉地压在我的胸口,
几乎让我窒息。每一天,都是酷刑。直到那一天。天气似乎格外阴沉,
厚重的铅灰色云层低低压着,病房里光线昏暗。林砚像往常一样来了,
今天他穿了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裤装,衬得那张属于苏晚的脸庞线条更加冷硬。
他没有带文件,脸色比窗外的天色还要阴沉,眉宇间凝着一股压抑的、山雨欲来的风暴。
他没有立刻走到床边,而是站在门口,目光沉沉地扫视着这间病房,最终落在我身上。
那眼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冰冷,都要…复杂。除了恨,
似乎还翻涌着某种更深沉、更激烈的东西。他一步步走近,脚步比平时沉重。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像丧钟的余韵。他停在我床边,没有坐下。只是俯视着我,
那双眼睛里翻腾的情绪几乎要将我吞噬。空气仿佛凝固了,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开口,声音低沉沙哑,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出来。我茫然地看着他,试图从混乱的记忆里搜寻。
什么日子?林砚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不,都不是…原主苏晚的记忆里,
似乎没有特别标记这一天。他捕捉到了我的茫然,
嘴角扯出一个极其难看、充满了巨大讽刺和悲凉的弧度。
“呵…”他发出一声短促而冰冷的嗤笑,像是在嘲笑我的无知,又像是在嘲笑命运的无常。
“看来,你果然忘了。或者说,你‘苏晚’,从来就没有记得过。”他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在极力压制着什么。再开口时,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那是属于林砚灵魂深处的震颤:“七年前的今天,就在这里…隔壁的ICU病房,
”他抬起手,指向病房墙壁的方向,指尖微微发抖,“我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声音骤然拔高,带着一种撕裂般的痛楚和刻骨的恨意:“她求了你!跪在地上求你!
求你看在她为林家做牛做马一辈子的份上,
求你看在…看在我这个‘丈夫’还在病床上苟延残喘的份上…借给她五十万!就五十万!
只要五十万!她就能做那个该死的手术!她就能活下来!”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灵魂上!属于原主苏晚的记忆碎片轰然炸开!
张绝望到扭曲的脸…还有“苏晚”当时那副高高在上、充满了鄙夷和不耐烦的嘴脸…“没钱?
没钱就去死啊!别脏了我的地毯!”“而你!”林砚猛地弯下腰,
那张属于我的脸因为极致的愤怒和痛苦而扭曲变形,他一把揪住我病号服的领口,
巨大的力量勒得我几乎窒息!“你当时说了什么?!”他咆哮着,
温热的、带着血腥味的吐息喷在我的脸上,“你说‘没钱?没钱就去死啊!别脏了我的地毯!
’苏晚!你这个毒妇!那是人命!那是我妈!她看着你长大!她把你当亲女儿!
”他剧烈地喘息着,眼睛赤红,像一头被彻底激怒、濒临疯狂的野兽。“五十万!
对你来说不过是买一个包的钱!一个包!”他用力摇晃着我,病床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可你吝啬到连一条活路都不肯给!就因为你恨我!就因为你恨我林砚没给你想要的‘爱’!
你就把恨意发泄在我唯一的亲人身上!”“是你!苏晚!是你亲手杀了我妈!
”最后一句指控,如同惊雷在我耳边炸响!震得我灵魂都在颤抖!原主的罪孽…如此深重!
如此不可饶恕!巨大的冲击让我脑中一片空白,连挣扎都忘记了。
我看着眼前这张因滔天恨意而扭曲的、属于我自己的脸,
和绝望…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巨大震惊、恐惧和…一丝荒谬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愧疚感,
猛地攫住了我。这愧疚感并非完全属于我自己。它更像是这具属于林砚的身体,
在听到母亲惨死的真相时,本能地、不受控制地涌现出的巨大悲恸!
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哀伤和愤怒,如同海啸般席卷了我,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防线。眼泪,
毫无预兆地、汹涌地从我的眼眶里滚落出来。滚烫的,咸涩的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滑入鬓角,
浸湿了枕头。这泪水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是这具身体对亡母最原始、最深切的哀悼。
林砚看着我汹涌而出的眼泪,他揪着我衣领的手猛地僵住了。他眼中的疯狂恨意凝固了一瞬,
随即被一种更深的、难以置信的愕然和困惑所取代。他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松开了手,
踉跄着后退了一步,死死地盯着我脸上不断滑落的泪水,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只刚刚揪过衣领的手。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我压抑不住的、因为身体虚弱而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和他粗重而混乱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像一曲荒诞又悲怆的二重奏。
他脸上的表情剧烈地变幻着,震惊、困惑、暴怒、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最终,
所有的情绪都沉淀为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寒。他深深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复杂得让我心惊胆战。然后,他猛地转身,几乎是逃离一般,大步冲出了病房。
门被他用力甩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整个房间都在颤抖。我躺在冰冷的床上,
泪水依旧止不住地流淌。身体深处属于林砚的悲恸还在汹涌,
而我自己的灵魂则在巨大的冲击中瑟瑟发抖。那沉重的、关于他母亲死亡的真相,
像一座无形的大山,轰然压在了我的身上,也压在了我们之间那道本就深不见底的鸿沟之上。
隔阂并没有消失,但一种诡异的平静降临了。林砚依旧每天来,但不再刻意用言语**。
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翻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眉头紧锁。林氏集团庞大商业帝国的重担,
正通过那些冰冷的纸张,一点点压在他——或者说,压在我原本的身体上。
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眉宇间的疲惫,那并非身体上的劳累,而是一种精神被极度压榨后的枯竭。
他处理文件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神也越来越锐利,
属于林砚的商业天赋在这具女性的身体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代价是显而易见的。这天下午,
阳光难得地透过百叶窗缝隙洒进来几缕。林砚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正对着笔记本电脑开一个跨国视频会议。屏幕上是几个金发碧眼、表情严肃的高管。
他用流利的英文下达着指令,逻辑清晰,气势迫人,完全掌控着局面。然而,
就在会议接近尾声,他准备做总结陈词时,异变陡生!
urethesupplychainresilienceby…”(“因此,
我们必须确保供应链的韧性…”)他的声音突然卡住了。我看到他(我的身体)猛地一僵!
握着鼠标的手指瞬间蜷缩起来,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原本挺直的背脊微微佝偻下去,
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小腹的位置。那张属于我的脸,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
变得苍白如纸,额角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紧紧咬着下唇,
似乎在忍受着某种突如其来的、剧烈的痛苦。视频那头的高管还在等着他的下文,
疑惑地叫了一声:“Mr.Lin?”林砚猛地吸了一口气,强行挺直了背脊,
对着摄像头挤出一个极其僵硬的笑容,
wupwithZhang.Meetingadjourned.”(“抱歉,
有紧急的国内事务。决定不变,后续跟进找张助理。会议结束。”)不等对方回应,
他几乎是粗暴地合上了笔记本电脑!屏幕合上的瞬间,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
猛地向后靠在椅背上,身体微微发抖,呼吸急促而紊乱。他一只手死死按着小腹,
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痛苦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羞恼的慌乱。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这一幕,
一个荒谬又无比清晰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进我的脑海——生理期!是这具身体,苏晚的身体,
那该死的生理痛发作了!原主苏晚就有严重的痛经毛病,每次发作都痛不欲生,
需要靠强效止痛药才能熬过去。而现在,这个麻烦,精准地降临在了林砚身上!
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呼风唤雨的顶级商业巨子,
此刻正被女性最原始的生理疼痛折磨得狼狈不堪!
一股难以言喻的、带着点幸灾乐祸的荒谬感冲上我的心头。但紧接着,
我看到了他痛得发白的嘴唇和微微颤抖的肩膀,
那点幸灾乐祸又迅速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一丝…奇异的感同身受?毕竟,
我现在也困在一具陌生的、无法掌控的男性躯壳里。就在他痛得蜷缩在椅子上,
眼神都有些涣散时,病房门被敲响了。不等回应,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推门而入。是林砚的首席助理,张凯。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恭敬。“林总,”张凯微微躬身,
目光扫过椅子上状态明显不对的“林总”(林砚),
又看了一眼病床上躺着的“林太太”(我),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
但语气依旧平稳,“这份并购案的最终协议需要您签字,法务部那边催得很急,
对方代表已经在会议室等了半小时了。”林砚猛地抬头,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
似乎想呵斥张凯不懂规矩。但他刚一张口,小腹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袭来,
疼得他倒抽一口冷气,冷汗顺着额角滑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只能死死地瞪着张凯,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和…一丝难以掩饰的虚弱窘迫。张凯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但职业素养让他硬着头皮站在原地,双手恭敬地递上文件和笔:“林总,您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砚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按着小腹的手因为用力而青筋暴起。
他似乎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对抗那波汹涌的疼痛,根本无暇他顾。而张凯举着文件和笔,
姿势也变得有些僵硬,额角也渗出了细汗,显然压力巨大。整个病房的气氛凝固到了冰点。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僵持中,一个念头如同破开迷雾的闪电,猛地击中了我!签字!
林砚现在痛得连笔都拿不稳,更别说签字了。而我…虽然林砚的身体还很虚弱,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被动“休养”,手指似乎恢复了一点力气。最重要的是,
原主苏晚为了模仿林砚的签名以方便挪用资金,曾经下过苦功夫!她的模仿能力堪称一流,
林砚的签名,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那些记忆碎片此刻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脑中!机会!
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一个证明我并非完全废物的机会!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起来。
我艰难地、极其缓慢地移动着我那沉重得如同灌了铅的手臂。
每一次挪动都牵动着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带来剧烈的酸痛。汗水瞬间浸湿了我的鬓角。
我的动作极其细微,但在这死寂的病房里,衣料摩擦的声音还是引起了注意。
林砚和张凯的目光同时转向了我。林砚的眼神先是惊愕,随即是极度的警惕和怀疑,
像是在看一个试图破坏他计划的危险分子。张凯则是一脸茫然和不解,
不明白这位植物人状态的“林太太”想做什么。我没有理会他们。
所有的意志力都集中在右臂上。手臂像生锈的机械臂,一寸一寸,极其艰难地抬离了床面,
颤抖着,极其缓慢地…伸向张凯手中的那支笔。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我的指尖每一次颤抖的靠近,都如同跋涉千山万水。汗水流进眼睛,带来一阵刺痛。
肺部因为用力而火烧火燎。终于!我的指尖,颤抖着,碰到了那支冰冷的金属笔杆!
那一瞬间的触感,像电流般窜遍全身!虚弱感依旧存在,
但一股巨大的、源自灵魂深处的亢奋和决心支撑着我!我猛地用力,一把将笔攥在了手中!
虽然动作笨拙,但那握住的力道却异常坚定!“林太太?”张凯彻底懵了,下意识想抽回手,
却被我死死攥住了笔。林砚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也顾不得腹部的剧痛了,
厉声喝道:“苏晚!你想干什么?!放下!”属于我的声音因为惊怒而变调。我没有看他,
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张凯手中的那份文件上。
艰难地、一字一顿地从喉咙里挤出嘶哑破碎的音节:“协…议…给…我…”张凯完全傻眼了,
求助般地看向林砚。林砚脸色铁青,眼神像刀子一样刮着我,胸膛剧烈起伏。
他似乎在飞快地权衡利弊——是任由这个荒谬的情况发展下去,
还是冒着被助理看出更多破绽的风险强行阻止?最终,他死死地盯着我握着笔的手,
眼神变幻莫测,最终化为一片深沉的晦暗。他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字:“…给。
”张凯如蒙大赦,
又惊疑不定地将那份厚厚的协议小心地放到我勉强能触碰到的、盖着被子的腹部位置。
我深吸一口气,肺部传来撕裂般的痛楚。
回忆着脑中关于林砚签名的每一个细节——起笔的力道,转折的角度,
收尾的锋芒…模仿苏晚模仿林砚签名的记忆!手臂沉重如山,
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剧烈的颤抖。笔尖悬在纸页上方,不住地晃动。我闭上眼,
凝聚起残存的所有力气和对回家的最后一丝渺茫希望,猛地落下!笔尖划过纸张,
发出沙沙的声响。动作笨拙而缓慢,线条因为手臂的颤抖而显得不够流畅,甚至有些歪斜。
但我模仿着记忆中的轨迹,一笔一划,艰难无比地…完成了那个名字——林砚。
最后一笔落下,我整个人如同虚脱般瘫软下去,笔从汗湿的手中滑落,掉在被子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前阵阵发黑。张凯小心翼翼地拿起文件,
看着上面那个虽然有些虚浮颤抖、但结构和神韵都极其接近林砚平时签名的笔迹,
眼睛瞬间瞪得滚圆!他难以置信地看了看签名,又抬头看了看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我,
最后目光惊疑不定地转向旁边脸色铁青、眼神复杂到了极点的“林总”林砚。
林砚没有看张凯。他的目光,如同实质的探照灯,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那眼神里翻涌着太多情绪:震惊,难以置信,审视,警惕,一丝被冒犯的怒意,
甚至…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可能都未曾察觉的…异样光芒。他沉默了几秒,
那沉默如同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最终,他对着目瞪口呆的张凯,
用一种听不出喜怒的冰冷语调开口:“文件有效。去处理吧。”张凯如获大赦,
又敬畏地看了我一眼,拿着文件,几乎是逃也似地离开了病房。门关上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沉重的寂静再次降临。林砚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我的床边。
他俯视着我,目光锐利如鹰隼,仿佛要将我的灵魂彻底洞穿。
刚才的剧痛似乎被他强大的意志力强行压制了下去,但眉宇间的疲惫更深了。
“签名…哪里学的?”他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审慎和探究。
我累得连眼珠都不想转动,只是疲惫地看着天花板,
喉咙里发出微弱的气音:“…看…你签过…”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他沉默着,
眼神在我脸上来回逡巡,似乎在评估我话语的真实性,
又像是在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占据了林砚身体的“苏晚”。过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命令的口吻:“手…抬起来。”我困惑地看向他。“我说,手抬起来!
”他加重了语气,带着不容置疑。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极其艰难地将右手再次从被子里挪出来一点,颤抖着悬在床边。
他看着我那只虚弱颤抖、却刚刚完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签名的手,眼神变幻莫测。然后,
他做了一个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动作。
他伸出了手——那只属于苏晚的、纤细白皙的手——没有去握我的手,
而是…将自己那只手的手掌,悬在了我的手掌上方。掌心向下,
距离我的掌心只有不到一寸的距离。他在干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他垂下眼睑,
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遮住了他眼底翻涌的复杂情绪。
他似乎在全神贯注地感受着什么,感受着从我虚弱的掌心传递出的…某种无形的波动?
或者仅仅是感受着这荒谬绝伦的处境本身?时间在那一刻仿佛被拉长、凝固。
我们之间隔着一具冰冷的植物人躯壳和一具因疼痛而僵硬的女性身体,
隔着他母亲的血海深仇和我(苏晚)的累累罪孽,
隔着一场离奇的身体互换和两个被强行扭曲的命运…但此刻,两只手,一上一下,
悬停在冰冷的空气里,掌心之间那不足一寸的虚空,
却仿佛成了连接两个破碎灵魂的唯一通道。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两人细微的呼吸声。
窗外的阳光不知何时被云层彻底吞噬,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下来。
就在这死寂的、充满了无形张力的一刻——那消失了许久的、冰冷而毫无感情的电子音,
毫无预兆地、突兀地在我(或许也在他)的脑海深处炸响!
…】【错误日志分析中…】【冗余数据清理完毕…】【时空锚点重新校准…】【…校准成功。
】【世界线基础规则恢复。】【检测到异常灵魂绑定状态…】【…分析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