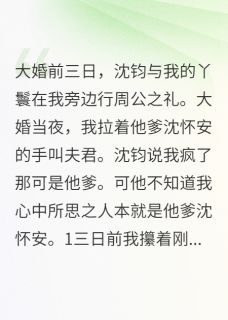大婚前三日,沈钧与我的丫鬟在我旁边行周公之礼。大婚当夜,
我拉着他爹沈怀安的手叫夫君。沈钧说我疯了那可是他爹。
可他不知道我心中所思之人本就是他爹沈怀安。1三日前我攥着刚裁好的嫁衣下摆,
屏风后传来衣料摩擦声时,我还以为是青黛来送冰湃酸梅汤,直到那声压抑的**刺破空气。
“你家**的嫁衣,真不如你身上这件红肚兜衬人。”沈钧的声音裹着情欲,
混着丫鬟急促的喘息在狭小的偏房里回荡。绣绷“啪嗒”坠地,我死死咬住下唇。
三日前他还跪在父亲灵前,握着我的手说此生唯我一人,
此刻却将我最信任的丫鬟抵在我日日刺绣的屏风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忽然笑出声。
笑声惊得屏风后骤然安静。青黛惨白的脸探出来时,我已经拾起绣绷,
指尖抚过那朵未完工的牡丹:“明日还要试妆,你们继续。”沈钧提着腰带冲出来,
脸上还带着未褪的潮红,我却对着他身后的老管家柔声道:“劳烦转告沈大人,
就说叶府嫡女三日后准时过门。”大婚前一日我修书一封到沈家,要沈怀安亲自来迎亲。
母亲攥着我的手腕,镯子硌得生疼:“哪有嫁儿子却让老子来迎亲的道理?你是着了什么魔!
”我并没有多作解释,勾起嘴角只说:“若沈怀安不来,这花轿我便死也不上。
”日头偏西时,沈府的管家踩着夕阳匆匆赶来。他手里的拜帖还带着体温,
语气却冷得像淬了冰:“我家老爷公务缠身,三书六礼皆已备齐,姑娘莫要坏了规矩。
”我捏着茶盏:“回去告诉沈大人,若想保住沈家体面,申时三刻前,他必须亲自来。
”管家的胡须抖了抖,转身离去。2和我料想的一样,沈怀安果然来了。
百姓挤在青石板两侧,窃窃私语声像夏日里的蚊蝇般嗡嗡作响。“不是说嫁世子吗?
怎么是侯爷亲自来迎亲?”“莫不是沈家弄错了?”错?我要的就是这举世皆惊的错。
拜堂的红毡已铺至眼前,司仪高亢的“一拜天地”刚出口,我突然抬手:“等一等。
”我从袖中抽出绿桃的有孕单子,
展开时故意让墨迹未干的“喜脉”二字对着满堂宾客:“不如今日三喜临门,沈府喜得金孙,
世子迎妾,侯爷娶妻。”“叶水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沈钧的怒吼震得烛火都晃了晃。
他涨红着脸冲过来,却在看到单子上的字迹时僵在原地。我转身走向沈怀安,
握住他微凉的手,指尖轻轻划过他掌心的薄茧。沈怀安猛地抽回手,
墨色蟒纹官袍扫过满地红烛,他眼底翻涌着震惊与慌乱:“叶姑娘休要胡说!
今日是你与钧儿的大喜之日!”我仰头望着他紧绷的下颌线,冷笑一声:“侯爷这话可笑,
您当真要我嫁一个与丫鬟苟且,还弄大人家肚子的浪荡子?”绣鞋踏前半步,
嫁衣的金线牡丹擦过他玄色衣摆,“绿桃腹中孽种已三月有余,沈府若是执意让我进这门,
明日全京城都会知道,你们沈家为了遮掩丑事,不惜让新妇吞下这口苦果。
”满室寂静得能听见落针之声。宾客们交头接耳的私语像潮水般涌来。
沈钧面色惨白如纸……而沈怀安盯着我,眼神晦暗不明,喉结滚动着,许久说不出话。
京城谁人不知,沈钧是大房过继给沈怀安的,而这位征战沙场的侯爷,早在西征时伤了根本,
此生再难有子嗣。如今,我这个叶家嫡女,不仅要将背叛我的丫鬟许给世子做妾,
更要当着全京城的面,逼沈家给我一个公道。我攥着那张薄薄的孕单,指尖微微发颤,
却努力维持着面上的镇定。这一刻,我等了太久。“叶水月!”沈钧赤红着双眼冲了过来,
他的锦袍凌乱,发髻歪斜,哪里还有半点世子的风范,“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爹!今天是你我的大婚!”他伸手便要抓我的手腕,我轻巧地侧身避开。
“沈钧,”我冷笑一声,“你还有脸提大婚?三日前,
你与我的丫鬟在偏房里行那腌臜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日?”我的话如同一把利刃,
瞬间刺破了婚堂的喧闹。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钧苍白如纸的脸上。
他踉跄了一下,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我转身面向沈怀安,他依旧站在原地,
神色冷峻。我深吸一口气,将孕单举到他面前:“侯爷,沈家世代清誉,
您当真要让这样的丑闻传出去?”我顿了顿,直视着他的眼睛,“与其让我嫁给这样的人,
不如侯爷给我一个公道。”沈怀安的目光扫过孕单,又落在我身上,沉默良久。
而沈钧在身后发出一声怒吼,却再没有勇气上前。一直端坐在太师椅上的沈老夫人缓缓起身,
我攥紧手中的孕单,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原以为要与沈府众人唇枪舌剑一番,
却不想老夫人接下来的举动让我瞳孔骤缩。
她布满皱纹的手突然握住我冰凉的指尖:“好好好!我早就想给怀安说门亲事了,
他非不同意。”老夫人浑浊的眼中泛起笑意,转头狠狠剜了沈怀安一眼,“这门亲事,
我同意了!”沈怀安身形一晃:“娘!你明知我……”话未说完,
沈老夫人手中的龙头拐杖重重杵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闭嘴!这侯府还有我说话的份!
”老夫人银丝晃动,威严的气场震得满堂宾客屏息,“当年西征伤了根本又如何?
难不成要看着你孤苦一辈子?”她的目光扫过面色惨白的沈钧,语气愈发冷硬。“祖母!
月儿她是我……”沈钧踉跄着上前,却被老夫人一声厉喝截断。“都不许说了!
”老夫人猛地转身,金丝绣鞋碾碎满地喜糖,“来人!去将侯爷的喜服取来!
今日就让怀安与叶姑娘拜堂成亲!”侍婢们慌慌张张奔去,沈怀安僵立原地,
喉结上下滚动却再发不出声音。3我望着沈怀安束着玉带的腰身,恍惚又回到五岁那年。
御花园的荷风裹着腥甜,十岁的少年将我从池水里捞起时,甲胄上的铜铃撞碎满池涟漪。
他把披风裹住我颤抖的肩膀,转身便将我塞给闻讯赶来的嬷嬷,连名字都未留下。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沈府三少爷沈怀安。每次宫宴,
我都隔着人群凝望他立在父亲身侧的背影。他比寻常贵公子多了几分冷峻,
腰间总悬着柄断了穗子的匕首。西征归来的沈怀安不再是记忆里鲜衣怒马的少年。
他总坐在书房批阅公文,苍白的面容上蒙着层霜,拒所有说亲的媒婆于千里之外。
我答应沈钧的求亲,不过是想着能嫁入沈家,就算只能隔着屏风听他说话,也算解了相思。
可命运竟如此眷顾。此刻老夫人的话还在耳畔回响,沈怀安的喜服已穿在身上,
那抹熟悉的玄色换成了喜庆的大红色,却依旧衬得他身姿挺拔如松。
沈钧在一旁嘶吼的声音渐渐模糊,我的目光死死钉在沈怀安紧绷的下颌线上,
多年来藏在心底的情愫翻涌如潮。“一拜天地……”司仪的声音响起。我屈膝行礼时,
指尖擦过沈怀安微凉的手背,那触感让我浑身一颤。原来真正站在他身边,
比我无数次的幻想都要令人心悸。三书六礼,凤冠霞帔,这场本该属于沈钧的婚礼,
终于成了我和他的。婚房里,沈怀安的影子被摇曳的火光扯得老长,
投在喜帐上像幅褪了色的水墨画。他的指尖反复摩挲着酒杯边缘,青瓷釉色被蹭得发暖,
却始终没抬头看我。“叶姑娘可知……”他的声音轻得像飘在烛烟里的灰,
尾音却被酒气浸得发涩,“我无法有子嗣,你嫁于我……”“京中谁人不知?”我打断他,
裙摆扫过满地喜字,在他对面缓缓落座。铜镜里映出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他眉间凝着霜雪,
我眼角沾着桃花。指尖按住他欲要斟酒的手,触到虎口处的剑茧,这双手曾握过银枪破敌,
此刻却在我掌下轻轻发颤。“沈怀安。”我故意唤他的字,看他睫毛剧烈颤动,
“我们已经拜堂,便是夫妻。”烛火突然爆了个灯花,将他眼底的暗潮照得分明。
他喉结滚动着,像有千言万语要冲出口,却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若你是赌气……”他突然抬头,却又迅速垂落,“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窗外夜风卷着落花扑在窗纸上,我望着他紧抿的唇线,忽然想起他西征归来那日,
他骑在赤雷马上,却未曾朝我的方向看上一眼。“夫君该喝合巹酒了。
”我端起那对并蒂莲纹的金杯,将他的酒盏斟得七分满。酒液晃出涟漪,映出两张交叠的脸。
他怔了怔,接过酒杯时指尖擦过我掌心,像片羽毛掠过心尖。“一仰而尽,岁岁同欢。
”我仰头饮下,辛辣的酒液滚过喉咙,却不及他指尖残留的温度灼热。他望着我泛红的眼角,
忽然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瓷杯重重磕在桌上,发出清越的响。红烛在此时轰然燃尽,
帐外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我抬手吹灭最后一盏烛火,黑暗瞬间漫过周身,
却遮不住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松烟墨香。“夫君,该歇了。”我的声音裹着夜色,
尾音在寂静中荡出暧昧的涟漪。榻上的软垫陷出细微声响,我知道他仍坐在原处。
指尖勾住寝衣系带,故意让丝绸滑落肩头:“夫君只是难有子嗣,难道那方面也不行?
”话音未落,便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月光从窗棂漏进来,
在他紧绷的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我翻身跪坐在床榻边缘,绣鞋蹭过他发凉的手背。
“沈怀安,”我俯下身时,青丝垂落拂过他发烫的耳垂,“我可不想和你做相敬如宾的夫妻。
”指尖顺着他喉结下滑,隔着衣料触到剧烈跳动的脉搏。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
力道大得几乎要碾碎骨头,却又在触及我手腕的瞬间松了几分。黑暗中,
他的气息喷在我唇畔:“叶水月,别玩火。”可他掌心的温度,分明比烛火更灼人。
我轻笑出声,将脸埋进他颈窝:“若这火能烧进你心里,我偏要把它燃得更旺些。
”4铜镜映出我唇角未褪的笑意,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颈侧那抹淡红痕迹。
春桃捧着胭脂盒候在一旁,见我对着镜中傻笑,忍不住好奇:“**,您在乐什么呢?
”我故意咬着帕子轻笑,昨夜沈怀安耳尖泛红的模样又浮现在眼前。谁说他不行?
分明是头蓄势待发的困兽,只不过被礼教枷锁缚住了爪牙。“没什么,想起些趣事。
”我接过玉梳,将如云青丝挽成新髻,“对了,侯爷呢?”“回**,侯爷寅时就去上朝了。
”春桃将鎏金步摇别进发间,簪头珍珠随着动作轻晃,“说是今日有紧要折子要奏。
”我对着铜镜调整耳坠位置,银铃轻响混着窗外鸟鸣。也是,
儿子的大婚陡然变成自己的喜事,满朝文武指不定怎么议论,他哪有时间告假。
想到沈怀安晨起时欲言又止的神情,我心底泛起丝丝甜意,起身往老夫人院中走去。
穿过九曲回廊时,晨露沾湿了绣鞋。刚迈进垂花门,便听见屋里传来冷嗤声。
沈钧生母……大房的吴氏斜倚在太师椅上,丹蔻染就的指尖叩着杯盏:“这成何体统?
好好的世子妃成了三弟的夫人,传出去让大房脸面往哪搁?钧儿可是过继给三弟的,
如今这般**闹剧,当我们大房没人了?”“放肆!”老夫人的龙头拐杖重重杵地,
震得檀木桌上的茶盏轻颤,“怀安是沈家的功臣!当年西征他九死一生,
伤了根本不能有子嗣,才让钧儿过继!如今钧儿做出这等丑事,大房还有脸来兴师问罪?
若不是怀安,沈家的爵位早没了!”我抬手理了理鬓边海棠,莲步轻移跨进门槛,
福身笑道:“儿媳给母亲、嫂嫂请安。”吴氏剜过来的眼神似淬了毒,我却恍若未觉,
接过春桃递来的茶盏:“这是今春的雨前龙井,特地给母亲尝尝。
”老夫人接过茶盏抿了一口,眼角笑意藏都藏不住:“还是月儿贴心,不像有些人,
整日就知道颠倒黑白。”吴氏脸色骤变,掐着帕子的手青筋暴起,
起身时锦缎裙摆扫落了桌上的茶点,却碍于老夫人威压不敢发作。老夫人转动着翡翠佛珠,
忽然轻叹一声:“钧儿呢?怎么还不来给母亲敬茶?”话音未落,雕花木门“吱呀”被撞开。
沈钧踉跄着冲进来,月白中衣外胡乱披着件墨色大氅,乌发散落肩头,眼下青黑如泼墨,
倒像是从阴曹地府爬出来的厉鬼。他的目光扫过满室众人,最后落在我身上时骤然瞪大,
喉间发出一声破碎的呜咽。我端起茶盏轻抿,任由滚烫的茶水熨烫舌尖。
金纹缠枝莲的杯沿映出沈钧颤抖的指尖……那双手,三日前还在撕扯丫鬟的衣襟。“母亲,
”我将茶盏搁在案上,声音甜得发腻,“您看,钧儿这是特意来给我奉茶了?
”沈钧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踉跄着要退出去。
老夫人的龙头拐杖“咚”地砸在青砖上:“站住!你昨夜去哪鬼混了?还不快给你母亲敬茶!
”吴姨娘在旁冷笑出声,帕子掩着唇角:“可不是该好好认认,这以后就是你嫡母了。
”沈钧僵在原地,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起身走到他面前,指尖挑起他下颌,
凑近轻声道:“好儿子,莫要让祖母失望。”他浑身剧烈颤抖,突然“噗通”跪在我面前,
瓷杯里的茶水泼在我裙裾上,洇开深色的痕,倒像是谁落下的泪。
滚烫的茶水顺着茜色裙摆蜿蜒而上,在金线牡丹间晕开深色的污渍,
恰似沈钧此刻破碎的尊严。他喉间滚动着不成句的呜咽,额头重重磕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
“这是做什么!”老夫人的声音带着怒意,“还不速速给你嫡母奉茶!
”沈钧颤抖着拾起散落的茶盏,茶汤在杯中晃出细碎的涟漪。他抬头望向我时,
眼底布满血丝,嘴角溢出一声带着哭腔的冷笑:“好……好一个嫡母……”话音未落,
突然扬手将茶水朝我泼来。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玄色身影闪过。沈怀安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他长臂一揽将我护在身后,飞溅的茶汤尽数泼在他的朝服上。屋内顿时一片死寂,
唯有他急促的呼吸声,温热地喷洒在我的发顶。“钧儿!”沈怀安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
“你疯了不成!”沈钧却似彻底癫狂,他跌坐在地,指着我们大笑起来:“我疯?
你们才是疯了!父亲抢儿子的妻子,这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他猩红的目光扫过吴姨娘煞白的脸,突然转向老夫人,“祖母,您口口声声说为了沈家,
可这桩婚事传出去,沈家才是真正的笑话!”老夫人的拐杖重重杵地,
震得满室噤声:“住口!月儿如今是你嫡母,从今日起,你便好好尽孝道!
”沈怀安松开我的瞬间,我趁机挽住他沾着茶渍的手臂,
指尖轻轻擦过他掌心的薄茧:“侯爷的朝服脏了,不如让妾身回房为您更衣?
”我抬眸望向他,在他骤然收紧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得逞的笑意。沈钧的嘶吼声渐渐远去,
我倚着沈怀安的臂膀缓步离开,身后传来吴氏压抑的啜泣。5朱红门扉在身后合拢的刹那,
沈怀安便后退半步与我拉开距离,玄色朝服上未干的茶渍在晨光里泛着冷灰。
他抬手欲解玉带,喉结滚动着吐出句“我自己来”,却被我抢在前面按住冰凉的玉扣。
“侯爷战场上杀敌的手,怎好做这些琐事?”我歪头轻笑,指尖故意擦过他腰间皮肤,
见他骤然绷紧的腹肌在月白中衣下起伏,“昨夜都不嫌我手笨,今日倒生分了?
”他僵在原地,任由我慢条斯理解开盘扣。窗外的晨阳斜斜切进屋内,
将我们交叠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像幅未完成的工笔画。当最后一颗纽扣滑落在地,
我佯装不稳跌进他怀里,青丝扫过他胸前狰狞的箭伤疤痕,西征时留下的印记,
此刻却随着他剧烈的心跳微微发烫。“当心。”他本能地环住我的腰,掌心的温度穿透薄绸。
我仰脸望着他绷紧的下颌线,指尖抚过他凸起的喉结:“侯爷在朝堂上威风八面,
怎么抱自家娘子时这般僵硬?”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却在触及肌肤时又松了力道。
呼吸扫过我泛红的耳垂,带着晨露般的凉意:“叶水月,莫要胡闹……”话音未落,
我已扯落他束发的玉冠,墨色长发倾泻而下,在晨光里流淌成缎。绣鞋勾住他的靴筒,
我将他往榻边带了半步,红唇擦过他紧绷的唇角:“若侯爷觉得我是胡闹,
”目光扫过他眼底翻涌的暗潮,“昨夜又何必应下这婚事?”雕花床榻发出细微的吱呀声,
帐幔在晨风中轻拂,将一室旖旎笼进朦胧的光晕里。春桃第三次叩门时,我歪在沈怀安怀里,
指尖缠着他散落在枕畔的长发,听着外头传来怯生生的“侯爷、夫人,早膳备好了”,
故意抬高声音:“回了吧,侯爷乏累,不便起身。”话音未落,
腰间便被沈怀安重重掐了一把。日头西斜时我们才踏出房门。沈怀安走在前面,
玄色锦袍下摆扫过青石板,背影却比晨起上朝时佝偻几分。我踩着他的影子亦步亦趋,
故意让新换的珠翠发钗在他耳畔叮咚作响。膳厅里早坐满了人。吴氏捏着帕子冷笑一声,
胭脂抹得浓重的脸在烛光下泛着青白:“某些人倒真是会勾人,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我倒觉得奇怪。”我伸手按住沈怀安要起身的动作,
指尖顺着他手背滑进掌心,“新婚燕尔不勾引自家夫君,难道去勾引旁人不成?
”说着夹起一块芙蓉糕,仰头轻晃他的手腕,“侯爷,您尝尝?”沈怀安耳尖红得滴血,
却顺从地咬下糕点。他喉结滚动的声响在寂静的膳厅格外清晰,
惊得吴氏手中的茶盏当啷坠地。“好个不知廉耻的狐媚子!哪有半点世家**的模样,
倒像那勾栏里的……”“够了!”老夫人的龙头拐杖重重砸在青砖上,震得满桌碗碟轻颤。
我趁机往沈怀安怀里缩了缩,指尖偷偷勾住他腰间软带。沈怀安骤然起身,
宽大的袖袍扫翻案上瓷碗。他稳稳扶住我,声音冷得像淬了冰:“母亲,
往后我与夫人就在自己院中用膳。”转身时他的手指穿过我的指缝,
掌心的汗意混着未散的松香,烫得人心尖发颤。跨过门槛的刹那,我回头望向吴氏铁青的脸。
沈怀安离去的脚步声渐远,书房铜锁扣上的声响顺着穿堂风飘来。
我对着菱花镜慢条斯理地拆着发间珠翠,春桃跪坐在软垫上替我卸甲,
嘴里还絮絮叨叨:“那大房的娘子怕是怕夫人影响她的地位,世子虽要称您一声母亲,
但毕竟世子可是她亲生的……”铜镜映出我勾起的唇角,指尖捏着鎏金步摇轻轻晃了晃,
珠玉相撞发出清脆声响。“她的地位?”我轻笑出声,将步摇搁在妆奁里,“这侯府的天,
终究是侯爷说了算。”窗外暮色渐浓,檐角铜铃在风中叮咚作响。我望着廊下摇曳的灯笼,
想起沈怀安耳尖的绯红,还有他转身时下意识握紧我的手。大房的算计、吴氏的嫉恨,
在我眼里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春桃,”我起身披上鹤氅,望着西沉的夕阳,
“去备些醒酒汤,等侯爷从书房出来。”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的缠枝莲纹,
心底泛起丝丝甜意。我既已嫁入侯府,得了心心念念的人,旁的虚名浮利,又何须在意?
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而真正要紧的,是如何让沈怀安那颗冷硬的心,彻底为我沦陷。
6夜已深,沈怀安书房的烛火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投在半掩的门上。我端着醒酒汤踏入时,
他正将最后一页文书放下,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堂堂叶府嫡**,”他忽然开口,
声音裹着夜色,“哪里学的这些勾人手段?”我将汤盏轻轻搁在案上,
烛光在他棱角分明的面容上跳跃,映得那双深邃的眸子愈发幽暗。指尖划过他手背,
故意带着几分慵懒:“我勾的可不是寻常人,是侯爷您啊。”见他耳尖微微发红,
又凑近几分,“若不是侯爷,这些手段,旁人可没福消受。”他喉结滚动,别开脸不再看我,
端起汤盏一饮而尽,却烫得微微皱眉。我忍不住轻笑出声,伸手替他擦拭嘴角,
他下意识要躲开,却被我握住手腕:“侯爷这般生分,可不像昨夜的模样。”第二日清晨,
我在花园赏着新开的芍药,忽听得假山后传来细碎的抽噎声。绕过太湖石,
便见绿桃跪在地上,孕肚已微微隆起,见我瞬间脸色惨白,拼命磕头:“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我还未开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沈钧不知从哪冲了出来,
挡在绿桃身前,眼神满是戒备与恨意:“叶水月,你又想做什么?!
”沈钧几乎是将绿桃整个人拽进怀里,骨节泛白的手死死扣住她颤抖的肩膀。
孕肚在藕荷色襦裙下显出柔和的弧度,却在他暴起的青筋下显得格外脆弱:“叶水月,
你敢动她……”“真是败了兴致。”我垂眸掐断指尖缠绕的蔷薇花枝,
碎刺扎进掌心也浑然不觉。沾着晨露的花瓣簌簌落在沈钧绣着金线的鞋面上,
倒像是撒了满地的嘲讽。不等他把话说完,我已提着裙摆绕过他们,
绣鞋碾过青石板的声响清脆如裂冰。春桃小跑着跟上,
发间银铃撞出慌乱的节奏:“这世子怕不是眼瞎,连……”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回头时正见她盯着我渗血的掌心,脸色发白。“无妨。”我用帕子随意裹住伤口,
望着远处沈怀安书房的飞檐,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蔷薇的甜香混着血腥气漫进鼻腔,
忽然觉得这满园春色都不如昨夜那人耳尖的红来得鲜活。雕花楼船缓缓划过护城河,
沈怀安亲手为我披上貂裘的温度还残留在肩头。他命人抬进叶家的十里红妆晃得人睁不开眼,
连管家看我的眼神都带了几分敬畏。母亲握着我的手,指尖在我腕间的翡翠镯子上摩挲。
镯子是昨晚沈怀安亲手为我戴上的。
“那日你非要怀安亲自来迎亲……”母亲的声音突然压低,绣着并蒂莲的帕子擦过眼角,
“是不是早有算计?娘早该想到,你从小就倔,认定的事哪有回头的道理。
”我将鱼食撒进池塘,锦鲤翻涌着争抢,搅碎了水面上的倒影。“母亲……这样甚好。
”风掀起珠帘,远处传来沈怀安与父亲交谈的声音,沉稳的声线让我不自觉地弯起唇角。
母亲望着我的神色,突然叹了口气:“只要你过得好……”她的话被一声脆响打断,
我失手将青瓷鱼食罐摔在青石上,碎片溅起的水花落在裙摆。望着满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