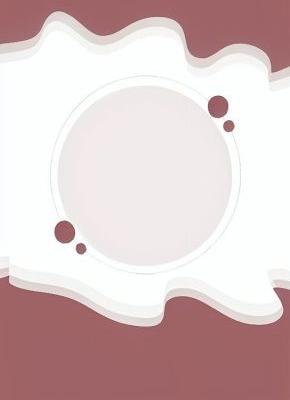傅聿川养了我三年,也透过我的眼睛看了另一个人三年。他未婚妻回国那天,
我攥着诊断单安静离开。三个月后,他却疯了一样砸开我的门:“学她学上瘾了?
连消失都要复制?”我望着他轻笑:“傅先生,你认错人了。”“从始至终,
我都在做我自己。”---墓园的风裹着深秋的凉,吹得人骨头缝都发冷。
林浅站在一块干净得过分的墓碑前,照片上的女人温婉笑着,眉眼间能看出与她有三分相似。
三分,足够了,足够成为一场荒唐交易的入场券。她拢了拢身上不算厚实的大衣,指尖冰凉。
三天前,傅聿川的白月光苏晚正式回国,傅家为她办的接风宴冠盖云集,
消息甚至不需要刻意打听,就自动钻进她这个被金屋藏娇的“赝品”耳中。也是在那天,
她确认了自己身体里的变化。一张轻飘飘的纸,重逾千斤。身后传来熟悉的汽车引擎声,
平稳地停在远处。傅聿川来了,他总会在这个日子来这里,雷打不动。林浅没有回头,
依旧静静地看着墓碑上的女人。三年,一千多个日夜,她扮演着傅聿川需要的影子,
揣摩苏晚的神态,模仿苏晚的喜好,连微笑的弧度都经过精确计算。傅聿川透过她的眼睛,
在看另一个人。她以前会偷偷看他,在他失神凝望她,却又分明不是在看她的时候,
心里某个角落会细细密密地疼。后来,那点不该有的妄念,被她自己亲手掐灭了。
脚步声停在身侧,带着他身上惯有的冷冽木质香。“来了。”他开口,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平淡,听不出情绪。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一瞬,像是在确认妆容是否完美,
神态是否够像。“嗯。”林浅低低应了一声,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次一样温顺。
她没问他苏晚回国的事,没问自己这个替身何时谢幕,
更没提口袋里那张揉得有些发皱的诊断单。有些界限,逾越了就是自取其辱。祭奠结束,
傅聿川率先转身走向车子,似乎笃定她会跟上。林浅却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挺拔,
冷漠,带着天生的疏离感。“聿川。”她轻轻喊了一声,不是平时刻意模仿苏晚的柔软音调,
是她自己的声音,清灵灵的。傅聿川脚步一顿,有些意外地回头。这称呼,她很少用。
“我想去城南那家甜品店买栗子糕。”林浅弯起眼睛,
露出一个苏晚式的、毫无攻击性的甜美笑容。那是苏晚最爱吃的,
也是“她”该在祭奠后提出的,一个合乎身份的小小要求。傅聿川眼底那一丝讶异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应如此”的淡漠。“让司机送你去。”他拉开车门,坐了進去。
黑色宾利无声地滑走,消失在墓园蜿蜒的车道尽头。林浅看着车子彻底不见,
脸上完美的笑容一点点褪去,最后只剩一片平静的苍白。她没有等司机,
径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回到那套住了三年的公寓,这里的一切都带着苏晚的痕迹,
从窗帘的颜色到沙发的款式,都是傅聿川按照苏晚的喜好布置的。她像个暂住的幽灵,
活在一个别人的壳子里。她的东西少得可怜,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所有属于“林浅”的痕迹。
她最后环视一圈这个精致冰冷的牢笼,将钥匙放在玄关的柜子上,轻轻带上了门。没有告别,
没有留恋。---三个月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
傅聿川的生活似乎并未因林浅的离开而产生任何涟漪。他按部就班地工作,应酬,
陪着苏晚出席各种场合。苏晚就应该是站在他身边的女人,优雅,得体,家世相当。
只是偶尔,在某个瞬间,他会下意识地看向身侧,那里空着,或者站着的是苏晚,
而不是那个总是微微低着头,小心翼翼模仿着一切的影子。他开始做同一个梦,
梦里总是林浅最后在墓园回头看他那一眼,平静无波,却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头,不疼,
却无法忽视。起初,他以为那点不适只是不习惯。习惯了她恰到好处的沉默,
习惯了她泡的温度正好的茶,习惯了她那双与苏晚相似的眼睛里,
偶尔流露出的、属于她自己的,怯生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直到他在苏晚身上闻到一款陌生的香水味,看到她用一个完全不像她风格的发夹,
听她说起在国外时一些独立张扬的往事片段……他才恍惚意识到,他记忆里的苏晚,
似乎一直是停留在几年前的那个模板。而林浅模仿的,也是那个过去的苏晚。
真正的苏晚已经在时光里改变了,只有林浅,在原地,固执地、精确地维持着那个“标准”。
一种莫名的焦躁感攫住了他。他派人去查林浅的去向。回报的消息很简单,
她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动用他给的任何一张卡,没有联系任何已知的朋友,
消失得干干净净。这种感觉,让他心烦意乱。
尤其是当他无意间在书房一个不起眼的抽屉角落里,发现一枚不属于苏晚,也不属于他的,
一枚很普通的银色细圈戒指时,那种烦躁达到了顶点。他记起来,林浅刚来的时候,
手上好像戴着这个,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他捏着那枚冰冷的戒指,
脑海里猛地炸开一个念头——她连离开的方式,都在模仿苏晚当年赌气出国吗?一种被冒犯,
被算计的怒火,混合着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恐慌,让他彻底失了控。“查!
给我掘地三尺把她找出来!”他砸了书房里一个明代的青花瓷瓶,胸口剧烈起伏。
下属战战兢兢,从未见过先生如此失态。当最终地址放在他桌上时,
傅聿川几乎是立刻抓起车钥匙冲了出去。---城北的老旧小区,
楼道里弥漫着淡淡的油烟和潮湿的气味。傅聿川用力拍打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手背青筋暴起。“林浅!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门内安静了片刻,然后,
锁舌“咔哒”一声响动。门开了。林浅站在门后,穿着简单的棉质长裙,
外面套了件宽松的针织开衫,小腹已经有了明显的隆起弧度。她的脸比之前圆润了些,
气色却很好,那双总是努力模仿着苏晚温顺垂下的眼睛,此刻清亮亮地看着他,
里面没有任何他预想的惊慌、愧疚或者讨好。平静得像一泓深秋的湖。
傅聿川所有的质问和怒火,在看到她那双眼睛和隆起的腹部时,猛地噎在了喉咙里。
他瞳孔骤缩,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短暂的死寂后,
他像是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着一种被欺骗和巨大荒谬感催生出的暴怒,
他一把挥开挡在门边的旧椅子,椅子砸在墙上发出刺耳的声响。“学她学上瘾了是吗?!
”他盯着她,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冰碴,“连玩消失这一套,
你都要原封不动地复制?!”林浅静静地听着,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波澜。等他吼完,
楼道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时,她才微微歪了歪头,唇边勾起一抹极淡的,
却清晰无比的弧度。那笑容,傅聿川从未在她脸上见过。不像苏晚,谁也不像,
只属于眼前的林浅。她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傅先生。”三个字,
疏离得像隔着千山万水。“你认错人了。”傅聿川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凝固。
他看着她的眼睛,听见她用一种平静得近乎残忍的语气,缓缓说道:“从始至终,
让你看着的人,让你透过我的眼睛想着的人,都是你心里的那个影子。”“而我,”她抬手,
轻轻放在自己隆起的小腹上,这是一个充满保护意味的,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动作,
“只是在扮演你付费点播的角色。”“现在,戏散场了。”她看着他骤然失血的脸色,
看着他眼中翻涌的震惊、混乱,以及那几乎要破土而出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
名为“失去”的恐慌。林浅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也真的就笑了出来,
那笑容冲淡了她眉宇间最后的阴霾,变得生动而明亮。她轻轻侧身,让开一点空间,
足以让他看清身后小客厅里简单却温馨的布置,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
在午后的阳光下舒展着枝叶。然后,她迎上他混乱不堪的视线,一字一句,
清晰地说道:“从始至终,我都在做我自己。只是你,傅聿川,你从来没想过要看清而已。
”傅聿川像是被这句话钉在了原地。他看着她平静的眉眼,看着她护住小腹的手,
看着她身后那个洒满阳光的小客厅——和他为她打造的精致牢笼截然不同,
这里充满了生活气息,是她自己的选择。“你自己?”他重复着这三个字,声音嘶哑得厉害,
“这三年……都是假的?”林浅轻轻摇头,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怜悯的透彻。
“对你来说是假的,对我而言只是一份工作。”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些,
“一份需要付出感情来表演的工作。
”傅聿川猛地想起无数个细节——她泡茶时微微颤抖的手指,
她在他失神凝望时悄悄垂下的睫毛,
她偶尔在他提及苏晚时那一闪而过的、被他误读为羞涩的黯然。原来那不是模仿,
那是她在努力压抑属于林浅的真实反应。“那份诊断单……”他艰难地开口。“扔了。
”林浅打断他,“在离开的当天就扔了。傅先生,我不需要用它来证明什么,或者换取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他紧握的拳头上,那里还捏着那枚被他当成罪证的银色戒指。“至于这个,
”她笑了笑,“它从来就不属于苏晚。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刚到你身边时,
你说它太廉价,配不上‘她’的身份,让我摘了。”傅聿川的手指猛地收紧,
戒指的边缘硌得他掌心生疼。他记得。他记得当时轻描淡写地说过这句话,
记得她默默取下戒指时低垂的眉眼。他以为那只是赝品对正品的顺从,
却从未想过那是在剥夺属于林浅的、为数不多的真实。楼道里的穿堂风带着寒意,
吹散了他来时满腔的怒火,只剩下无处遁形的狼狈。“孩子……”他几乎是本能地问出口。
林浅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那是一种母兽护崽般的警惕。“我的。”她斩钉截铁,“与你,
与傅家,与这场交易,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像最后一记重锤,
砸碎了他所有试图重建掌控感的可能。他意识到,她不是在赌气,不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她是真的,彻底地,要从他的世界里剥离出去。“如果傅先生没有其他事,
”林浅往后退了半步,手扶在门框上,是个准备送客的姿态,“我这里地方小,
容不下您这尊大佛。而且,”她抬眼,目光清凌凌地落在他脸上,
“苏**要是知道您来找我,怕是不太合适。”她甚至体贴地为他,也为她自己,
划清了最后的界限。傅聿川喉结滚动,想说什么,却发现所有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质问?他以什么立场?补偿?她明确表示不需要。挽留?他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仿佛要将这个陌生的、真实的林浅刻进眼里。
然后,他转身,一步一步走下昏暗的楼梯,背影竟带着几分从未有过的踉跄。
林浅静静地关上门,锁好。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她缓缓吐出一口气,
一直紧绷的肩膀终于松懈下来。手心,其实早已被指甲掐出了深深的印子。她走到窗边,
轻轻撩开素色的窗帘一角,看着那辆熟悉的黑色宾利在楼下停留了许久,最终才缓缓驶离,
消失在城市的车流里。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觉得,一直压在心头的那块巨石,
好像终于被挪开了。虽然留下了一个深坑,但阳光,总算能照进来了。---几个月后,
城北一家新开的独立书店。林浅穿着舒适的孕妇裙,正在整理书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行动有些不便,但脸上总是带着平和宁静的光晕。书店是她用这几年偷偷攒下的钱盘下的,
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她不再需要模仿任何人,只需要做她自己。风铃轻响,
有客人推门而入。林浅抱着几本书回头,笑容在触及门口那道身影时,微微一顿。
傅聿川站在门口,没有像上次那样带着一身戾气。他穿着简单的深色大衣,
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目光落在她隆起的腹部上,复杂难辨。他走到柜台前,
将纸袋轻轻放在台上。“城南那家店的栗子糕,”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我记得……你爱吃。”林浅看着那熟悉的包装盒,
忽然想起墓园外她最后一次以“替身”身份提出的要求。原来他记得,只是当时,
他以为那是“苏晚”爱吃。她轻轻摇头,将纸袋推了回去,语气温和却疏离:“谢谢傅先生,
不过你记错了。爱吃栗子糕的不是我,是苏**。我其实,”她顿了顿,坦诚道,
“对栗子过敏。”傅聿川的手僵在半空,脸色一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又一个他认错的细节,
又一记无声的耳光。他看着眼前这个眉目沉静、气质温婉却透着坚韧的女人,
终于清晰地认识到——他弄丢的,从来不是苏晚的替代品。而是一个鲜活的、独特的,
名叫林浅的女人。“我……”他想说点什么。“傅先生,”林浅打断他,目光清澈见底,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很好。”她指了指这个小小的书店,
脸上露出一个真实而满足的微笑:“这才是我的生活。”傅聿川看着她眼底的光芒,
那是他在那套公寓里从未见过的光彩。他所有未曾说出口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他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像是要把这个真正属于林浅的笑容记住。然后,
他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林浅看着他消失在门口,低头,轻轻抚摸着肚子,
感受着里面小生命有力的胎动。窗外,阳光正好。她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光荏苒,
转眼已是三年后。“浅语书店”已然成为城北小有名气的一处温馨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