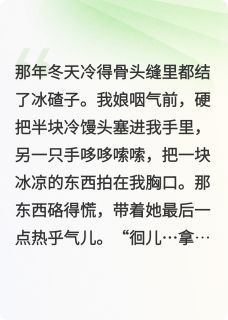那年冬天冷得骨头缝里都结了冰碴子。我娘咽气前,硬把半块冷馒头塞进我手里,
另一只手哆哆嗦嗦,把一块冰凉的东西拍在我胸口。那东西硌得慌,
带着她最后一点热乎气儿。“徊儿…拿着…你爹的…”她喉咙里像塞了把破风箱,
呼哧呼哧响了几声,眼里的光“噗”一下,灭了。那年我八岁,手里的馒头冻得跟石头似的,
牙印子刻在上面,像刻在心上。啃馒头?不,从那天起,我啃的就是恨,一口一口,
又冷又硬,磨得嗓子眼冒血。新朝姓赵,开国的皇帝叫赵隼。我爹那颗脑袋,
就是被他亲手砍下来,挂在高高的城门楼上,像挂一块烂腊肉,风干了整整三天。
我那时个儿矮,挤在人群里,踮着脚才看得清。脖子被北风吹得凉飕飕的,
心里却像塞满了烧红的炭火,烫得五脏六腑都在冒烟。那火烧了整整十二年,
烧得我把自己名字都改了,从“燕回”到“燕徊”。回?回不去了,只能像条丧家狗,
在暗地里徘徊。潜伏这事儿,说白了就是装孙子。我混进新朝的都城,
在街角一家破茶馆里支了个摊子,给人说书混口饭吃。专捡前朝那些风光旧事讲,
讲得唾沫横飞,底下听书的老头老太丢下几个铜板,唏嘘两声“作孽哟”,也就散了。
铜板叮当响,我耳朵竖着,听他们闲磕牙,一点点把赵家那点龌龊底细摸了个门儿清。
赵家如今风头最盛的,是安阳郡主赵明锦。赵隼的亲侄女,十六岁就敢提刀上阵砍人,
二十岁封了郡主,手里攥着北境三十万大军的虎符。茶馆里唾沫横飞:“啧啧,那郡主,
青面獠牙!一顿能吃三个小孩儿!”我低头抠着桌角掉漆的木屑,心里直翻白眼:扯淡吧,
又不是庙里的夜叉。我给自己描画了一张皮:温润如玉的谋士,手无缚鸡之力,
但一肚子“坏水”,专出阴损的主意。这名声像长了腿,在城里跑得飞快。三个月后,
一张烫金的帖子递到了我住的破瓦房里头。落款是安阳郡主府,说是请我去“喝茶”。
捏着那张硬邦邦的纸,我嘴角咧开,后槽牙都跟着隐隐作痛——鱼,
到底还是闻着腥味儿上钩了。头一回踏进郡主府那道高高的门槛,
我特意换了身簇新的月白长衫,头发用一根素玉簪子别得一丝不乱。袖子里揣了把白纸扇,
扇骨上“清风徐来”四个小字,是我自己用刻刀一点点抠出来的,
为的就是显得肚子里有点墨水。她被引到府里一处临水的凉亭。亭子里,赵明锦背对着我,
一身绛红色的窄袖骑装,头发只用根红绳高高束起,手里正忙活着。不是批公文,
也不是擦宝剑——她在削苹果。一把薄薄的小刀在她指间翻飞,灵活得像是活物。
苹果皮被旋成一条连绵不断、均匀得吓人的红带子,垂下来,愣是没断。刀刃反射着日光,
晃得我眼皮直跳,心里头飞快地盘算着:这玩意儿要是削在脖子上,得有多利索?
“你就是那个会讲故事的燕先生?”她冷不丁地转过身。那声音清亮,
带着点刚睡醒的懒洋洋,眼睛却像河面反射的阳光,亮得有点扎人。我赶紧拱手,
腰弯得恰到好处,声音压得又低又柔和:“正是在下。”她没客套,
“咔嚓”就是一大口咬下去,苹果的汁水顺着她线条清晰的下巴往下淌。她随手用手背一抹,
动作利落得像个老兵痞子:“听说你嘴皮子利索,主意也多。给我出个主意。北边那些蛮子,
最近皮又痒痒了。我想让他们安生,但又懒得动刀兵,费钱费人。咋整?
”这题我熟得不能再熟。前朝怎么没的?不就是被这帮蛮子闹腾得焦头烂额,我爹带兵去打,
结果……我清了清嗓子,把心头那点翻腾的恨意往下压了压,开口:“蛮子缺盐缺茶,
日子过得苦哈哈。郡主不如以商制夷,开互市,用盐茶布匹,换他们的马匹牛羊。
先稳住他们两年。这两年里头,咱们在北境加紧屯田,粮草自给自足了,他们再想闹腾,
也蹦跶不起来了。”话说完,我垂着眼,等着她的反应。凉亭里安静了一瞬,
只有风穿过竹叶的沙沙声。再抬头,正对上她眯起的眼睛。
那把削苹果的小刀在她掌心里轻巧地转了个圈,寒光一闪。“啧,
”她唇角勾起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你这法子嘛……”她拖长了调子,
我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我半个月前刚写完折子,递上去啦。”轰的一声,
我感觉脑子像是被谁拿大锤子砸了一下,嗡嗡作响。完了!撞枪口上了!
这郡主根本不是个草包!冷汗瞬间浸透了里衣。我慌忙补救,腰弯得更低了:“郡主英明!
是在下……拾人牙慧了,惭愧,惭愧!”她没接话,反倒“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笑声清脆,带着点恶作剧得逞的得意。她扬手,把啃得光溜溜的苹果核朝我怀里一扔,
准头奇佳。我下意识接住,那果核还带着点湿漉漉的凉意。“拾得好!”她拍拍手,
像丢掉了什么麻烦,“明儿个就来府里报到,当个幕僚。月钱十两,管饭。”十两!
够我买二十个冷馒头了!我赶紧低下头作揖,嘴角拼命往下压,
生怕那点压不住的狂喜泄露出来——成了!计划通!进府第一天,
我琢磨着得把“病秧子”人设立稳了。起了个大早,
在屋里对着窗户纸“咳咳咳”猛咳了三声,声音凄惨得连自己都信了。出门时扶着墙根,
一步三喘,弱柳扶风似的。刚蹭到院子里,就听见一阵沉闷的“砰砰”声,震得地面都在抖。
抬眼一看,好家伙!赵明锦就在院子当间儿,一身利落的短打,
正对着一个半人高的沉重沙袋练拳。那拳头砸下去,沙袋像个挨揍的胖子,
痛苦地大幅度晃荡着。她额头上一层薄汗,脸颊红扑扑的,一回头瞧见我,眼睛一亮,
冲我招手:“哟,燕先生起得挺早啊!来来来,活动活动筋骨,比划比划?
”我看着她那砂锅大的拳头,再看看自己这细胳膊细腿,咳得更加情真意切,
郡主……咳咳咳……在下……体弱……怕是……一拳过去……就得见祖宗了……”她撇撇嘴,
明显有点扫兴:“啧,真不禁造。那行吧,帮**点轻省活儿。库房昨儿进了三百石军粮,
你给算算,够咱北境那三十万张嘴嚼巴几天?”“是,郡主。”我如蒙大赦,赶紧溜到账房。
算盘珠子被我扒拉得噼啪作响,快得几乎要冒出火星子。
三百石军粮……三十万大军……我心里头飞快地拨着算盘,越拨心越凉,
指尖都冻得发麻——撑死了五天!五天之后,就得喝西北风!这郡主,精得跟猴儿似的,
糊弄她?门儿都没有!看来“病秧子”这招不顶用,得换个路子走。
“知心哥哥”路线就此上线。她半夜顶着寒风巡营回来,脸冻得发青。我掐着点儿,
端着一碗滚烫的、冒着浓烈姜味的汤,像个门神似的蹲在她卧房门口。“郡主,巡营辛苦,
喝口热乎的,驱驱寒。”她瞅了我一眼,大概是累狠了,没废话,接过去仰脖就灌。
“咕咚咕咚”几大口下去,碗底空了。她被那姜味冲得直皱眉,
龇牙咧嘴地吐着舌头:“嘶——燕徊!你这汤里放的是姜,还是姜祖宗?想辣死我啊!
”我早有准备,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打开是几颗蜜饯果子,
递过去:“郡主息怒,压压。”她拈起一颗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囊囊地嚼着,
含糊不清地嘟囔:“算你还有点良心。”就这么一来二去,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
我俩混熟了。她练拳练得满头大汗,我适时递上温热的毛巾;她熬夜批军报熬得两眼通红,
我就在旁边掌灯添茶;她对着办事不利索的下属拍桌子骂娘,
我就默默递上一杯温度刚好的水——顺便摸出怀里那个小本本,飞快地记下她的“金句”。
什么“脑子让门挤了?”、“眼睛长在**上了?”、“这点事儿都办不利索,
回家抱孩子去吧!”……打算以后写进史书里,标题都想好了,《安阳郡主骂人实录》。
有次她骂完人,口干舌燥地灌水,一扭头正好瞥见我低头猛写。她好奇地凑过来,
一把抢过那小本本。看了两眼,她先是愣住,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笑得直拍桌子,
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燕徊!燕徊!你活腻歪了是吧?啊?记这玩意儿干嘛?
想等我死了刻碑上?”我吓得缩着脖子,像只受惊的鹌鹑,
小声辩解:“为……为郡主立传……留待后世评说……死……死也光荣……”她止住笑,
伸出一根手指,带着常年握刀磨出的硬茧,不轻不重地戳在我脑门儿上,戳得生疼。“立传?
”她哼笑一声,“我看你是想气死我,好继承我的虎符吧?”指尖的粗糙感留在皮肤上,
有点疼,又有点痒,我耳朵根子莫名其妙地发起烧来,烫得厉害。
真正让我差点魂飞魄散的事儿,发生在冬至那天。府里热热闹闹包饺子,
我混在人群里帮忙剁馅儿。大概是她那句“立传”戳得我心神不宁,刀一偏,剁在案板边上,
力道震得怀里那硬邦邦的东西一滑——叮当一声脆响!
那块我娘给的、随身藏了十几年的破玉佩,不偏不倚,掉在了赵明锦脚边。时间像是冻住了。
剁馅儿的、擀皮的、说笑的,全都停了。空气凝固得能拧出水来。赵明锦弯腰,动作不快,
甚至有点慢悠悠地,把那块玉佩捡了起来。她没看我,只是捏着那玉佩,
对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仔细地看。光线穿过玉佩,
清晰地映出背面那繁复而独特的龙纹——前朝皇室的身份象征,像一道烧红的烙铁,
烫得我瞳孔猛地一缩。完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手里那把沉重的剁骨刀差点脱手砸在脚背上。她终于抬起头,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脸上,
脸上那点包饺子的笑意消失得干干净净,声音像结了冰:“解释。
”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几乎是凭着本能,“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油腻腻的地面上,
膝盖砸得生疼。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脑子在极度的惊恐下反而转得飞快,
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像气泡一样往外冒,带着哭腔,情真意切:“郡主明鉴!
这……这真是我爹的遗物啊!他……他生前就是个穷酸的前朝史官!前朝没了,
赵家……赵家进了城,他……他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就被……就被砍了脑袋!死得冤啊!
”我一边哭诉,一边狠狠掐着自己的大腿内侧,剧痛袭来,眼泪立刻像开了闸的洪水,
哗哗往下淌,“我留着它,就是……就是提醒自个儿,在这乱糟糟的世道里,
人命……人命贱得像草!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地活着啊!”我哭得声嘶力竭,
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肩膀一抽一抽,看着要多惨有多惨。凉亭里只剩下我压抑的抽泣声。
赵明锦捏着那块玉佩,沉默地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
刮过我的眼泪,刮过我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那沉默长得像一个世纪。就在我快要喘不上气,
以为下一秒她就会叫侍卫把我拖出去砍了的时候,她忽然手腕一翻,把那块烫手的玉佩,
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回我怀里。“收好,”她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听不出喜怒,
“别让人看见。”说完,她转过身,径直走到案板前,拿起一张饺子皮,
舀了一勺馅儿放上去,手指翻飞,动作流畅地捏合起来,
仿佛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从未发生过。我愣在原地,像尊泥塑木雕。
怀里那块玉佩冰凉刺骨,却烫得我手心全是汗,湿漉漉的。我攥紧它,指节用力到发白,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第一次,
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冒出来:这郡主……她可能……真没我想的那么傻。她到底信没信?
她为什么不发作?无数的疑问像蚂蚁一样啃噬着我的神经。除夕夜,宫里赐宴,她喝了不少。
回府时脚步都有些虚浮,却死活不肯回房,硬拉着我爬上府里最高的望楼看烟花。
漆黑的夜空被一朵接一朵炸开的火树银花照亮,红光映在她脸上,
那双平日里锐利逼人的眼睛,此刻竟显得有些湿漉漉的,蒙着一层少见的迷离和柔软。
“燕徊,”她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点飘忽,带着浓浓的酒气,“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其实不想拿刀的。”她打了个酒嗝,身子晃了晃,
我下意识伸手虚扶住她的胳膊。“我想当女将军,威风凛凛那种……可我爹不让,
他说……说女孩子家,就该安安分分待在闺房里绣花……”她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后来啊……赵家起兵了,我爹死了……嘿,没人管我了,
我反倒……反倒能拿刀了。”她仰头,又灌了一口酒,酒液顺着嘴角流下,
“可……可我还是……没绣过花。一次都没有。”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委屈。
夜风很冷,吹得她单薄的衣衫紧贴在身上。
看着她微微发红的鼻尖和带着醉意、有些茫然的眼神,
我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针尖轻轻扎了一下,又酸又软。那句安慰的话,根本没经过脑子,
脱口而出:“我替你绣。”她愣了一下,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
差点从栏杆上翻下去,全靠我死死拽着。“你?哈哈哈!燕徊!”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指着我,上气不接下气,“你连……连针都拿不稳吧?别逗了!”我脸上臊得慌,
心里却莫名地较上了劲。第二天,我真就偷偷摸摸溜出了府,在城里最不起眼的杂货铺里,
买了一套最便宜的针线。躲在房里,对着块布头,笨手笨脚地戳。
指尖不知道被扎了多少个血眼子,疼得我龇牙咧嘴。折腾了大半天,
终于歪歪扭扭地绣出了一个勉强能认出是“锦”字的玩意儿,丑得惊心动魄。趁她不注意,
我偷偷把它缝在了她最常穿的那件墨色披风内衬里,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她一直没发现。
可每次看到她披着那件披风,大步流星地走过回廊,或者在沙盘前蹙眉凝思,
我心里就像偷偷开了瓶陈年的甜酒,咕嘟咕嘟地冒着细密欢快的小气泡,
带着一种隐秘的、近乎幼稚的满足感。这感觉陌生又新奇,冲淡了那啃噬多年的恨意。开春,
料峭的寒风还没散尽,北境果然传来了急报。蛮族几个大部落联合,集结重兵,悍然叩关,
烧杀抢掠,边关告急!烽火狼烟像一道狰狞的伤疤,撕裂了北方的天空。
赵明锦脸上的那点柔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被寒风吹散的薄雾。她眼神锐利如鹰隼,
周身散发出一股铁血肃杀之气。点将,披甲,动作快得惊人。沉重的玄铁甲胄覆盖在她身上,
发出冰冷的金属摩擦声。她翻身上马,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天生就该在战场上驰骋。“燕徊!
”她勒住躁动的战马,回头看我,声音斩钉截铁,“跟我走!军师!”没有犹豫,
我立刻翻身上了另一匹备好的战马。马蹄踏碎驿道的尘土,一路向北疾驰。
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混合着尘土和马匹的汗味。
看着前方那个挺拔的、被甲胄勾勒出凛然轮廓的背影,我心头沉甸甸的,
复仇的火焰与另一种陌生的、沉甸甸的东西交织缠绕,理不清,剪不断。
战场比想象中更残酷。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和尸体腐烂的混合气味,令人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