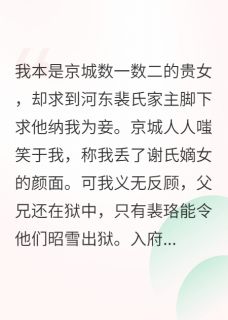我本是京城数一数二的贵女,却求到河东裴氏家主脚下求他纳我为妾。京城人人嗤笑于我,
称我丢了谢氏嫡女的颜面。可我义无反顾,父兄还在狱中,只有裴珞能令他们昭雪出狱。
入府那日,裴珞勾着我的下颌,眉眼上挑。“清清,既为妾室,就要恪守妾室的本分,
每日勤勉服侍于我,不得推诿,明白吗?”我望着这个曾是我未婚夫的男人,俯首下拜。
“清蘅明白,定会用心伺候裴主与夫人。”——1裴珞粗鲁地将我扔上床榻,
纵情释放他不知餍的欲望。无论我怎样哭求,都不曾停下来。
直到他将浸透一抹殷红的元帕从我身下抽出,
那双被欲色填满的眼眸泛起滔天波澜——“清清,你怎会——”我嗓音沙哑,
挣扎着问他:“裴主,我的父兄……您答应过的……”他倏然冷笑,拂开我汗湿的发丝。
“清清,长夜漫漫,莫要提煞风景之人。”这一夜,他要了七次水。初承恩露的我,
根本就不能承受这般剧烈的欢情。次日去给夫人请安时,走路都不利索。裴珞的夫人,
是帝后最宠爱的嘉喜公主,当年被裴珞从民间寻回后,与他一见倾心,成就一段佳话。
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笑容绽放,如春水照花。“清蘅,昨夜很辛苦吧?”“夫君疼惜我,
从不肯那般粗鲁。你是妾室,他自可不必怜惜。好好伺候着吧!
”我低下谢氏嫡女尊贵的头颅,柔顺和婉。“清蘅晓得,会恪守本分。
”嘉喜公主轻笑一声:“既然你站立不得,便跪侍于我。”我自小金尊玉贵,
从未做过伺候人的活。在嘉喜公主那里跪侍一天,膝盖早已磨破了皮,剧痛不已。
可裴珞夜间依旧没有放过我。他看着我布满伤痕的膝盖,眼神冷若寒冰。
“莫要以为把自己搞得一身伤,就能躲过去!”“你当日跪求于我,
宁可入府为妾也要救你父兄,便该知道身为妾室,这就是你的本分!”本分?
他与嘉喜公主日日都在提醒我,做个床榻之间的玩物,屈辱一生,便是我的本分!
眼角的泪水早已一片冰凉,裴珞在满足的喘息中解开我手腕上的绸带,抚摸着那一片红痕。
“清清,像从前那样唤我一声,唤我七郎。”七郎……那是我从前与他情好之时,
才会唤出的缱绻爱语。可现在,他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丞相,他的妻是尊贵无比的公主。而我,
是他的贵妾。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到不起一丝波澜。“裴主,清蘅只是个妾室,
唤您裴主,才是妾的本分。”2次日,我并未再去跪侍嘉喜公主。嘉喜公主入宫小住,
好多日不曾回来。丫鬟红芜拿来药膏为我细细涂抹,药香浓郁,一闻便知是上好的。“红芜,
你可能出府?”尽管昨日裴珞告知,我父兄已被释放,可我并不能完全放心。
妾室不可随意出门,我如今被困在这一方天地,只怕还不如一个丫鬟自由。红芜面色为难,
神色中带了几分不忍:“**,家主吩咐了,咱们倚晴院中,所有人出去,
都得拿他的亲笔手谕才可放行。”我心中泛起一阵麻麻的痛,裴珞他……竟对我如此残酷。
我与裴珞相识五年,曾经的我是谢氏嫡女,而他是裴家世子,门当户对。曾经的他,
长身玉立,面如冠玉,是京城第一佳公子。我在谢家宴席上捡到他的贴身玉佩,
从此与他交往。三年前,他拿着这枚贴身玉佩前来提亲,世人皆称,裴郎谢女,天作之合。
可在即将成婚之时,他的继母骤然过世,他需得守孝三年,不得成婚。
那时的我拿着玉佩对他说:“七郎,一生一世,我都会等你。”可我终究没有等到他。
一年前,他在东南九丘之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遇见了帝后遗落在民间多年的女儿。
且与她,一见钟情。回到京都之后,他当即退了谢府的亲事,迎娶嘉喜公主。
世人皆骂他忘恩负义,谢家也转而支持他的父亲。我什么也没说,只将他聘礼退还,
与他相忘于江湖。我自问,从未有负于他。他终究是斗赢了自己的父亲,继承家主之位,
官居一国之相,却罗织罪名将我父兄下狱。我只得拿着当年他予我的青玉佩,跪求于他,
放过我的父兄。他只称:“入府为妾,我保你父兄无虞。”他竟憎恶谢氏到如此地步,
贬昔日的未婚妻为妾,折辱谢氏满门。寄人篱下,我身不由己,依然只能匍匐在裴珞脚边,
请他允我回谢府看一看。他倒是未曾动怒,只拍了拍腿:“坐上来,让我看看,
你能为谢氏做到什么地步。”我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于他,他明明是极为满足的,
却鄙夷地将帕子扔在我身上。“不过如此还敢为谢氏筹谋,毫无自知之明!
”我将手心掐得发白,终于明白,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轻袍缓带,温文尔雅的裴家世子。
他恨谢氏,也恨我。3嘉喜公主生辰,裴珞为她置办了精致宴席,他坚持要我也出席。
我坐在下首,看着他们夫妻举杯共饮,脉脉含情,心中却一片麻木。
嘉喜公主忽然开口:“听闻裴郎当初为了追求清蘅妹妹,一曲《凤求凰》惊艳整个京都,
裴郎何时也为我弹奏一曲?”裴珞笑得温文尔雅:“这有何难,去取绿漪来。”我心中一顿,
终究是垂下了眼眸。绿漪,是当日订婚之时,我送他的举世名琴。他如今要用我送他的琴,
为旁人弹奏当年向我表明心意的曲子。裴珞……你竟厌恶我至此。当夜,
裴珞去了嘉喜公主房中。这还是我入府以来,他第一次去嘉喜公主房中。不用服侍于他,
于我也是好事。只是还未到入寝时分,他就又一次出现在我房中,连衣衫也未换,
身上还带着嘉喜公主惯用熏香味道。他将我放于膝上,神色轻佻:“嘉喜身子弱,倒不似你,
天生就是个玩物,怎么弄都耐受得住。”我不愿遂他心意:“妾来了癸水,不能侍奉裴主。
”他却以修长手指摩挲我的口唇:“只要你有心侍奉,有的是办法。”他身上的香味太重,
我有点嫌弃,别开了脸去。他冷笑一声,骤然放开我:“你三哥偷娶庶族女子。士庶不婚,
此举已犯刑律,你说我是不是应将他流放两千里?”我倏然怔愣,当即跪下,
低头解开他的腰带。“裴主,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的三哥……”他笑得满足又放肆,
手指抚过我的头顶:“清清,你天生就是要伺候男人的。”嘉喜公主未再要我跪侍,
却要我时常陪她出席各种贵女的宴会。我在这种宴会上只得随侍在她身边,
听着旁人对我的冷嘲热讽。“那不是谢清蘅吗?当初吟诗作画,号称京城第一才女,
看看她如今的样子!”“自甘为妾,不知廉耻!”“当年皇后娘娘选太子妃,她都看不上,
还说只要一心人。呵,真是咎由自取。”嘉喜公主看我的目光中,竟有几丝怜悯。
“清蘅妹妹,这些女人爱嚼舌根,你莫往心里去。不如去园子里走走,那边也清净些。
”我随即离去,却在廊下遇见了最不想见到的人。大理寺卿,欧阳澈。
欧阳澈少时在谢家读过几年书,十七岁便中了探花郎。当初裴珞退亲,他当晚便来提亲。
他是寒门探花,如玉君子。父亲当即允了他,不过一个月便将我嫁与他。是我,背弃了他。
我为救父兄,让他签了和离书,义无反顾入裴府为妾。让他成为京中笑柄,受尽言语奚落。
我避无可避,他却上前,一把拉住我。“清蘅妹妹,你过得可还好?那裴……他可有欺辱你?
”我抬眸望他,却红了眼眶。最该恨我之人,看向我的眼神中,却没有半分恨意,唯有心疼。
“澈哥哥,忘了我吧,我不值得你记挂。”“不——”他握着我的手,
将一个纸团不动声色地塞给我。“清蘅妹妹,我对你的心从未变过。无论你何时想要回头,
我都会在原地等你。”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抬眸之时,却看见裴珞在长廊尽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眼神中,极尽嘲讽。4当夜,正院来人传话,说家主与夫人行房事,
让我跪侍一旁。红芜满面愤懑:“**,你是妾室,却不是通房。他们怎可以如此折辱?
”我喟然长叹,裴珞让我做他的妾,可不就是为了折辱我么?我跪在正房门侧,
听着帐中衣物窸窸窣窣。嘉喜公主的喘声悠长娇媚,带着满腔的春情与幸福。
裴珞果然很怜惜她,与同我在一起之时,天差地别。他同我在一起之时,
床榻摇得几乎要散架,他口中满是难堪之言,无一不在折辱于我。可在这里,床榻纹丝未动,
他甚至连一丝喘息也无。半晌,他平淡的声音响起:“过来,给我擦拭。”我膝行至他脚旁,
并未抬头,只觉得他浑身冰冷,散发着透骨的寒意。
他手指抚上我的后颈:“今日同欧阳澈说什么?”我心下一跳:“没什么,
只是遇见了简单招呼一声。”欧阳澈给我的纸团中,告诉我父兄皆安,让我不必担心。
且还说,若我有任何需求,就去找洗衣房的王大娘,她会帮我。这件事,
万万不能被裴珞知道。随着我的擦拭,裴珞抚在我后颈上的手指渐渐滚烫,
他的身子也渐渐发热。
他竟……起了欲念……可他的嗓音却一如既往的冷淡:“我以大理寺卿之妻为妾,
他可有不服?”我倏然心惊,停下手上的动作。裴珞权倾朝野,当初我的父亲身为谢氏家主,
吏部尚书,一朝被他扳倒竟连毫无还手之力。而欧阳澈,只是个没什么根基的寒门。
“他……没有不服。当初的和离书,他也是签了名的。”“还算他有几分自知之明。
”裴珞冷哼一声,手指顺着脖颈,深入我的衣襟。“不要……”我不想在这里,如此和通房,
就真的没有区别。嘉喜公主掀开罗帐,笑着看向我。“清蘅只怕还不知,
谢家主传信昭告天下,已将你逐出谢氏门庭。以后你就不再是陈郡谢氏嫡女。
”我脑中轰得一声,支撑不住身子,颓然坐在地上。裴珞飞快地扫了一眼嘉喜公主,
看向我的眼神中,竟有那么一丝慌乱。看来,是真的……我眼前一黑,渐渐失去了意识。
待我再度醒来之时,裴珞的手放在我的小腹上,轻轻摩挲。他端来一碗汤药给我,
闻起来竟有杜仲的味道。“避子汤,以后每日都得喝。”他的神色波澜不惊,
看不出任何喜怒。我疑虑顿生,裴珞擅医术,当初我曾与他在医庐中相伴,一同采药制药。
杜仲,明明是保胎的。可如今……我接过药碗,一饮而尽。
他将当初那块青玉佩重新系于我腰上。“清清,你服侍公主不当,罚你禁足两个月。
莫要再乱跑,好好闭门反省。”我垂首听命:“妾知道了。”5裴珞日日都来,
却并未要我服侍。他只是看一看我,歇在旁边软榻上。我不必侍奉他,也不必侍奉公主,
难得清闲下来。偶尔习字执笔之时,想起父母亲族,难免神思恍然。父亲将我逐出门庭,
也是好事。我不必再为了谢氏讨好裴珞,委屈求全。我开始变得嗜睡,偶尔干呕不已。
裴珞对此置若罔闻,他只每日让我喝下那碗避子汤,并不许我医治。他变得极为忙碌,
常常夜半方归。我偶尔夜间惊醒,却感觉他的手抚在我的小腹上,那双凌厉的丹凤眼中,
竟有几分难得的柔和。“清清,我需离京几日,你切莫出院子。”可我终究是出了院子,
嘉喜公主绑了我的丫鬟红芜,说她偷盗,要将她当场打死。红芜与我一同长大,
她已是我最后的亲人,我必须救她。待我赶去时,红芜已被打得奄奄一息,满口血沫。
嘉喜公主眼神目光掠过我的腰腹,懒洋洋道:“我有一块玉佩,是裴郎所赠定情之物。
却被这贱婢偷盗而去,今日定要将她处死。清蘅不要插手,改日给你拨个更好的丫鬟。
”我跪于漫天飞雪之中,将手掌贴于额上,趴伏在冰冷积雪之中。“请问公主,
那玉佩是什么样子?”“不过一块青玉佩,正面有个珞字。”我将腰上玉佩取下,
毫不犹豫递给嘉喜公主。“是我指使红芜偷的,还请公主放过红芜。
”嘉喜公主罚我跪于雪地之中,直至天明。京城的雪夜寒冷彻骨,我渐渐没了知觉,
小腹中的下坠感越来越强烈,一阵一阵抽痛。我昏迷在大雪之中,身下的皑皑白雪上,
一滩怵目惊心的暗红。恍惚中,似是裴珞将我抱回房内。我摸到他眼角的泪水,
自那颗我吻过无数遍的泪痣上缓缓流过。醒来时,他已是眉间覆满寒霜。我四下看看,
却不见红芜的身影。“红芜呢?”我心下惶急。“一个丫鬟,
竟令你不顾我的命令私自跑出院子。”裴珞眼神中泛起彻骨痛意,他掐住我的脖颈,
将我面庞抬起,逼我直视于他。“你保不住我的孩子,这丫鬟就该死!”我惊慌失措,
鞋也顾不得穿,奔出房门,一眼就看到红芜的尸体上覆着一层白布。她本就奄奄一息,
是裴珞当胸一剑,彻底要了她的命。我抓着裴珞的衣襟,
声音尖利至撕裂:“你为何要这么做!她已是我最后的亲人……”“亲人?
你没保住的那个孩子与你我血脉相连,他才是你最后的亲人!”裴珞将我狠狠禁锢在怀中,
手掌的力度强硬狠厉。我忽而大笑,撕下那温良柔顺的伪装,满面嘲讽:“裴主,
妾日日喝着避子汤,怎会有孩子?”裴珞手掌一僵,扳正我的面孔,目光在我脸上疯狂探寻。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故意让嘉喜罚你……你根本不想生下我的孩子!”“说!是不是!
”我小产后本就虚弱,被他这般剧烈摇晃,身下再度流出斑斑血迹。可我却似感觉不到痛,
只对他扬起嘲讽的唇角:“裴主,妾卑微,不配生下你的孩子。”裴珞倒退一步,
身形竟有几分踉跄。他终是口气软了几分:“清清,不要再闹了。只要你愿意生下我的孩子,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想要出府。”6我将红芜敛葬,
葬于京郊一处鸟语花香之处。裴珞直接搬入我房中,日日要我,需索无度。我得了他的允许,
时不时可以出府,逛逛胭脂铺子,买买衣衫布料。也仅此而已。他派两个心腹暗卫跟着我,
我除了逛铺子以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京城最有名的胭脂铺「花间阁」新上了一批胭脂,
我穿一身蓝裙,坐于靠近窗子的妆案旁前,让掌柜亲自为我试妆。暗卫在路边看着我的身影,
并未跟过来。直到太阳西斜,他们屡次回头,发现蓝衣女子依旧在那妆案旁。
他们终于觉得不对,冲入阁中,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蓝衣女子,是披了一袭蓝裙的人偶。
而我早已不见踪迹。胭脂铺的掌柜,伙计,统统跑了个干净。裴珞封了京城大肆搜捕,
又令兵士将谢府与大理寺卿府邸重重包围,也未寻到我的踪迹。他并不知道,
我早已出了京城,跟着波斯人的商队一路西行。他也不知道,我通晓波斯语。
京城最出名的胭脂铺是我的私产,掌柜伙计均是我用熟了的家仆。红芜,
则是掌柜的亲生女儿。我本就皮肤白皙,将头发以秘法染成金色,换上胡女衣装,
又戴了面纱。一路上,畅通无阻。回望京城,我没有半分留恋。裴珞,愿你我永不相见!
我在安西一个小城市置了间书铺,闲时便为来往的商队做翻译。除了午夜梦回的惊惧噩梦,
我从未想起过裴珞。我想他也应该忘了我,与嘉喜公主做一对恩爱夫妻。
隔壁木匠的小儿子安达喜爱读书,时不时来我铺子里蹭免费的书看,我也不揭破他,
只是偶尔让他做些活计来补偿。安达手脚麻利,不多时便补好一扇柜门。少年皮肤黝黑,
笑容淳朴。炎炎烈日下,额角滚下大颗汗珠。我笑着递上一块帕子:“擦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