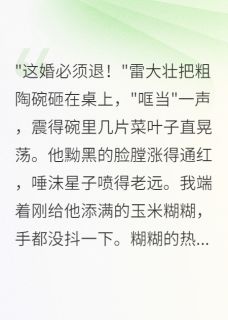
简介:他黝黑的脸膛涨得通红,唾沫星子喷得老远。我端着刚给他添满的玉米糊糊,手都没抖一下。糊糊的热气扑在脸上,有点烫。"为啥?"我问,声音平平的,像问今天地里的草锄没锄干净。"为啥?"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蹭地站起来,指着我鼻子,"雷瓷!你还有脸问为啥?你爹瘫炕上多久了?药罐子烧钱跟烧纸似的!你娘那身子骨...
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得诡异。王管事没再来,里正和雷老三一家也像缩头乌龟一样没了动静。村里那些闲言碎语反而更多了,都说我得罪了贵人,死期不远了。
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拼命侍弄那几亩薄田,希望能多收几粒粮食。空闲就去后山挖点野菜,运气好能逮只野兔或者捡点蘑菇。雷墩儿就拴在我腰上,跟个小尾巴似的。日子苦得像黄连泡的水。
这天,我刚把一小把掺了野菜的糙米下锅……
退婚的事,像长了翅膀,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雷家坳。出去挑水,河边洗衣裳,甚至下地拔草,都能感觉到那些黏在背上的目光。
"啧啧,雷瓷那丫头,命是真硬,克亲啊!"
"可不是嘛!爹瘫娘病弟傻,谁家敢要?雷大壮跑得对!"
"听说雷大壮攀上高枝了?要去镇上大户人家当差?难怪看不上她了!"
"长得是俊,可惜了,就是个扫把星!"
那些议论,压低了声……
"这婚必须退!"雷大壮把粗陶碗砸在桌上,"哐当"一声,震得碗里几片菜叶子直晃荡。他黝黑的脸膛涨得通红,唾沫星子喷得老远。
我端着刚给他添满的玉米糊糊,手都没抖一下。糊糊的热气扑在脸上,有点烫。"为啥?"我问,声音平平的,像问今天地里的草锄没锄干净。
"为啥?"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蹭地站起来,指着我鼻子,"雷瓷!你还有脸问为啥?你爹瘫炕上多久了?药罐子烧钱跟烧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