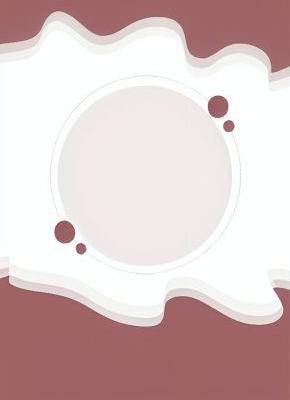水晶高脚杯里,猩红的液体仿佛凝固的血,映照着天花板上那盏巨大而冰冷的水晶吊灯。
林晚坐在长餐桌的一端,像一尊精心打扮过的木偶。桌上铺着爱尔兰空运来的手工蕾丝桌布,
中央是新鲜空运的白玫瑰与尤加利叶插花,散发着矜持的香气。
银质烛台上的蜡烛已经燃掉一小半,烛泪缓缓堆积。
几道精致的法餐——鹅肝、焗蜗牛、低温慢煮的和牛牛排——在她面前逐渐失去温度,
如同她一点点沉入冰窖的心。墙上的布谷鸟钟,木制小鸟机械地弹出来,叫了九声。每一声,
都像敲在她的肋骨上。十年了。嫁给陆靳言的十年,也是她扮演另一个女人的十年。白薇薇,
那个像月光一样笼罩在她婚姻上空的名字。她记得新婚夜,他醉醺醺地捏着她的下巴,
眼神迷离又冷酷:“知道为什么娶你吗?因为你这双眼睛,有几分像她。安分点,
做好你的影子,陆太太的位置就是你的。”于是她学白薇薇的穿着,
只穿素净的白色、米色;学她说话时轻柔拖长的尾音;放弃了她最爱的辣味川菜,
改做清淡的粤菜和苏帮菜;甚至把她留了多年的长发,也烫成了白薇薇那样的微卷。
她像一个虔诚的学徒,临摹着一幅不属于自己的画卷,
期盼着画的主人偶尔能投来一丝认可的目光。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那个特殊的**始终沉默着。她甚至怀疑是不是手机坏了,一次次拿起检查,信号满格。
也许,他根本不记得这个日子了吧。或者,记得,但觉得与她无关。
玄关处终于传来指纹锁开启的“滴滴”声。林晚像被电击般猛地站起身,心脏骤然紧缩,
又疯狂跳动。她下意识抚平裙摆上并不存在的褶皱,
脸上挤出练习过千百遍的、模仿白薇薇的温柔浅笑,几乎是小跑着迎上去。门开了。
高大的身影裹挟着夜晚的寒气和淡淡的酒气进来,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
眉眼深邃,却覆着一层永不融化的霜雪。但他不是一个人。
一个穿着香奈儿最新款白色软呢裙的女人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笑容甜美,
声音娇嗲:“靳言,你们家好大好漂亮哦,比我在法国住的古堡酒店也不差呢。”是白薇薇。
正主回来了。林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停止了流动。
她看着白薇薇自然地将外套脱下,递给旁边的佣人,那姿态,仿佛她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陆靳言的目光扫过来,落在林晚身上,带着惯有的审视和不耐烦:“还站着干什么?
没看到有客人?薇薇还没吃晚饭,让厨房再准备几个她爱吃的菜。”命令的口吻,理所当然,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被撞破的尴尬。林晚机械地接过他脱下的外套,
上面沾染着陌生又昂贵的女士香水味,刺得她鼻尖发酸。她像个被输入错误指令的机器人,
呆呆地看着陆靳言极其自然地引着白薇薇走向餐厅,
甚至绅士地为她拉开了原本属于林晚的主位椅子。“呀,晚晚,你准备了这么多菜呀?
好用心哦。”白薇薇坐下,目光扫过一桌冷掉的盛宴,语气惊讶,眼底却藏着隐秘的嘲讽,
“不过我和靳言刚参加完一个酒会,吃了点东西,现在不太饿呢。这些……好像也凉了,
吃了对胃不好。”陆靳言闻言,眉头微蹙,对候在一旁的管家道:“撤下去,
重做薇薇爱吃的清蒸东星斑和蟹肉竹荪汤。”“是,先生。”佣人们悄无声息地上前,
动作迅速地将林晚耗费一下午心血准备的菜肴一一端走。那盘她小心翼翼控制火候的牛排,
被像处理垃圾一样倒进垃圾桶,发出沉闷的声响。林晚站在原地,
手里还抱着那件带着别人香水味的外套,觉得自己也像那盘牛排,被无情地丢弃了。
她默默走到长桌的末尾,那个离陆靳言最远的位置坐下。像个多余的旁观者。
晚餐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进行。白薇薇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她在法国的见闻,
时装周、画展、私人派对……那些林晚从未接触过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陆靳言偶尔颔首,
嘴角噙着一丝难得的、真实的笑意,那是林晚从未得到过的温和。
他甚至细心地替白薇薇布菜,挑出鱼刺。林晚低着头,用银叉机械地戳着面前新上的沙拉,
翠绿的蔬菜吃在嘴里,只剩下苦涩。她听着他们的谈笑风生,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或者说,
一个不该出现在这幅和谐画面里的瑕疵。“对了,晚晚,”白薇薇突然将话题引向她,
笑容无辜又残忍,“听说你这几年,一直在学我的样子?其实真的没必要啦。靳言跟我说过,
模仿得再像,也失去了本真,反而显得可笑。做自己不好吗?虽然……”她顿了顿,
上下打量了一下林晚,“可能有点难为你了吧。”空气瞬间凝固。佣人们屏息低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陆靳言的眉头皱得更紧,他似乎觉得白薇薇的话有些过了,但最终,
他只是将目光投向林晚,带着一丝不耐和警告:“薇薇心直口快,没有恶意。你听着就是,
别胡思乱想。”没有恶意?林晚猛地抬起头。十年来的委屈、不甘、隐忍,
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她看着眼前这个她爱了十年、卑微到尘埃里的男人,
看着他维护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心脏疼得快要裂开。“陆靳言,”她的声音干涩发颤,
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晰,“这十年,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一个随时可以丢掉的、拙劣的复制品吗?”陆靳言显然没料到她会直接质问,愣了一瞬,
随即脸色沉了下来,语气冰冷:“林晚,注意你的身份!安安分分做你的陆太太,
陆家不会亏待你。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贪图不属于你的东西!”贪图?她贪图什么?钱?
地位?还是他那颗永远捂不热的心?是啊,她最贪图他的爱,也最不值钱。
白薇薇轻轻扯了扯陆靳言的袖子,声音委屈又大度:“靳言,你别凶晚晚嘛,
今天毕竟是你们结婚纪念日……虽然,你答应陪我去看《星夜》午夜场首映的,
时间快到了哦。听说很难抢的,还是你特意让助理包了场……”陆靳言立刻起身,
脸上的不耐被歉意取代:“好,这就走。”仿佛多留一秒,都是浪费生命。走到门口,
他像忽然想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回头对僵在原地、脸色惨白的林晚吩咐:“下周末薇薇的生日宴,就定在家里花园,
你亲自负责筹备,所有流程按最高规格来。我不希望出任何纰漏。”门“砰”地一声关上。
巨大的声响在整个空旷的别墅里回荡,然后是无边无际的死寂。佣人们不知何时都已退下。
林晚独自站在奢华却冰冷的餐厅中央,看着长桌上几乎没动过的、为白薇薇重做的菜肴,
看着那重新点燃却无人欣赏的蜡烛。她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肩膀剧烈地颤抖,
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癫狂,眼泪却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模糊了眼前的一切。十年。
三千六百多个日夜。她倾尽所有热情和爱意,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那天之后,林晚病了。
高烧反复,昏昏沉沉。陆靳言没有回来,甚至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
只有家庭医生每天准时来报到,开最贵的药,打最贵的针。佣人张妈偷偷告诉她,
先生陪着白**去海岛度假了,为生日宴挑选礼服。林晚躺在巨大的双人床上,
感觉身体和心一样冷。她看着天花板上繁复的浮雕,
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囚禁在金丝笼里的雀鸟,羽毛黯淡,歌声喑哑。烧稍微退去后,
她强撑着起来。陆靳言的书房需要定期整理,这是他立下的规矩,即使她病了,
佣人也不敢代劳,生怕碰坏了什么重要文件。他的书房和他的人一样,
冷硬、整洁、一丝不苟。巨大的红木书桌上,除了电脑和一部座机,空无一物。
她熟练地用软布擦拭灰尘,将略微歪斜的摆件归位。
当她擦拭书架顶层一个落了些灰的檀木匣子时,手一滑,匣子掉在地上。
“啪嗒——”匣子摔开,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除了一些旧邮票和钢笔,
还有一张泛黄的合照,以及一个用透明证物袋装着的小块褪色布料。
照片上是少年时期的陆靳言和一个女孩,女孩笑靥如花,正是白薇薇。但林晚的目光,
却被那块布料牢牢吸住了。那是一块蓝色的棉布手帕残角,边缘被烧焦发黑,
上面用白色的线,绣着一个歪歪扭扭、几乎辨认不出的“晚”字。她的呼吸骤然停止!
这是……这是她小时候的手帕!是母亲教她刺绣时,她绣的第一件东西,虽然丑,
她却很喜欢,用了很久!她猛地想起一段被尘封的记忆碎片——大概十四五岁的夏天,
她去看望在陆家老宅帮工的远房姨妈,贪玩跑去了后山的仓库附近。突然听到爆炸声,
然后是浓烟滚滚……她吓坏了,想跑,却听到里面传来微弱的呼救声。她咬着牙冲进去,
看到一个少年被倒下的货架压住了腿,额头流血不止,已经陷入半昏迷。
她拼尽全力挪开货架,用自己的手帕死死按在他流血的额头,瘦弱的身体几乎透支,
才一点点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她记得自己吓得浑身发抖,
记得少年模糊的轮廓和痛苦的**,记得他紧紧攥着她的手,像是抓住唯一的浮木……后来,
陆家的人闻声赶来,混乱中,她因为吸了浓烟也体力不支晕了过去。再醒来,已经在姨妈家,
姨妈只叮嘱她别乱说话,免得惹麻烦……原来……那个少年是陆靳言?!所以,
当年救了他的人,是她林晚?!那块她用来给他止血的手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和白薇薇的照片放在一起?一个可怕的、荒谬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中了她!
是白薇薇冒领了她的救命之恩?!所以陆靳言才对白薇薇如此特别,
所以他才娶了有几分像她的自己?!巨大的冲击让她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稳。
她扶着冰冷的书架,才勉强没有摔倒。心脏狂跳,血液逆流,浑身一阵冷一阵热。就在这时,
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毫无预兆地涌上喉咙。她冲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干呕起来,
眼泪都呕了出来。最近总是这样,嗜睡、乏力、反胃……一个更加荒谬,
却又隐隐带着一丝微弱希冀的念头,闯入她混乱的脑海。她……是不是怀孕了?
这个孩子……来得如此不是时候,却又像是绝望深渊里垂下的一根蛛丝。
也许……也许因为这个孩子……陆靳言会……会怎样呢?她会动摇吗?她不知道。但这一刻,
她迫切地需要知道答案。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戴上口罩墨镜,
偷偷去了离家很远的一家药店,买了好几支不同品牌的验孕棒。回到家,反锁洗手间的门。
她颤抖着手拆开包装,按照说明操作。等待结果的那几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她死死盯着白色的显示窗口,心跳如擂鼓。终于……清晰的两条红杠。又一支,
还是两条红杠。她怀孕了。
在她和陆靳言极其有限、近乎履行义务的、毫无温存可言的亲密中,
竟然奇迹般地孕育了一个孩子。一丝复杂的、掺杂着恐慌和微弱喜悦的情绪,像细小的藤蔓,
缠绕上她死寂的心。这是她的骨肉,是她血脉的延续,是这冰冷世界里可能唯一的牵绊。
那微弱的希冀又开始冒头——也许,也许他知道后,会有一点点的动容?
会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对她……有一点点不同?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颤抖着手,
第一次主动拨通了陆靳言的电话。她甚至卑微地想,只要他有一点点关心,
她就告诉他当年的真相,告诉他她才是救他的人……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对面背景音嘈杂,
有悠扬的小提琴声,还有白薇薇娇俏的笑声:“靳言,快来看,这颗钻石好闪哦!
”陆靳言的声音隔着电话传来,带着被打扰的不耐烦:“什么事?
我不是说过没事别打我电话?”林晚的心凉了半截,但还是鼓起勇气,声音发颤:“靳言,
我……我怀孕了。”对面沉默了几秒。那沉默像一把钝刀,在她心上缓慢地切割。随即,
冰冷刺骨、充满嘲讽的声音炸响在她耳边:“林晚,你真是越来越有手段了!怎么,
以为用孩子就能绑住我?谁知道是不是我的种?打掉!”“不是的!真的是你的!
我只有你……”她急急地辩解,声音带上了哭腔。“我没空听你演戏!”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不留一丝余地,“听着,立刻、马上,去医院处理掉!还有,薇薇的生日宴马上到了,
你给我安分点,要是敢出任何问题,你知道后果!”“嘟嘟嘟——”忙音像死亡的宣告,
彻底掐断了她最后一丝幻想和刚刚燃起的、对未来的微弱期盼。
孩子……他连他自己的骨肉都可以如此轻易地宣判死刑。只因为,是她林晚生的。
巨大的绝望和冰冷的恨意,如同海啸般瞬间将她吞没。她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
手机从无力的手中滑落。她摸着依旧平坦的小腹,那里悄然孕育着一个不被父亲期待的生命。
泪水无声地滑落,但这一次,不再是委屈和悲伤,而是彻底的死心和决绝。也好。从此,
她真的只剩下这个孩子了。她缓缓抬起头,
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眼睛红肿、卑微可怜的女人。够了。她深吸一口气,
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坚硬、沉静。她最后看了一眼这栋承载了她十年噩梦的华丽牢笼。
是时候离开了。白薇薇生日宴当晚,陆家庄园灯火璀璨,恍如白昼。
巨大的草坪被精心布置成梦幻花园,香槟塔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衣着光鲜的宾客们觥筹交错,
笑语喧哗。专业的交响乐队演奏着悠扬的乐曲。
陆靳言作为宴会的实际主导者和白薇薇的护花使者,穿着高级定制的白色西装,
俊美得如同童话里的王子。他全程陪在白薇薇身边,看着她穿着昂贵的定制礼服,
像只花蝴蝶般在人群中穿梭,接受着众人的赞美和艳羡。“靳言,你看王太太送的翡翠,
成色真好!”“靳言,李总刚才夸你眼光好,把宴会办得这么成功呢!
”白薇薇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和得意。陆靳言端着酒杯,唇角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应付着来往的宾客,心里却莫名地有些烦躁和……不习惯。
那个平时总会在他视线范围内小心翼翼出现的女人,今天似乎一直没看到。
就连宴会的各项流程,也都是管家在忙前忙后地指挥,她人呢?
又躲到哪里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他下意识地搜寻了一圈,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