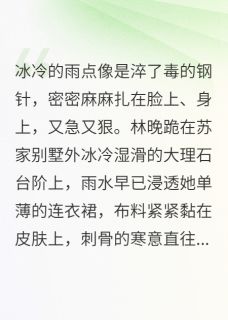冰冷的雨点像是淬了毒的钢针,密密麻麻扎在脸上、身上,又急又狠。
林晚跪在苏家别墅外冰冷湿滑的大理石台阶上,雨水早已浸透她单薄的连衣裙,
布料紧紧黏在皮肤上,刺骨的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她浑身都在控制不住地发抖,
牙齿咯咯作响,每一次急促的呼吸都带着白茫茫的水汽。脚下,散落着被撕得粉碎的纸张。
那是她的大学毕业证书,几个小时前还承载着对未来卑微却真实的期许。如今,
那些象征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碎片,像肮脏的垃圾一样,被无情地踩进泥泞的水洼里,
字迹模糊一片。别墅那两扇沉重的、象征着森严等级和冰冷拒绝的雕花铁门,
在她身后“哐当”一声巨响,死死关闭。那声音如同最后的判决,
彻底斩断了她与这栋华丽牢笼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门内透出的那点暖黄灯光,
吝啬地照亮了门口一小片区域,却吝啬地不肯多分一丝暖意给门外泥泞中的她。
林晚的手指早已冻得麻木僵硬,几乎失去知觉。她固执地、近乎自虐般地抠挖着地上的泥水,
徒劳地试图将那些被雨水泡得发胀、沾满污秽的纸屑一点点拢在一起。雨水冲刷着她的手背,
泥水顺着指缝流下,混着一种更温热的液体——那是额头被硬物砸破后淌下的血,
正顺着她的眉骨、颧骨蜿蜒而下,滴落在那些碎纸上,晕开一小片惊心动魄的暗红。
砸中她的,是一个冰凉沉重的物件——一个雕工异常繁复精美的翡翠莲蓬。
那是苏家老爷子苏宏业书房博古架上的旧物,据说是某位早逝姨太太的遗物。就在刚才,
她被粗暴地推出门外时,苏宏业那续弦的妻子,
那个妆容永远一丝不苟、眼神却淬着毒汁的继母徐曼,冷笑着抓起它,狠狠砸在了她的额角。
“滚!拿着你这野种碰过的东西,一起滚!别脏了苏家的地!”徐曼尖利刻薄的声音,
穿透厚重的雨幕和紧闭的铁门,毒蛇般钻进林晚的耳朵。林晚的动作猛地顿住。
她缓缓抬起头,任由冰冷的雨水冲刷着额头的伤口,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
视线透过凌乱湿透贴在脸上的发丝,死死锁定在泥水里那个沾着血污和污泥的翡翠莲蓬上。
那抹绿,在浑浊的泥水和刺目的血红映衬下,显得异常诡异而冰冷。它像一个屈辱的烙印,
一个被彻底抛弃的证物。野种……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她的心上。是啊,
她林晚,在苏家当了整整二十年备受宠爱、锦衣玉食的“苏家大**”,
原来只是个鸠占鹊巢的野种。一场精心策划了二十年的骗局,
一场为苏家真正的血脉挡灾避祸的卑劣替身游戏。如今,真正的金枝玉叶被寻回,
她这个冒牌货,自然就该像垃圾一样被清扫出门,连同她过去二十年付出的所有感情和努力,
都成了令人作呕的笑话。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比这深秋的冷雨更甚百倍,
从她心底最深处汹涌而出,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
她不再试图去捡那些已经彻底毁掉的纸屑碎片。手,带着一种近乎决绝的颤抖,
伸向泥水中那个冰冷的翡翠莲蓬。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玉石,
以及玉石上沾染的、属于她自己的、带着体温的血迹和冰冷的污泥。她用尽全身力气,
紧紧攥住了它。尖锐的莲蓬边缘硌着掌心,带来清晰的痛感。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湿透的裙摆沉重地贴在腿上。额头的伤口还在流血,混着雨水流进眼睛,
视野一片模糊的猩红。她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象征着过去二十年虚幻人生的铁门,
门内透出的光,此刻在她眼中只剩下虚假和冰冷。没有哭喊,没有哀求。
只有无边无际的冰冷和一种沉入深渊般的死寂。
她攥紧了手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那个冰冷、沉重、沾着她血迹的翡翠莲蓬,猛地转过身,
踉跄着,一步一步,坚定地、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外面无边的、吞噬一切的黑暗暴雨之中。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却又无比清晰地将那个名为“苏晚”的幻影,
彻底碾碎在身后的泥泞里。雨幕,瞬间吞没了她单薄而决绝的背影。五年光阴,
足以冲刷掉太多东西。额角那道被翡翠莲蓬砸出的伤疤,早已褪去了最初的狰狞红肿,
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几乎融入肤色的浅白痕迹,像一道被时光刻意淡化的旧年封印。
唯有在情绪剧烈波动或极其疲惫时,才会隐隐泛起一丝酸胀,
提醒着林晚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苏家别墅的雕花铁门、水晶吊灯的光芒、以及徐曼那淬毒般的眼神,
都已在记忆深处模糊成一片遥远而压抑的背景噪点。那枚曾沾满血污和污泥的翡翠莲蓬,
如今静静地躺在一个铺着深蓝色天鹅绒的旧首饰盒里,被她藏在了出租屋衣柜最深的角落,
和几件同样带着旧时光气息的廉价衣物挤在一起。她很少去触碰它,仿佛那是一件不祥之物。
生活像一条被砂纸反复打磨过的河,粗糙,却也顽强地向前流淌。
林晚早已褪尽了“苏家大**”所有不切实际的浮华外衣。白日里,
她是“墨韵”画廊里那个沉默寡言却手脚麻利、对艺术品保养知识熟稔于心的助理。夜晚,
她则缩在城郊老旧的出租屋里,就着昏黄的台灯光,在二手笔记本电脑上敲敲打打,
接一些设计、文案之类的零碎散活。每一分钱都挣得实实在在,
带着汗水的咸涩和指尖的酸麻。“墨韵”的老板是个有些艺术脾气的干瘦老头,姓周,
业内都叫他老周。他看中了林晚身上那股子被生活磨砺出的沉静和手上那份难得的细致功夫。
“小林啊,”老周曾叼着他那从不离手的烟斗(尽管里面从未装过烟丝),
眯着眼打量正在小心翼翼为一批新到的水彩画覆上保护膜的林晚,“你这手活儿,
没在正经修复工作室干过几年,练不出来。屈才啦!”林晚只是低着头,
用小刷子轻轻拂去画框边缘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浮尘,声音平静无波:“周老师过奖了,
混口饭吃罢了。”日子就在这单调重复的节奏里滑过。直到这一天,
“墨韵”所在的这栋艺术气息浓厚的大厦楼下,平日里略显清冷的街道,
突然被一种浮华喧嚣的气氛彻底点燃。巨大的充气拱门横跨路口,
上面张扬地喷绘着金色的艺术字:“恭贺苏氏集团千金苏蕴**芳诞!
”红毯从苏氏集团旗下的奢华酒店大堂一路铺到人行道边缘,
两侧簇拥着成排盛放的香水百合和昂贵的蓝色妖姬,
馥郁到近乎甜腻的香气霸道地弥漫在空气里。衣着光鲜的侍者端着香槟托盘穿梭不息,
黑色礼宾车鱼贯而入,下来的人无不妆容精致、衣香鬓影,闪光灯此起彼伏,
捕捉着每一位踏入红毯的名流身影。苏家真千金苏蕴的生日宴,排场之大,
几乎成了全城瞩目的焦点。林晚抱着一个沉重的、装着几幅待装裱画作的大纸箱,
费力地从画廊后门挤出来,恰好撞上这铺天盖地的奢华阵仗。
她下意识地往旁边阴影里缩了缩,像是怕被那过于炫目的光芒灼伤。
目光扫过那刺眼的拱门和喧闹的人群,一种混杂着反胃和冰冷的麻木感悄然爬上心头。
苏家……苏蕴……这两个名字,像两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她早已刻意冰封的心湖底,
激起了几圈细微却无法忽视的涟漪。额角那道旧疤,又开始隐隐地泛酸。她深吸一口气,
混杂着花香的冰冷空气灌入肺腑,压下那股不适。正打算绕开这片令人窒息的浮华,
从侧面的小巷抄近路离开时,
一阵异样的、极力压抑的骚动声从不远处酒店侧门通往后方花园的僻静连廊传来。
那声音很微弱,几乎被前面震耳的音乐和人声彻底淹没。但林晚的神经,
却像被一根无形的针猛地刺了一下。她停下脚步,抱着箱子的手臂微微收紧,
目光锐利如鹰隼,穿透人群的缝隙和连廊入口装饰用的巨大盆栽枝叶,
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一闪而过的场景。两个穿着酒店安保制服、身形异常魁梧的男人,
一左一右,几乎是半架半拖着一个纤细的身影,
正快速而粗暴地将她往连廊深处、那片被高大树木和假山遮蔽的黑暗角落拽去。
那个被拖拽的身影……林晚的心猛地一沉。即使隔着一段距离,即使那人低垂着头,
长发凌乱地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
林晚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身衣服——正是今天所有娱乐新闻头版头条上,
苏蕴穿着的那套价值不菲的高定礼服!此刻那昂贵的面料被粗暴地揉皱,
裙摆拖曳在冰冷的地面上。更让林晚瞳孔骤然收缩的是,
那个被拖拽的女孩似乎并未完全失去意识。她的身体在徒劳地、微弱地挣扎着,
一只纤细苍白的手死死地抠着连廊冰冷的廊柱,指尖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
仿佛那是她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那点微弱的反抗在两个壮汉的力量面前,
如同螳臂当车。林晚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让她抱着箱子的指尖都失去了知觉。是苏蕴!
苏家刚刚找回来、正被捧在手心里的真千金!绑架?
在自家为她举办的、全城瞩目的生日宴上?这念头荒谬得让人遍体生寒。
她几乎是本能地想要后退,想要转身逃离这片即将发生的、属于苏家的肮脏漩涡。
苏家的一切,都该被彻底埋葬在五年前那个雨夜里!她林晚早已付清了代价,
凭什么还要被卷入?然而,就在她脚步微动,身体下意识地向阴影深处缩去的刹那,
连廊深处那个被拖拽的女孩,似乎用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猛地抬了一下头!
凌乱潮湿的发丝被甩开了一瞬,露出半张脸孔。那张脸在连廊幽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惨白,
额头布满细密的冷汗,眼神涣散失焦,嘴唇艰难地开合着,却发不出任何清晰的声音。
林晚的目光,像被磁石牢牢吸住,死死钉在了女孩微微敞开的礼服领口之下,
那露出的、线条精致的锁骨上。就在那白皙的肌肤上,
赫然印着一枚小小的、形状清晰的月牙形胎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一只无形的手粗暴地按下了暂停键。
所有的喧嚣——震耳的音乐、人群的谈笑、闪光灯的咔嚓声——都诡异地退潮,
化作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噪音。林晚的耳边,只剩下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的轰鸣,
沉重得像是下一秒就要炸开!月牙胎记!这个印记,像一道撕裂时空的闪电,
瞬间劈开了她记忆深处最黑暗的角落,照亮了某个早已被刻意遗忘的片段。
不是苏家富丽堂皇的别墅,不是衣香鬓影的宴会厅。是更早,
更早的时候……一条冰冷、肮脏、散发着食物馊味和垃圾腐臭气息的后巷。
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小小的她,穿着单薄的旧衣服,
蜷缩在一个散发着霉味的破纸箱里,胃里饿得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拧绞,
疼得她意识模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她以为自己会无声无息地冻死、饿死在那条臭水沟边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了。
比她高不了多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却很干净的旧棉袄,梳着两个羊角辫。
那个小女孩蹲在她面前,黑葡萄似的眼睛里盛满了真切的担忧。小女孩没有问话,
只是默默地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小心包裹着的东西。打开,
是半块又冷又硬、边缘已经发干的面包。她小心翼翼地把面包掰开,
将看起来稍软一点的那一半,轻轻塞进了饿得奄奄一息的林晚手里。然后,
她笨拙地把自己那件旧棉袄脱下来,裹在了冻得瑟瑟发抖的林晚身上。
“快吃……暖暖……”小女孩的声音细细的,带着点怯生生的温柔。林晚抬起沉重的眼皮,
模糊的视线里,只清晰地看见了小女孩弯腰时,
从旧棉袄领口露出的、左边锁骨上那枚小小的、形状独特的月牙形胎记。
像黑暗里忽然亮起的一弯微光。那个画面,那半块冰冷却救命的硬面包,
那件带着陌生体温的旧棉袄,还有那枚小小的月牙胎记……成了林晚童年灰色记忆里,
唯一带着暖色的烙印。她甚至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只记得那弯月牙。
后来她被苏家“收养”,锦衣玉食,却再也没能找到那个后巷里给她温暖的小女孩。
直到苏蕴被认回苏家,铺天盖地的报道照片里,苏蕴锁骨上那枚月牙胎记,
被媒体刻意放大渲染,成了苏家血脉不容置疑的“铁证”。那一刻,林晚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点微光,那个给予她片刻温暖的小女孩,
竟是她被命运捉弄、鸠占鹊巢二十年之久的……正主!荒谬绝伦!造化弄人!
五年前那个雨夜,被苏家弃如敝履的绝望冰冷,
与此刻连廊深处苏蕴被至亲推向深渊的惨烈景象,如同两股汹涌的暗流,
在林晚心中猛烈地撞击、撕扯!她攥着纸箱边缘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深深陷进硬纸板里,
指关节泛出骇人的青白色。救?还是不救?无数个声音在脑中尖叫嘶吼。救她?凭什么?
她是苏家的真千金!是顶替了自己二十年富贵人生的“受益者”!苏家那群豺狼虎豹,
连自己的亲生血脉都下此毒手,她林晚一个早被扫地出门的“野种”,凭什么去蹚这滩浑水?
卷进去就是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