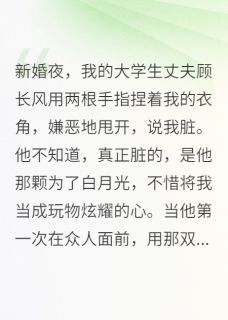新婚夜,我的大学生丈夫顾长风用两根手指捏着我的衣角,嫌恶地甩开,说我脏。他不知道,
真正脏的,是他那颗为了白月光,不惜将我当成玩物炫耀的心。当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
用那双从未碰过我的手,温柔地为我理顺发丝时,我没有半分感动。我只看到他眼角的余光,
正挑衅地瞟向他对面,他那刚结婚的发小——苏晓月。他不是爱我,他只是在用我,
向另一个男人展示他的“战利品”有多乖顺。01“林晚意,把你的东西挪远点,
别碰我的书。”冰冷的声音像淬了冬月的雪,砸在我心口。
我刚把从娘家带来的土布包袱放在桌上,离他那几本烫金封面的书还有一尺远,
他就急不可耐地开了口。今天是我们的新婚第一天。屋里红双喜的剪纸还崭新发亮,
我的心却已经蒙上了一层灰。我叫林晚意,从村里嫁到这城里大院,
人人都羡慕我嫁了个大学生,前途无量。只有我知道,我的丈夫顾长风,这位天之骄子,
有多看不起我这个农村媳妇。新婚之夜,他用被单在床中间划出一条“三八线”,
警告我:“你最好别越界,我嫌脏。”那晚,我睁着眼,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一夜未眠。
此刻,我默默地把包袱挪到墙角,低声应了句:“知道了。”顾长风没再看我,
他拿出一块雪白的手帕,仔仔细细地擦拭着刚才被我包袱“污染”过的桌面,
仿佛上面沾了什么瘟疫。他身上那股子清高的书卷气,此刻在我看来,
就是一把把戳人心的刀子。这块手帕,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对了,”他擦完手,把手帕叠成整齐的方块放回兜里,
“过两天我发小苏晓月和她男人要来家里吃饭,你准备一下。”苏晓月。这个名字像一根针,
轻轻扎了我一下。我听大院里的婶子们说过,她是顾长风的青梅竹马,也是个文化人,
前阵子刚嫁给了隔壁厂的工程师。“你到时机灵点,别给我丢人。”顾长风补充道,
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命令和警告。我捏紧了衣角,指甲陷进粗糙的布料里。我能怎么丢人?
是说话带着乡音丢人,还是不会用他那些复杂的餐具丢人?“听见没有?”他皱起眉,
对我这种迟钝的反应很不满。“听见了。”我点点头,把所有情绪都咽回肚子里。
接下来的两天,顾长风对我愈发挑剔。嫌我走路声音大,嫌我洗碗水溅了出来,
甚至嫌我身上的肥皂味太廉价。我像个提线木偶,在他划定的条条框框里小心翼翼地活着。
终于,苏晓月夫妇来的那天到了。我按他的吩咐,换上了他指定的那件的确良衬衫,
局促地坐在饭桌旁。苏晓月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穿着一身时髦的连衣裙,烫着精致的卷发,
举手投足都透着城里姑娘的自信和优越。她的丈夫,那个叫李建兵的工程师,高大健谈,
一来就和顾长风熟络地聊起了国家政策和文学。我像个局外人,插不进一句话。饭桌上,
顾长风一反常态,话多了起来,句句不离自己单位的器重和未来的规划。我注意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瞟向李建兵,带着一股暗暗较劲的意味。突然,
李建兵笑着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苏晓月碗里,宠溺地说:“晓月,你最爱吃的,多吃点。
”苏晓月甜甜地笑了。那一瞬间,我看到顾长风的脸色僵了一下。他沉默了片刻,然后,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做出了一个让我浑身血液都凝固的动作。他伸出筷子,夹起一块鱼肉,
利落地剔掉鱼刺,然后稳稳地放进了我的碗里。他的动作很轻,甚至带着一种演练过的温柔。
“晚意,”他开口,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柔和,“看你瘦的,多吃点,补补身子。
”我端着碗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02顾长风的手指修长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这样一双手,连我的衣角都嫌弃。此刻,它却为我剔了鱼刺。周围的空气仿佛静止了。
苏晓月和李建兵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李建兵随即哈哈一笑,举起酒杯:“长风,
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疼媳妇的模范丈夫啊!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顾长风嘴角勾起一抹得体的笑容,谦虚地摆摆手:“应该的,应该的。
”他甚至没看我一眼,那份温柔,那句“疼媳妇”,全是说给对面听的。
我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碗里的鱼肉散发着热气,却像一块冰,冻得我从里到外都发冷。
他的炫耀,是我的耻辱。他不是在疼我,他只是在李建兵面前,扳回一局。苏晓月看着我,
眼神复杂。那里面有惊讶,有探究,还有一丝……不易察明的情绪,或许是同情,
或许是别的。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茉莉花香水味,飘过来,让我觉得和这个屋子格格不入。
我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着那块鱼肉,迟迟没有送进嘴里。“怎么不吃?
”顾长风的声音带着一丝催促,潜台词是“别在这时候给我掉链子”。我抬起头,
努力扯出一个笑容:“凉了,我热一下。”说着,我端起碗,笨拙地站起来,差点撞到桌角。
在厨房里,**着冰冷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刚才那一幕,像一出荒诞的戏剧。
我是主角,却没有一句台词,只能任由导演摆布。我将那块鱼肉倒进了泔水桶。回到饭桌,
气氛已经恢复了热烈。顾长风和李建兵开始拼酒,苏晓月在一旁温柔地劝着,
一家人其乐融融。我重新坐下,给自己盛了一碗白饭,默默地吃着。“弟妹,
”苏晓月忽然转向我,笑意盈盈,“你和长风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以前都没听他提起过。
”来了。我攥紧了筷子,这个问题像是在审问。顾长风抢在我前面回答:“家里安排的,
她性子内向,不爱说话。”一句话,就给我定了性。顺便解释了他“金屋藏娇”的原因。
李建兵打趣道:“长风你这可是不声不响干大事啊,我们都以为你一心只读圣贤书呢。
”“再读圣贤书,也得过日子嘛。”顾长风轻描淡写地回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顿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送走客人后,屋里瞬间恢复了死寂。
我默默地收拾着杯盘狼藉的餐桌,顾长风坐在椅子上,闭着眼,似乎是喝多了。
我把他脱下来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准备挂好。
一股不属于他的、淡淡的茉莉花香钻进我的鼻子。是苏晓月的味道。刚才在饭桌上,
她就坐在顾长风旁边。我的心,又被扎了一下。“今天,你做得很好。”他忽然睁开眼,
眼神清明,哪有半分醉意。他是在夸我,夸我这个工具,在他需要的时候,配合得很好。
我没说话,只是把他的外套挂在衣架上。那件外套的袖口,有一个不起眼的磨损痕迹,
是我偷偷帮他缝补的,他大概从未发现。“以后在外面,就按今天这样。”他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语气里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满意,“记住你的身份,做好你该做的,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你的发小,苏晓月,”我终于忍不住,抬起头直视他,
“你是不是喜欢她?”顾长风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03“你胡说什么?
”顾长风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张清秀的脸因为愠怒而显得有些扭曲。“我胡说?
”我看着他,第一次没有躲闪他的目光,“你今天在饭桌上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做给她和她男人看的吗?你嫌我脏,却当众给我夹菜,顾长风,你不觉得恶心吗?
”“啪!”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我的脸上。**辣的疼,
从脸颊迅速蔓延到整个脑袋,耳朵里嗡嗡作响。“林晚意,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议论我的事?”他掐住我的下巴,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
“你以为你嫁进我们顾家,就是城里人了?我告诉你,你骨子里就是个刨土的,
永远上不了台面!”他的话,比巴掌更伤人。我看着他暴怒的眼睛,忽然就不觉得疼了,
也不觉得怕了。心死的人,是不会怕的。我平静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顾长风,
我们离婚吧。”他愣住了,似乎没料到一向逆来顺受的我,会说出这两个字。在八十年代,
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随即,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嗤笑出声:“离婚?林晚意,你脑子坏掉了?离了我,你回村里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活?”“我能拿什么活,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甩开他的手,
从墙角的包袱里,拿出我那个掉了一块漆的搪瓷缸子,这是我唯一的私人物品。“我嫁给你,
不是为了让你作践的。”我把搪瓷缸子抱在怀里,那上面印着的“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
此刻显得格外讽刺。“好,好得很!”顾长风怒极反笑,他指着我的鼻子,“林晚意,
你有种。我倒要看看,你离了我顾长风,能活成什么样!”他以为我在说气话,
以为我第二天就会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地继续当他的摆设。他错了。第二天一早,
我没做早饭,而是回了趟娘家。我没有哭诉,只是平静地告诉父母,我要离婚。
父母当然是惊雷轰顶,我爹气得抄起烟杆就要打我,骂我不懂事,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
非要回来丢人现眼。我没有辩解。回到顾家,顾长风见我真不是在开玩笑,也慌了神。
他不是怕失去我,是怕丢了他大学生的人,怕单位的唾沫星,
怕他在苏晓月夫妇面前刚立起来的“模范丈夫”人设崩塌。他开始跟我讲道理,
说夫妻哪有不吵架的,说他还年轻,脾气不好,让我多担待。我不为所动。他见软的不行,
又来硬的,把家里大门一锁,不准我出门。“林晚意,我告诉你,只要我不点头,
这婚你就别想离!”我就这样被他软禁了起来。我没有再跟他吵,每天沉默地待在屋里,
他给饭就吃,不给就饿着。我的沉默,像一根刺,扎得他坐立不安。转机,
发生在一个星期后。那天,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顾长风的大哥,顾长山,从部队回来了。
04顾长山是探亲回来的。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形高大挺拔,
皮肤是常年日晒风吹的古铜色。他的眉眼和顾长风有几分相似,但气质截然不同。
顾长风是清高的书生,而顾长山,则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沉稳,锐利。“长风,我回来了。
”他的声音低沉有力。顾长风打开门,看到他大哥,脸上挤出笑容:“哥,你回来了。
”顾长山点点头,目光越过他,落在了屋里形容憔悴的我身上。我瘦了一圈,脸色蜡黄,
眼神空洞。“弟妹这是怎么了?病了?”顾长山皱起了眉。“没……没什么,
”顾长风眼神闪躲,“就是……就是有点水土不服。”顾长山没说话,他走进屋,
把手里的网兜放在桌上,里面是几个苹果和一包桃酥。他把东西推到我面前:“弟妹,
吃点东西。”我看着他,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这是我嫁进顾家后,
第一次有人真正地关心我。晚上,我听见兄弟俩在院子里说话。“你和弟妹到底怎么回事?
她瘦得都脱相了。”是顾长山的声音。“哥,你别管了,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就是把人关在屋里不让出门?”顾长山的声音严厉起来,“长风,
你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我听院里王婶说了,你为了跟李建兵攀比,在饭桌上作秀,
是不是?”顾长风沉默了。“你把人家一个好好的姑娘娶进门,不是为了让你当枪使的。
你要是不想跟人好好过日子,就别耽误人家。”顾长山的话,一字一句,都敲在了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顾长风没再锁门。我以为事情有了转机,却没想到,是更深的深渊。第二天,
顾长风的母亲来了。她拉着我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劝我不要离婚,说长风还年轻,
让我多包容。我只是摇头。见我油盐不进,她话锋一转,开始数落我的不是,
说我生不出孩子,拴不住男人的心。就在我以为她们要放弃的时候,
顾长风端了一杯加了糖的水给我,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语气说:“晚意,喝点水吧,
我们好好谈谈。”我看着那杯水,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我假装喝了一口,
趁他们不注意,把水倒进了窗台的花盆里。那天晚上,我早早地躺下了,却毫无睡意。
我藏在枕头下的一把小剪刀,被我紧紧握在手里。这是我唯一的防身武器。半夜,
我感觉有人掀开了我的被子。是顾长风。他身上带着酒气,眼睛里是我看不懂的欲望和挣扎。
“晚意,”他压低声音,“我们生个孩子吧,有了孩子,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这就是他们“好好谈谈”的结果。用一个孩子,
彻底把我捆死在这里。我猛地坐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推开,尖叫道:“你滚开!
”他被我推得一个踉跄,恼羞成怒地扑了过来:“林晚意,你别给脸不要脸!我是你男人!
”就在他的手要撕扯我衣服的瞬间,我举起了手里的剪刀,对准了他的脸。“你再过来,
我就杀了你!”05剪刀的尖端,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顾长风的动作停住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仿佛在看一个疯子。“你……你疯了!
”“是你把我逼疯的!”我握着剪刀的手在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顾长风,我再说一遍,
我们离婚!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们对峙着,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房门被一脚踹开。顾长山像一尊铁塔一样站在门口,
他看到屋里的情景,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那只常年握枪的手上,青筋暴起。“顾长风!
你在干什么!”他一声怒吼,震得屋顶的灰尘都簌簌往下掉。顾长风吓得一个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