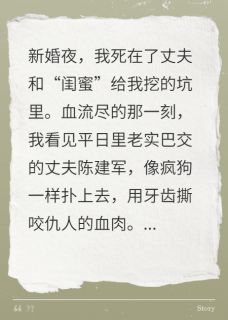新婚夜,我死在了丈夫和“闺蜜”给我挖的坑里。血流尽的那一刻,
我看见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丈夫陈建军,像疯狗一样扑上去,用牙齿撕咬仇人的血肉。原来,
他不是不爱,只是爱得太晚。再睁眼,我回到了新婚夜,他红着脸,紧张地搓着手,
轻声问:“秀兰,我……我能上炕了吗?”我笑着拉开被角,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媚眼如丝:“死鬼,磨蹭什么?天都亮了,还想不想抱媳妇儿了?”男人嘛,**一下,
不就好用了?这辈子,我要他清清白白,也要那对狗男女,死无全尸!01“秀兰,
俺……俺能上来了不?”耳边传来男人紧张又带着浓重鼻音的询问,我猛地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不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而是用报纸糊墙的土坯房顶和那盏昏黄的15瓦灯泡。
我的丈夫陈建军,正赤着上身,穿着一条的确良大裤衩,手足无措地站在炕边。他肌肉结实,
皮肤是常年劳作晒出的古铜色,此刻却因为害羞,从脖子红到了耳根。我重生了,
回到了1983年,和陈建军的新婚之夜。上一世,就是这个男人,
在我被奸夫李鬼推下山崖,被“闺蜜”王兰补刀后,疯了一样冲过去,用最原始的啃咬,
为我报了仇,最后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他不是不爱我,只是太老实,嘴太笨。而我,
蠢了一辈子,错信了那对狗男女,不仅害了自己,也毁了他本该充满希望的一生。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我喘不过气。看着他那副纯情又无措的样子,
我心底的恨意与爱意交织翻涌。“愣着干啥?等着我下去请你?”我故意板起脸,
声音却软了下来。陈建军“欸”了一声,像是得了圣旨,手脚麻利地爬上炕,
却只敢紧紧挨着炕沿,离我足有半米远,紧张得像个准备上战场的士兵。我心头一软,
也懒得再逗他。上一世的亏欠,这一世我要加倍偿还。就在我准备主动靠近他时,
“砰砰砰”,破旧的木门被敲得震天响。“建军!建军!开门啊!出大事了!
”门外传来李鬼焦急的喊声。来了。上一世,就是这声敲门,拉开了我们悲剧的序幕。
李鬼以“配电房的图纸出问题,急着要”为由,把新婚之夜的陈建军叫走。
老实的陈建军信了,这一走,就给了王兰那个**趁虚而入的机会,她跑来“陪”我,
给我灌了下了药的红糖水,再然后,
李鬼就“恰好”闯了进来……他们联手制造了一出“捉奸在床”的戏码,毁了我一辈子。
陈建军的身体瞬间绷紧,翻身就要下炕:“肯定是厂里有急事,秀兰你等我,我马上回来!
”我一把抓住他粗壮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肤里。“别去。”我盯着他的眼睛,
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可是……”陈建军一脸为难,“李鬼是我最好的兄弟,
图纸要是真出了问题,是要影响生产的,那可是大事!”“兄弟?”我冷笑一声,坐起身,
身上的红被面滑落,露出白皙的肩膀,“你家兄弟专挑人新婚夜喊人出门?
他咋那么会掐点呢?早干嘛去了?”我这话问得直接,陈建军一时语塞,愣在了那里。
他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门外的李鬼还在继续表演:“建军!你快点啊!
张主任发了好大的火,说你要是再不来,明天就别来上班了!你的铁饭碗还要不要了?
”“铁饭碗”三个字,像是一记重锤,砸在了陈建军的心上。在这个年代,
国营工厂的正式工,就是金饭碗,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他急了,
用力想挣开我的手:“秀兰,你别闹,这是正事!”“我闹?”我没松手,反而更用力了,
另一只手指着门外,一字一顿地问他,“陈建军,你用你那榆木疙瘩脑袋好好想想,
张主任是什么人?他是厂里的生产主任,图纸归技术科管,就算图纸真有问题,
也轮不到他来管你要!他给你脸了?”上一世的我,根本不懂这些厂里的门道,
只知道傻乎乎地放他走。但抱着他冰冷的尸体时,我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早就将这些关系理得一清二楚。陈建军彻底懵了,他呆呆地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陌生。他可能想不明白,自己那个从村里娶回来的,
据说有些内向胆小的媳妇,怎么会懂这些?我没给他思考的时间,凑到他耳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吹了口气。“老公,春宵一刻值千金。
今晚你要是敢出这个门,我就敢把它从里面锁死。不信,你试试?”02我的声音又轻又软,
像羽毛一样挠着他的耳廓,但话里的内容却让他浑身一僵。陈建军的呼吸都重了几分。
他不是傻子,只是忠厚。我把话挑得这么明白,他再迟钝也该咂摸出点不对劲的味道了。
门外的李鬼还在扯着嗓子喊:“建军!你倒是说话啊!你媳妇是不是不让你出来?
我说你小子,可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忘了兄弟啊!这可是关系到你前途的大事!
”他越是这么喊,就越是坐实了我的话。哪有兄弟会这样在新婚之夜,挑拨人家夫妻关系的?
我就是要让陈建军亲耳听听,他这个“好兄弟”的嘴脸。我松开手,好整以暇地重新躺下,
拉过被子盖住自己,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淡淡地说:“门没锁,要去你自己去。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今天晚上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明天咱俩就去街道办。
”“去街道办干啥?”陈建军下意识地问。“离婚。”我轻飘飘地吐出两个字。
陈建军像被雷劈了一样,整个人都定住了。这个年代,离婚是天大的事,
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词会从他刚过门一天不到的媳妇嘴里说出来。
“秀兰,你……你别吓我……”他的声音都带上了颤抖。“我没吓你,
我主打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我学着后世的流行语,语气却冰冷,“你自己选,
是要你那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前途’,还是要我这个热炕头上的真媳妇。”说完,
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不再看他一眼。我知道,这步棋很险。但对付陈建军这种犟驴,
不下猛药不行。我必须在他心里,把我和李鬼的信任度,拉到两个极端。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门外李鬼还在不甘心地叫骂,
和陈建军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我赌他对我这个新媳妇的好奇和重视,胜过对兄弟的盲从。终于,
我听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不是下炕,而是……他躺下了。
一股带着热汗和肥皂味的阳刚气息,从背后将我笼罩。“俺不去了。”他闷闷地说,
“前途没了可以再挣,媳妇没了,俺……俺就真没了。”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成了。第一步,保住了。门外的李鬼骂骂咧咧地喊了一阵,见里面始终没动静,也觉得没趣,
最后撂下一句“陈建军你给老子等着”,悻悻地走了。世界终于清净了。我转过身,
面对着陈建军。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一半在明,一半在暗,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有疑惑,
有探究,但更多的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后怕。“秀兰,你……你咋知道张主任不管图纸?
”他还是问出了口。我总不能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吧?我眨了眨眼,身体往他那边挪了挪,
几乎贴在了他身上,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爹告诉我的。
”我爹是隔壁村小学的校长,读过书,有些见识,拿他当挡箭牌最合适不过。“我爹说,
城里工厂规矩大,一个萝卜一个坑,让我嫁过来之后多看多学,
别傻乎乎的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他还说,越是上赶着在你面前称兄道弟的,越要小心,
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专门等你‘报恩’呢。”这番话,半真半假。我爹确实叮嘱过我,
但绝没有这么直白。可对于此刻的陈建军来说,这番来自“文化人”岳父的提点,
简直是金玉良言,正好能解释我今晚的“反常”。他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眼神里的怀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敬佩。“还是爹有文化,看得透。
”他憨憨地挠了挠头,“俺就是个粗人,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所以啊,
”我顺势攀上他的脖子,吐气如兰,“以后多听媳妇的话,保你吃香的喝辣的。现在,
能干点正事了吗?老公?”最后两个字,我说得又软又媚。陈建军的身体瞬间就炸了。
他那双常年抡大锤、拧螺丝的大手,有些不知所措地放在我腰上,
滚烫的温度几乎要将我的睡衣烫出个洞。“秀兰……”他声音沙哑,像是一头被困住的野牛。
“嗯?”我故意拖长了尾音。下一秒,天旋地转。他一个翻身,将我牢牢地压在了身下,
那双黑亮的眼睛里,像是燃起了两簇火。“俺听你的。”03第二天一早,
我是被院子里王兰那标志性的、夹子一样的声音给吵醒的。“建军哥,你起来没呀?
我给你们熬了小米粥,趁热喝点吧!”我睁开眼,身边的陈建军已经不见了。
炕上还留着他的余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又满足的气息。我动了动,
只觉得浑身像是被大卡车碾过一样,酸软无力。陈建军这个糙汉,看着老实,到了炕上,
简直就是个不知疲倦的打桩机。不过,这种感觉,踏实。我披上衣服,
撑着发软的腿走到门口,一拉开门,就看见王兰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衫,
手里端着个搪瓷碗,正“含羞带怯”地看着刚洗漱完的陈建军。阳光下,
她那张涂了雪花膏的脸白得有些不自然,扭着腰,梗着脖子,自以为风情万种,在我看来,
却像一只急于开屏的野鸡。她看见我,立刻堆起“亲热”的笑容:“哎呀,秀兰妹子,
你可算起来了。昨晚累坏了吧?快来,兰姐特意给你们熬的粥,快趁热喝了补补身子。
”她一边说,一边故意把“累坏了”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眼神还意有所指地在我俩之间来回打转,那副样子,
就好像她昨晚躲在咱们床底下听了一夜似的。我心里冷笑。上一世,她就是这样,
打着“好闺蜜”的旗号,对我嘘寒问暖,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的男人,
觊觎我的一切。陈建军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耳根又红了,接过碗,瓮声瓮气地说:“谢了。
你……你咋来这么早?”“我这不是担心你们嘛,”王兰说着,就想往屋里走,
“昨晚李鬼哥那么喊,你都没出去,是不是秀兰妹子不让你去啊?妹子你也真是的,
建军哥的前途要紧啊,你怎么能……”“站住。”我淡淡地开口,拦在了门口。
王兰的脚步骤然停下,有些错愕地看着我。**在门框上,懒洋洋地抬起眼皮,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王兰姐,我家门槛高,怕绊着你。有话就在院子里说吧。
”这话里的疏离和敌意,傻子都听得出来。王兰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勉强挤出个笑容:“秀兰妹子,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咱俩谁跟谁啊……”“咱俩不熟。
”我直接打断她,“另外,我男人昨晚为什么没出门,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事,
好像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吧?”我这话一出,院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陈建军惊讶地看着我,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而王兰,
那张精心伪装的“亲切”面具,终于裂开了一道缝。“秀兰!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我是一片好心!我是怕建军哥被领导穿小鞋!”她拔高了声音,眼眶一红,
委屈得像是受了天大的欺负。这演技,不去唱样板戏都屈才了。“穿小鞋?”我笑了,
走下台阶,踱到她面前,压低声音,“那也比戴绿帽子强吧?王兰姐,你说对不对?
”王兰的瞳孔骤然收缩!她做贼心虚,自然明白我话里有话。“你……你胡说八道什么!
”她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了。“我胡说了吗?”我歪着头,一脸无辜,
“我就是打个比方。毕竟,谁家好人会大半夜去敲人家新婚夫妻的门,
又会一大清早端着粥来打探消息呢?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和我家建军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我们村管这种行为叫‘挖墙脚’,
不知道你们城里,管这个叫什么‘新潮’?”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
狠狠地扇在王兰的脸上。我就是要当着陈建V的面,把她那层虚伪的皮,一点一点地扒下来!
陈建军就算再迟钝,此刻也听出了不对劲。他皱着眉头,看着王兰的眼神里,
已经带上了一丝审视和怀疑。“够了!”王兰终于绷不住了,
她把手里的碗重重地往地上一摔,尖叫道,“赵秀兰!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要不是我,建军哥能看得上你?”图穷匕见了。
这才是她的真心话。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我没理她,而是转向陈建军,眼眶一红,
委屈地撇了撇嘴,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建军……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看上我,是因为她?
”我这副泫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样子,和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我,判若两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陈建军一下子就慌了神,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睛,心疼得不行,
连忙摆手:“不是!秀兰你别听她胡说!跟她没关系!是俺……是俺自己相中你的!
”他急得满头大汗,指着王兰,怒道:“王兰!你在这胡咧咧什么!赶紧给俺媳妇道歉!
”“道歉?凭什么!”王兰彻底撕破了脸,“陈建军,你就是个睁眼瞎!
我哪点比不上这个乡巴佬?我……”“你闭嘴!”陈建军一声怒吼,打断了她。
这是我两辈子以来,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胸膛剧烈起伏,眼睛瞪得像铜铃,
指着门口:“你给俺滚!以后别再来俺家!俺们家不欢迎你!”王兰被他吼得一愣一愣的,
大概是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对自己“有求必应”的老好人,会突然变得这么绝情。
她恨恨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淬了毒的刀子。“好……好!陈建军,赵秀兰,
你们给我等着!”撂下狠话,她哭着跑了。一场大戏,终于落幕。我看着陈建军,
继续保持着委屈巴巴的表情,用手指轻轻戳了戳他的胸膛。“老公,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啊?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陈建军看着我这副样子,心都快化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放在嘴边哈着气,急切地解释:“瞎说!俺媳妇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谁都比不上!
那个王兰,她就是……就是吃饱了撑的!”看着他笨拙又真诚的模样,
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行了,信你了。”我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踮起脚,
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这是奖励你的。”陈建军瞬间石化,脸红得像猴**。我心情大好,
转身准备回屋,却一眼瞥见邻居张大妈正扒在墙头,看得津津有味。我心里一动,
一个计划悄然成形。我故意拔高了声音,对着屋里喊:“哎呀,建军,你快来看看,
这是啥呀?”陈建军不明所以地跟着我进了屋。
我指着炕上那一小块已经干涸的、暗红色的印记,
一脸“天真”地问:“这是不是就是娘说的‘落红’啊?她说有了这个,
就说明我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了。”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墙外的张大妈听个一清二楚。
陈建军的脸“轰”的一下,彻底熟透了。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赵秀兰,
是清白完整的!我看以后王兰和李鬼那两个**,还怎么泼我“破鞋”的脏水!
04搞定了王兰,接下来就该轮到李鬼了。果不其然,陈建军去上班没多久,
李鬼就找上门来了。他没敢进院子,就扒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瞧,看见我一个人在家,
才换上一副自以为和善的笑容走了进来。“弟妹啊,建军上班去了?”他搓着手,
笑得一脸褶子。“有事?”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头也没抬,直接怼了回去。
李鬼被噎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那个……弟妹,昨晚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那也是为了建军好,张主任他……”“打住。”我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冷冷地看着他,
“李鬼,你要是真为了建军好,就该知道新婚之夜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你倒好,
半夜三更跑来砸门,安的什么心,你自己不清楚吗?”李鬼没想到我一个新媳妇,
敢这么跟他说话,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弟妹,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跟建军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倒是你,
刚嫁过来就挑拨我们兄弟感情,你安的又是什么心?”他开始给我扣帽子了。
我笑了:“挑拨?李鬼,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就你干的那些事,还需要我挑拨?
你敢不敢跟我去厂里,当着张主任的面,咱仨对峙一下,
看看昨晚到底是不是他让你来叫人的?”李鬼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他当然不敢。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就是他编的。“你……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他开始耍横,
声音也大了起来,似乎想用气势压倒我,“厂里的事,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是不懂。
”我点点头,慢条斯理地擦干手,“我只懂一个道理,谁想让我男人不好过,
我就让谁全家都不好过。”我的眼神很平静,但李鬼却像是被毒蛇盯上一样,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你……你威胁我?”“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往前一步,逼近他,
压低声音,“李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王兰那点破事。你们俩一个图我男人的岗位,
一个图我男人的房子。打的好算盘啊。”上辈子,陈建军死后,李鬼顶替了他的岗位,
还和王兰火速搞在了一起,住进了我们这间婚房。这些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
李鬼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惊恐和慌乱,他没想到,自己隐藏得最深的秘密,会被我一口叫破。
“你……你血口喷人!”他色厉内荏地吼道。“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有数。
”我盯着他的眼睛,“我劝你,离我男人远点。不然,下一次,我就不是跟你在这废话了,
我会直接去厂纪委,举报你跟王兰乱搞男女关系,作风有问题。”在这个年代,
“作风问题”四个字,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切。李鬼的冷汗“刷”地就下来了,他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想不通,这些事,我一个刚从村里来的女人,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王兰那个蠢货说漏了嘴?他越想越有可能,心里把王兰骂了个狗血淋头。
“算……算你狠!”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敢再多说一句,转身就想溜。“等等。
”我叫住他。他僵硬地转过身。我从兜里掏出两毛钱,丢在他脚下。“这是什么意思?
”他愣住了。“赏你的。”我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毕竟,
让你白白演了这么一出大戏,我也过意不去。拿着钱,去买包烟抽,
就当是我给你和你那好‘妹妹’王兰的封口费了。记住,以后见了我家建军,绕道走。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李鬼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死死地攥着拳头,
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但他不敢发作。我的手里,握着他的死穴。他最终还是弯下腰,
捡起了那两毛钱,然后头也不回地,夹着尾巴跑了。看着他狼狈的背影,我心里一阵快意。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李鬼这种人,是不会轻易善罢甘she的。但没关系,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这辈子,我有的是时间和他们慢慢玩。傍晚,陈建军下班回来,
情绪明显有些低落。“咋了?在厂里受气了?”我给他端上一杯晾好的白开水,关切地问。
他灌了一大口水,才闷闷地说:“李鬼今天一天都没搭理我,见了我就躲。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秀兰,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他还是那个重情义的傻大个。
我心里叹了口气,柔声说:“你没错。有句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心里要是真有你这个兄弟,就不会干出那种事。倒是你,今天在厂里,
有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风言风语?”陈建军想了想,一拍大腿,“还真有!
今天车间里都在传,说李鬼跟咱们车间那个新来的实习生王兰,好像……好像关系不一般。
有人看见他俩昨天晚上在厂子后门的小树林里拉拉扯扯的。”我心里一动。来了。
邻居张大妈的嘴,果然比广播还快。我昨天故意在院子里和王兰吵架,
又故意让张大妈听到“落红”的事,就是为了制造舆论。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王兰是个不检点的女人,而我赵秀兰,是清白的。这样一来,
就算以后她和李鬼再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也没人会信了。“建军,”我握住他的手,
认真地看着他,“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从今天起,离李鬼和王兰远一点。
他们俩,不是好人。”陈建军看着我清澈又坚定的眼睛,虽然心里还有些困惑,
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俺听你的。”05日子看似恢复了平静。陈建军听了我的话,
在厂里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李鬼。李鬼大概是被我抓住了把柄,也不敢再主动招惹,
两人在车间里,几乎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王兰,更是好几天都没了踪影。
我估计她是被我的话和厂里的流言蜚语给吓住了,暂时不敢再出来作妖。但我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以李鬼和王兰的性格,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
我必须赶在他们下一次出手前,为我们这个小家,找到一条更稳妥的后路。这个年代,
虽然还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但南方的风已经吹了过来,个体户的政策也渐渐放开。
光靠陈建军在厂里那点死工资,想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应对未来的风险了。
我把我的想法跟陈建军说了。“做生意?”他听完我的话,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秀兰,你没发烧吧?咱都是工人家庭,祖祖辈辈就没出过一个商人。
这……这不是投机倒把吗?是要被抓起来的!”他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什么投机倒把,
现在政策都变了,叫‘个体经营’。”我耐心地跟他解释,“建军,你想想,
你修车的技术那么好,厂里谁不夸你?咱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开个修车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