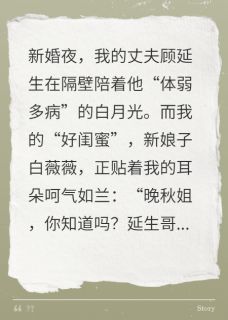新婚夜,我的丈夫顾延生在隔壁陪着他“体弱多病”的白月光。而我的“好闺蜜”,
新娘子白薇薇,正贴着我的耳朵呵气如兰:“晚秋姐,你知道吗?延生哥胸口那颗朱砂痣,
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笑了,抄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将里面的酒泼了她一脸。闹剧?不,
这只是个开始。在这个人人都想端稳铁饭碗的八零年代,顾延生这盘棋下得太大,
大到差点连我都骗了过去。01“林晚秋!你被举报在高考中作弊,录取资格取消!即刻起,
下放到三车间劳动改造!”喇叭里的声音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当着全厂人的面,将我凌迟。
我死死盯着台上那个亲手把我送进地狱的男人,我的未婚夫,顾延生。
他穿着崭新的干部服,胸口别着大红花,身旁站着今天真正的新娘——厂长的女儿,
白薇薇。三天前,他还拉着我的手,信誓旦旦地说要娶我,今天,
他就亲手撕毁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娶了别人。
周围的指指点点像无数根钢针扎在我身上。“看,就是她,勾搭顾科长不成,就去考大学,
结果还是个作弊的!”“长得跟个狐狸精似的,心思就是不正!”我的视线越过人群,
和顾延生对上。他的眼神冷得像冰,没有半分往日的温情。他身边的白薇薇,
却朝我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那张平日里纯洁无瑕的脸上,此刻写满了得意。我懂了。
这是一场早就设计好的阴谋。“我不服!”我冲开人群,疯了似的想冲上台,“顾延生!
你告诉我!为什么!”两个高大的联防队员死死架住我,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往外拖。
我挣扎着,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顾延生!你会后悔的!”他终于动了。他迈开长腿,
一步步朝我走来。全场都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他走到我面前,蹲下身,
用那双我曾无比迷恋的眼睛看着我,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林晚秋,别闹了,很难看。
”他的手,那双曾经能精准修好任何进口机器的、骨节分明的手,
此刻却整理了一下我的乱发,动作轻柔,眼神却冰冷。
一个微小的、硬硬的东西被塞进了我的掌心。我被拖走了,
像一团破布被扔进了机器轰鸣、油污遍地的三车间。刺鼻的机油味让我一阵干呕。
车间主任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他斜着眼打量我,吐了一口浓痰:“新来的?
别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就金贵,到了这儿,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去,
把那堆废料清了!”我攥紧了手心里的东西,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那是一枚小小的、被磨得看不出图案的铜扣子。是我送给顾延生的第一件礼物,
我亲手从我爹的旧军装上剪下来,给他缝在了贴身的衣物里。他把它还给我了。
是在宣告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吗?不,不对。我摊开手掌,借着昏暗的灯光,
才发现铜扣子下面,压着一张被叠成细条的纸。上面只有三个字,和一串数字。
“别信他。735。”他?他是谁?是厂长?还是另有其人?735又是什么意思?
我脑子飞速旋转,还没等理出头绪,身后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哎呀,晚秋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白薇薇穿着一身鲜亮的红色连衣裙,与这肮脏的车间格格不入。
她身后跟着几个女工,都用看好戏的眼神看着我。“听说你被分到这儿了,
我跟延生哥特地来看看你。”她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延生哥说了,你虽然犯了错,
但毕竟相识一场,让我们多‘照顾照顾’你。”她特意加重了“照顾”两个字。
我冷冷地看着她,不说话。我知道,她今天的表演才刚刚开始。果然,她走到我面前,
弯下腰,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你知道延令哥为什么选我吗?
因为我爸是厂长。而你呢?你那个当臭老九的爹,早就自身难保了。”我的心猛地一沉。
“哦,对了,”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精致的手帕,
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灰尘,“延生哥还说,他从来没碰过你,嫌你脏呢。”话音刚落,
她脚下一滑,直直地朝旁边堆满零件的铁桶倒去。“啊!”一声凄厉的尖叫,
响彻整个车间。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几个冲上来的女工死死按住。“林晚秋!
你竟敢推薇薇!”“黑心肝的毒妇!自己倒霉了还想害人!”白薇薇躺在地上,
崭新的连衣裙上蹭满了油污,额角磕破了,流下一缕刺眼的鲜血。她梨花带雨地看着我,
眼睛里却藏着一丝得意的狠毒。我知道,我被算计了。从我踏进这个车间开始,
就掉进了她挖好的另一个坑里。就在这时,车间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响起:“都住手。”是顾延生。他来了。
02顾延生逆着光走进来,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径直走到白薇薇身边,将她扶起,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半分迟疑。“延生哥,我好怕……”白薇薇抽泣着,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
躲进他怀里。“没事了。”顾延生拍了拍她的背,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那一刻,
车间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脏一寸寸裂开的声音。我攥紧了手里的铜扣,
那冰冷的触感,让我保持着最后一分清醒。“顾科长,是林晚秋推的薇薇!我们都看见了!
”一个女工抢着邀功。“对!她就是嫉妒薇薇嫁给了你!”顾延生抬起头,
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像在看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甚至还带着几分厌恶。
“林晚秋,”他开口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看着他,忽然就笑了。
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说不是我,你信吗?”他沉默了。这沉默,
比任何指责都更伤人。“好,很好。”我点点头,抹掉眼泪,站直了身体,
“既然顾科长认定是我,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是要扣我工资,还是把我送去联防队,
悉听尊便。”我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显然让他有些意外。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说:“从今天起,三车间的卫生,归你一个人包了。
什么时候干不完,什么时候不准下班。”说完,他便扶着白薇薇,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
转身离去。白薇薇靠在他怀里,回头给了我一个无声的口型:跟我斗?我站在原地,
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才缓缓松开几乎要嵌进肉里的拳头。一个人打扫整个车间,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这是要往死里整我。可我脑子里,却反复回想着那张纸条。
“别信他。735。”第一个“他”,指的应该是厂长,白薇薇的父亲,白建国。
那么第二个“他”呢?顾延生刚才那番做派,不就是在让我“别信他”吗?他是在演戏?
演给谁看?735……735……这串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一边机械地扫着地上的油污和铁屑,一边苦苦思索。我们厂里,
跟735有关的……是机床型号?还是什么零件编号?“喂,新来的!
”车间主任的破锣嗓子打断了我的思索,“磨蹭什么呢!天黑之前扫不完,你就睡在这儿吧!
”我没理他,继续埋头干活。就在我清理一个废弃的储物柜时,
我的手碰到了一个松动的铁皮。我心里一动,用力一掰,铁皮后面,
竟然藏着一个老旧的铁饭盒。我打开饭盒,里面没有饭,只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我翻开笔记本,瞳孔猛地一缩。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一些日期和数字,
看起来像是账本,但又有些奇怪。每一笔记录后面,都跟着一个“白”字。白建国!
我立刻想到了这个名字。这是他的黑账!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立刻将笔记本塞进怀里,
用脏兮兮的工服盖好。就在这时,我忽然注意到笔记本的封皮内侧,
印着一串几乎被磨掉的编号。——735。原来是这个意思!顾延生给我的数字,
是这个储物柜的编号!他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东西的?我强压下心头的狂喜和震惊,
继续打扫。临近下班,我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另一个标着“735”的旧零件箱。
里面除了一堆废铁,还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拿起书,很沉。我翻开,
书页中间被掏空了,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台小巧的……收音机?不,比收音机更精密。
这年头,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我把它藏进怀里,心脏砰砰直跳。顾延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我那重病在床的父亲还没睡,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我给他喂了药,
回到自己那间漏风的小屋。我锁好门,拿出笔记本和那台奇怪的机器。我研究了半天,
才发现那不是收音机,而是一台小型的磁带播放机,里面还有一盘磁带。我戴上耳机,
按下了播放键。一阵滋滋的电流声后,一个被刻意压低的声音传了出来。
是顾延生的声音。“晚秋,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你或许会恨我,但请你相信我。
你的高考被人顶替,不是意外。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人重新翻出来,也不是偶然。
”“这一切,都和白建国有关。他想拿到纺织厂和钢铁厂合并后新厂区的技术改造项目,
而你父亲是最大的阻碍。他手里,有白建国贪污挪用公款的证据。”“我娶白薇薇,
是为了接近他,拿到他真正的账本。你手里的那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需要时间。
”“委屈你了。但是,只有我站得够高,才能保护你。等我。”录音很短,
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摘下耳机,整个人都僵住了。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
原来是这样。他不是不爱,他是爱得太深。他用自己的前途和名声,
为我铺了一张巨大的保护网,而我却在网上,像个傻子一样对他嘶吼,怨恨他。顾延生,
你这个**!你这个天底下最大的傻瓜!我擦干眼泪,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不,
我不能只让你一个人战斗。第二天,我主动找到了车间主任。“王主任,
听说车间里那台从德国进口的‘卡尔’纺纱机坏了很久了,一直没人能修好?
”王主任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怎么?你一个扫地的,还想修机器?别说你,
就是厂里那几个老技术员,对着那堆洋文说明书都头大。”我笑了笑,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复杂的零件图。“或许,我可以试试。
”我父亲是留洋归来的工程师,我从小耳濡目染,加上我自己争气,德语和机械原理,
我懂。这台机器的图纸,我早就研究透过。王主任看着图纸,眼睛都直了。
他虽然不懂技术,但也能看出这图纸的专业。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你……你真的行?
”我没有回答,只是拿起工具,走到了那台落满灰尘的庞然大物面前。我知道,
这是我的机会。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林晚秋,不是一个只能扫地的废物。我要站起来,
站到足够高的地方,站到能与顾延生并肩的位置。而我不知道的是,车间二楼的窗户后面,
一双深邃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
03“卡尔”纺纱机是厂里几年前花大价钱从西德引进的宝贝,自从半年前出了故障,
就成了块废铁。厂里请了好几拨专家,都束手无策。现在,我这个“作弊犯”,
竟然说要修好它。整个车间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围过来看热闹。“她疯了吧?
那机器全是洋文,她看得懂吗?”“估计是想出风头,等下有她哭的。”“就是,
装模作样!”我充耳不闻,脑子里只有那张烂熟于心的图纸。我拧开螺丝,拆开外壳,
复杂的线路和精密的齿轮立刻暴露在我眼前。问题出在一个核心传动轴的磨损上。
这是一个设计缺陷,需要一个特殊的垫片来校正。我抬起头,
对还在发愣的王主任说:“王主任,我需要一块厚度0.3毫米的铜皮,还有一把精钢锉刀。
”王主任下意识地就想拒绝,但看到我专注而自信的眼神,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去!
给她拿!”半个小时后,一个崭新的、完全由手工打磨出来的垫片,出现在我手中。
我深吸一口气,将垫片小心翼翼地安装进去,然后重新组装好机器。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走到电闸前,看着王主任。他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我合上电闸。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后,
沉寂了半年的“卡尔”纺纱机,发出了平稳而有力的轰鸣声。“动了!真的动了!
”“天呐!她真的修好了!”整个车间瞬间沸腾了!王主任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你…你叫什么名字?”“王主任,
我叫林晚秋。”我平静地说道。从今天起,这个名字,将不再与“耻辱”挂钩。
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工厂。第二天,我还没到车间,
厂部的一纸调令就下来了。我被调入了技术科,成了技术科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技术员。
我搬离了那个充满油污的三车间,走进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那些曾经对我指指点点的同事,现在看到我,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小林师傅”。我知道,
这是我为自己赢得的尊重。晚上,我再次戴上耳机,听着那段熟悉的录音。这一次,
我的心里不再是委屈,而是充满了力量。顾延生,你看,我没有让你失望。
我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悄悄调查白建国的黑料。我发现,
厂里好几项原材料的采购价都高得离谱,而供应商,
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一个叫“宏发贸易”的皮包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法人,
是白建国的小舅子。我将这些线索一一记下,等待着时机。这天,白薇薇又来了。
她不再是那副高高在上的胜利者姿态,而是带着几分戒备和试探。“林晚秋,你别得意。
”她在我办公桌前站定,“你以为进了技术科,就能怎么样?延生哥的心,还是在我这儿。
”我头也没抬,继续画着我的图纸。“是吗?那他怎么天天睡在办公室,连家都不回?
”最近厂里都在传,顾科长为了工作,废寝忘食,是青年才俊的楷模。只有我知道,
他是在躲着她。白薇薇的脸瞬间白了。“你胡说!”她尖叫道,
“延生哥那是为了厂里的项目!”“哦?是为了项目,
还是为了躲一个连他胸口有几颗痣都数不清的枕边人?”我放下笔,抬眼看她,
笑得云淡风轻。这句话,精准地踩在了她的痛处。她和顾延生,根本就是假结婚。“你!
”她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白薇薇,”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
直视着她的眼睛,“别再来招惹我。你那点小把戏,在我这里,不够看。”我身上的气场,
让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顾延生走了进来。
他看到我们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你们在干什么?
”白薇薇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的表情,跑到他身边:“延生哥,
我……我只是想来看看晚秋姐,可她……”“她怎么了?”顾延生打断她,
目光却落在我身上。那眼神深处,藏着一丝我能读懂的担忧。我心里一暖,
但面上依旧不动声色。“没什么,”我拿起桌上的图纸,“我只是在和顾夫人,
探讨一下技术问题。”我故意加重了“顾夫人”三个字。顾延生的嘴角似乎抽动了一下。
他从我手中拿过图纸,看了一眼,眼中露出一丝赞许。“这个改进方案不错,很有想法。
”他公事公办地评价道,“下班后,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们详细讨论一下。”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了,从头到尾,没再给白薇薇一个眼神。白薇薇的脸,青一阵白一阵,
精彩极了。她死死地瞪着我,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我却觉得无比痛快。下班后,
我如约来到科长办公室。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门。“进。”我推门进去,
看到顾延生正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他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有些落寞。
“图纸带来了吗?”他没有回头。“带来了。”我将图纸放在他桌上。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顾延生,”我终于还是没忍住,
开口叫了他的名字,“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告诉我全部的计划?”他转过身,
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晚秋,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只要记住,保护好自己。
”“我怎么保护自己?”我有些激动,“你知不知道我……”“我知道。”他打断我,
一步步向我走来,“我都知道。你修好了‘卡尔’,进了技术科,怼走了白薇薇。
你做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他的声音里,带着骄傲。“但是,还不够。
”他走到我面前,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白建国这棵树,根扎得太深,想要连根拔起,
我们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武器。”“什么武器?”他没有回答,而是忽然伸出手,
将我拉到了他怀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熟悉的、淡淡的烟草味。
“别动,”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有人在看。”我的心猛地一跳。顺着他的目光,
我看到对面办公楼的窗帘后面,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是白建薇薇的人。“晚秋,
”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致命的诱惑,“配合我。”下一秒,他低下头,
吻住了我。04这个吻,不带任何情欲,只有冰冷的、试探的意味。我浑身僵硬,
脑子里一片空白。几秒钟后,他松开了我,但手依然紧紧地箍着我的腰。
“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会嫉妒,会发疯。”他对着我的唇,一字一句地说,
声音却不大,刚好能让可能存在的窃听器捕捉到。这句潜台词,是在告诉我,他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在乎我。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他是在故意演戏给白薇薇,或者说,
是给白建国看。他要让白建国相信,他对自己这个“情敌”怀恨在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潜伏下去。我的心,又酸又胀。“顾延生,你**。”我咬着牙,
低声骂了一句,眼眶却红了。“我知道。”他用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
眼神里满是歉意和心疼,“再忍一忍,很快就结束了。”说完,他松开我,
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科长派头。“这个方案,晚上回去再完善一下,明天早上交给我。
”“是,科长。”我低下头,掩去眼中的情绪。我拿着图纸,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心情久久无法平复。顾延生的那个吻,像一枚烙印,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思考他那句“更有力的武器”到底是什么。
白建国的黑账,我已经有了一部分。但要扳倒他,光有这些还不够。
我需要一个能让他无法翻身、一击致命的证据。机会,很快就来了。几天后,
厂里要组织一次技术骨干的培训,地点在省城。为期一周。带队的人,是顾延生。而我,
作为技术科的新秀,自然也在名单之列。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省城之行,会是关键。
出发那天,白薇薇来送顾延生。她当着所有人的面,为他整理衣领,柔声嘱咐,
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顾延生全程面无表情,只是在上车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读懂了他眼神里的信息:万事小心。到了省城,我们住进了省**招待所。
安顿好之后,顾延生召集我们开会,布置了培训期间的任务。会议结束后,
他单独留下了我。“今天晚上,会有人给你送一样东西。”他压低声音说,“拿到东西后,
立刻离开招待所,去火车站,买最早的一班车回来。”“那你呢?你怎么办?
”我紧张地问。“我自有安排。”他看着我,眼神无比凝重,“记住,东西拿到手,
一刻也不要停留。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晚上,
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午夜十二点,房门被轻轻敲响了。我从猫眼里看出去,
外面站着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看不清脸。我的心跳到了极致。我打开一条门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