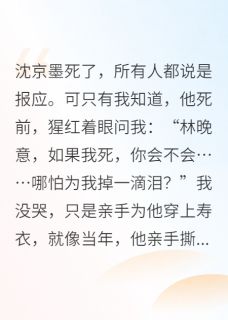沈京墨死了,所有人都说是报应。可只有我知道,他死前,猩红着眼问我:“林晚意,
如果我死,你会不会……哪怕为我掉一滴泪?”我没哭,只是亲手为他穿上寿衣,就像当年,
他亲手撕碎我的嫁衣一样。可没人知道,午夜梦回,我摸着腰后那道狰狞的疤,撕心裂肺。
那只曾为他一人舞动的玉蝴蝶,终究是碎了。而我,
也早就不是那个爱穿白裙子的纺织女工了。01我和陈烨的婚事,是整个红星纺织厂的喜事。
他将攒了三年的工资换成了一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而我,
则将我妈传给我的那匹“的确良”白布,熬了七个通宵,做成了最时兴的连衣裙。领证那天,
陈烨骑着他的二八大杠,载着我穿过厂区,风将我的白裙子吹得像蝴蝶的翅膀。
我搂着他的腰,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可就在拐进民政局胡同口的那一刻,
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像一头沉默的野兽,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车窗缓缓摇下,
露出一张过分英俊却毫无温度的脸。“林晚意?”他开口,声音像数九寒冬的冰凌子。
我愣住了,全厂没人不认识这张脸——新上任的厂长,沈京墨。京城来的高干子弟,留过洋,
手腕铁血,来厂里三个月,就让三个倚老卖老的老车间主任卷铺盖滚蛋了。
他是高悬在天上的人,怎么会认识我这个小小的纺织女工?陈烨把我护在身后,
紧张地扶了扶眼镜:“厂长,您……您有事?”沈京墨的视线却越过陈烨,像淬了毒的钩子,
死死地钉在我身上。更准确地说,是钉在我被风吹起的裙摆下,若隐若现的腰窝处。那里,
有一块蝴蝶形状的胎记。小时候,我妈总说,这是观音菩薩点化的“玉蝴蝶”,是福气。
可此刻,我只觉得那块皮肤像被烙铁烫过一样,**辣地疼。“跟我走。”沈京墨的语气,
不是商量,是命令。“厂长,我们……我们正要去领证。”我攥紧了陈烨的衣角,
鼓起勇气说。“领证?”他轻笑一声,那笑意却比冰还冷,“我批准了吗?
”这句嚣张至极的话,让周围看热闹的工友都倒吸一口凉气。在八十年代,厂长就是天,
可没人敢这么霸道。陈烨气得脸都红了:“厂长,婚姻自由,这是国家……”“国家?
”沈京墨打断他,慢条斯理地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
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灰尘的皮鞋,“在这个厂里,我就是规矩。”他推开车门,
一步步向我走来。他的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哒、哒”声,每一下,
都像踩在我的心上。他没再看陈烨一眼,只是走到我面前,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林晚意,给你两个选择。一,现在跟我走,
你弟弟的病我来治,陈烨的工作我来安排。二……”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惨白的脸上,
一字一句,残忍无比。“——你信不信,我能让你们一家,明天就从这个城市消失,让陈烨,
一辈子在锅炉房里挖煤,活得不如一条狗。”02我选择了第一条路。或者说,我没得选。
我那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弟弟,就是我妈的命,也是我的命门。
我看着陈烨被沈京墨的司机“请”走,他猩红着眼睛,嘶吼着我的名字,却被死死捂住嘴。
我不敢回头,怕一看,就再也迈不动腿。伏尔加轿车里,暖气开得很足,熏得我头晕。
沈京墨就坐在我身边,他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冷杉味道,可我却觉得,那是毒药的气息。
车子没有开往医院,而是停在了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洋楼前。这是厂里分给厂长的住所,
像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下车。”他命令道。我机械地跟着他走进那栋房子,
里面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和恐惧。锃亮的地板,柔软的沙发,还有墙上我看不懂的油画。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倒了两杯红酒,将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尝尝。”我摇了摇头。
他也不勉强,自顾自地抿了一口,然后走到我身后。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温热地洒在我的后颈,让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把裙子……脱了。”他的声音很轻,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屈辱、愤怒、恐惧,
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猛地站起来,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衣服:“沈京幕!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他笑了,绕到我面前,伸出手指,轻轻挑起我的下巴。他的指尖很凉,
像蛇的信子。“我想看看,那只蝴蝶。”他的眼神,不像在看一个人,
而像在欣赏一件觊觎已久的珍宝。那种**裸的占有欲,让我不寒而栗。
“我弟弟……”我声音颤抖地问。“放心,”他松开我,坐回沙发上,
姿态优雅地交叠起双腿,“我已经安排了全市最好的心外科专家,明天就给他手术。
至于陈烨,我让他去子弟校当老师了,清闲,体面。”他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像一张网,将我牢牢困住。“为什么……是我?”我还是不明白。沈京墨看着我,
眼神幽深得像一潭不见底的湖水。他没有回答,而是说了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我母亲,
是苏绣大师。她最喜欢绣的,就是蝴蝶。”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了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
“可惜,她眼睛熬坏了,再也拿不起针了。”我愣住了,不明白他提这个做什么。“她总说,
最美的蝴蝶,不是绣出来的,而是天生的。有灵性,会呼吸,独一无二。”他站起身,
一步步逼近我,目光灼热得像要将我烧穿,“林晚意,我要你这只蝴蝶,
为我一个人……跳舞。”我终于明白了。他不是要我的人,他是要我腰后那块胎记。他把我,
当成了一件可以满足他和他母亲病态癖好的收藏品。这一刻的羞辱,比他强迫我脱衣服更甚。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沈厂长,”我抹掉眼泪,一字一句地说,
“我这只蝴蝶,很贵的。你……买得起吗?”这是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反抗。
用他最在乎的“交易”,来刺痛他。沈京幕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捏住我的手腕,
力道大得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林晚意,别给脸不要脸。”他凑到我耳边,声音阴冷,
“你最好记住,你不是在跟我谈价钱。你,以及你的一切,从现在开始,都是我的。
”03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第二天,整个纺织厂都传遍了。说我林晚意嫌贫爱富,
为了攀高枝,在领证当天甩了未婚夫陈烨,爬上了新厂长的床。流言蜚语像刀子,
将我割得遍体鳞伤。可我什么都不能说。弟弟的手术很成功,
沈京墨把他安排在了最好的单人病房。我妈来送饭时,拉着我的手,
一边哭一边笑:“晚意啊,多亏了沈厂长,不然小杰他……”我看着妈鬓角的白发,
把所有的苦涩都咽了回去,笑着说:“妈,沈厂长是好人。”好人?我心里冷笑。
好人会把一个女人当成玩物囚禁起来吗?从那天起,我搬进了那栋小洋楼。
沈京墨给了我最好的物质生活,法国进口的连衣裙,闻所未闻的护肤品,
甚至还有专门的阿姨照顾我的饮食。但他有一个规矩。每天晚上,
我都要换上他指定的真丝睡裙,趴在床上,露出腰后的那只蝴蝶。而他,会坐在床边,
开着一盏昏暗的台灯,一看就是一整夜。他从不碰我,却用那种审视艺术品的目光,
一寸寸地凌迟我。我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金丝雀,被困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我试过反抗。
我故意弄脏裙子,故意在他看我的时候背过身去。结果,他当着我的面,
一个电话打到人事科,让陈烨从子弟校老师,变成了冲洗厕所的清洁工。那天,
我第一次跪下来求他。“沈京墨,我求你,放过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他用那双擦过皮鞋的手帕,
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动作温柔得近乎残忍。“晚意,我说过,别惹我生气。”他俯下身,
在我耳边说,“你乖乖的,他才能好好的。懂吗?”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我终于明白,
我不是金丝雀,我只是他用来牵制陈烨,牵制我所有在意的人的……人质。
而我腰后的那只蝴蝶,就是我的罪证。我开始变得沉默,顺从。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有一天,他带回来一台进口的录像机和一台彩电,
这在当时是稀罕物。他放了一盘录像带,是国外的芭蕾舞《天鹅湖》。他对我说:“学会它。
”于是,我每天对着电视,笨拙地模仿着里面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学这个,
直到我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在他面前跳起那段舞蹈时,
他眼中迸发出的那种近乎疯狂的迷恋,让我瞬间明白了。他要的,是一只会跳舞的蝴蝶。
他甚至请来了专业的老师教我。那个老师是个上了年纪的白俄女人,她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同情。有一次,趁着沈京墨不在,她悄悄对我说:“姑娘,你腰后的那块胎记,
和他母亲的,一模一样。”我如遭雷击。“他母亲……?”“是的,”白俄老师叹了口气,
“他的母亲,曾经是上海滩最红的**,艺名就叫‘玉蝴蝶’。后来,她为了他的前程,
自杀了。”原来,是这样。我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我只是他用来复活他母亲记忆的……一个容器。我腰后的蝴蝶,不是我的,
是属于那个叫“玉蝴蝶”的女人的。这个认知,比任何羞辱都让我感到恶心。那天晚上,
沈京墨回来时,我第一次主动对他笑了。我穿着最漂亮的裙子,为他跳了一支舞。
在他看得最入迷的时候,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对准了腰后的那只蝴蝶。“沈京墨,
”我笑着流泪,“你不是喜欢它吗?我毁了它,好不好?
”04刀尖离皮肤只有一厘米的时候,沈京墨扑了过来。他夺下我手里的刀,
力道大得几乎要将我的手腕折断。那双总是古井无波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惊恐和暴怒。
“林晚意!你疯了!”他低吼,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没疯!”我歇斯底里地朝他喊,
“是你疯了!沈京墨,你这个变态!我不是你妈!我不是!”“啪!”一个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我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耳朵里嗡嗡作响,嘴角尝到了一丝腥甜。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沈京墨看着自己发红的手掌,似乎也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
空气凝固得像要结冰。良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对不起。”对不起?
我捂着**辣的脸,笑了。我觉得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可笑的笑话。他毁了我的人生,
囚禁我的自由,践踏我的尊严,现在,他打了我一巴掌,然后说对不起?“沈京墨,
”我抬起头,直视着他,“你杀了我吧。”与其这样半死不活地当一个容器,一个替身,
我宁愿死。他看着我眼中决绝的死志,脸色变得惨白。他后退了一步,
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从那天起,他变了。他不再逼我跳舞,
不再用那种审视的目光看我腰后的蝴蝶。他甚至开始尝试……讨好我。
他会从京城带回最新鲜的荔枝,因为我无意中说过一句想吃。他会笨拙地学着给我做饭,
结果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他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地坐在床边,用一种我看不懂的,
混杂着痛苦和挣扎的眼神看着我。他甚至,允许我出门了。虽然身后总跟着他的司机,
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我去了医院看我弟弟。他恢复得很好,
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看到我,他开心地扑过来:“姐!
你什么时候也给我找个像沈厂长那样的姐夫啊?他又帅又有本事!”我摸着他的头,
笑得比哭还难看。离开医院,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纺织厂的子弟校门口。放学**响起,
孩子们像快乐的小鸟一样冲出校门。然后,我看到了陈烨。他瘦了,也黑了,
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他身边站着一个很清秀的女老师,正笑着跟他说些什么。陈烨的脸上,
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他有了新的生活,而我,
也该认命了。我转身准备离开,却被那个女老师叫住了。“请问,您是林晚意吗?
”我点了点头。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我:“这是陈烨……让我转交给你的。”我接过那封信,信封上,是陈烨熟悉的字迹,
写着“晚意亲启”。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回到那栋小洋楼,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拆开了那封信。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晚意,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不要怕,等我。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等我有了足够的能力,我一定会带你走。——爱你的,陈烨。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将墨迹晕开。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从来没有怪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把信死死地攥在胸口,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