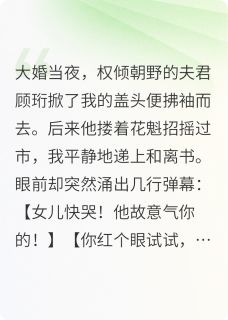顾珩开始每日都来。
他不再穿那身象征权柄的深色官袍,只着一身素色的常服。脸色依旧苍白憔悴,走路时右腿明显有些跛,是那夜长跪留下的伤。他总是在清晨或傍晚,安静地出现在我的房门外,并不进来,只是隔着门扉站一会儿。有时端着一碗他亲手熬的、散发着古怪气味的药膳,有时捧着一束带着露水的、不知从哪里采来的野花。
他不再说那些强势的命令,也不再试图靠近。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一个犯了错等待宽恕的孩子。偶尔,他会隔着门,用嘶哑干涩的声音,低低地说一句:“药……趁热喝。”或是,“花……开得很好。”
我从未回应过。药膳冷透了,便让李妈妈端走。野花,也任由它们在门外枯萎。
他似乎也并不期待我的回应。只是日复一日,固执地出现,沉默地放下东西,然后沉默地离开。那跛着脚、在晨光或暮色中踽踽独行的背影,透着一种沉重的孤寂。
【他好像……真的在悔改?】
【膝盖伤得不轻吧?每天还来……】
【晚晚还是不肯原谅他啊……】
【换我我也不原谅!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弹幕消失了,这些念头却在我心底无声地划过。
日子在一种诡异的僵持中滑过。冬雪消融,庭院里那株老梅树竟也抽出了几丝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