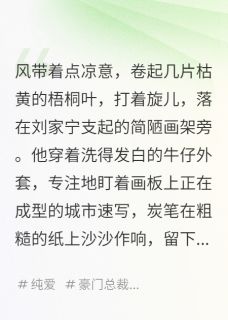风带着点凉意,卷起几片枯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刘家宁支起的简陋画架旁。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专注地盯着画板上正在成型的城市速写,
炭笔在粗糙的纸上沙沙作响,留下利落的线条,
勾勒出桥下匆忙车流的动感与远处钢筋森林的冷硬轮廓。指尖染上了炭黑,
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年轻俊朗的侧脸滑下,没入干净的衣领。周围行人步履匆匆,
偶尔有人瞥一眼这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帅气青年,目光里带着好奇或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就在这时,一道影子斜斜地覆盖了他的画纸,带来一阵若有似无的冷冽暗香,
像雪后松林里悄然绽放的玫瑰。这香气霸道地侵入了他画笔营造出的世界。
刘家宁下意识地抬起头。逆着光,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双鞋。尖头,细高跟,深酒红色的麂皮,
包裹着纤巧的足踝,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精致与昂贵。视线顺着那流畅的腿部线条向上,
是剪裁极佳的黑色阔腿裤,垂坠感十足,走起路来应该如流云拂过。再往上,
是一件质感极好的米白色羊绒衫,勾勒出成**性丰润饱满却不失挺拔的曲线。最后,
他的目光撞进了一双眼睛里。女人看起来四十出头,岁月似乎对她格外宽容,
只在她眼角留下了几道极淡、却更添韵味的细纹。她的五官明艳大气,下颌线条清晰,
此刻微微扬着,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审视。乌黑浓密的长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落鬓边,柔和了那份锐利。她的眼神很特别,像深不见底的寒潭,
此刻正毫不避讳地、带着强烈兴趣地打量着刘家宁,以及他面前的画板。那目光里的热度,
与周遭微凉的空气格格不入,让刘家宁握着炭笔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她身后半步,
跟着一个穿着得体西装、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像一道沉默的影子。“画得不错。
”女人开口,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奇特的沙哑磁性,像天鹅绒滑过耳膜。
她直接忽略了刘家宁画板上“街头写生,50元一幅”的小纸牌,目光依旧锁在他脸上,
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有没有兴趣,换个地方画点别的?”刘家宁愣了一下,
还没完全消化这突如其来的搭讪。他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纸牌,以为对方没看清价格。
“呃…女士,我这里是写生,画风景或者街景的,五十块一幅。”他解释道,声音清朗,
带着点刚毕业学生的青涩。女人——顾晚舟,轻轻笑了一声,
那笑声像细碎的冰珠落在玉盘上,清冷又悦耳。她上前一步,高跟鞋踩在天桥的水泥地上,
发出清脆笃定的声响。那阵冷冽馥郁的香气瞬间变得更为清晰,几乎将刘家宁包围。
她微微倾身,视线掠过画板上城市的天际线,
最终落回刘家宁因专注而微微绷紧的年轻面容上。“风景?”她重复着,尾音微微上扬,
带着一丝慵懒的嘲弄。“再好的风景,看久了也乏味。
”她伸出一根保养得宜、涂着深豆沙色指甲油的手指,
指尖轻轻拂过画纸上那片他精心描绘的、代表远处高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区域。
那指尖几乎要碰到纸面,却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画我。”顾晚舟抬眸,目光像带着钩子,
直直刺入刘家宁的眼底。“一小时,五千块。”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五千?一小时?刘家宁的呼吸猛地一窒,握着炭笔的手指骤然收紧,
指节泛白。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冲击力不亚于迎面撞上一堵墙。他需要这笔钱,迫切地需要。
刚毕业,工作室的租金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各种账单雪片般飞来,
压得他喘不过气。天桥上风吹日晒一整天,运气好也就挣个两三百。五千一小时,
简直是天降横财。然而,没等他从这巨大的诱惑中回过神来,顾晚舟的下一句话,
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烧红烙铁,瞬间蒸腾起灼人的水汽。“画不好……”她红唇微启,
吐出的字眼带着一种慢条斯理的残忍和……难以言喻的暧昧。那只刚刚拂过画纸的手,
优雅地抬起,食指的指尖,带着微凉的触感,极其缓慢地、带着某种不容抗拒的意味,
轻轻划过刘家宁因紧张而上下滚动的喉结。“……就肉偿。”她的声音压得更低,
那沙哑的磁性在耳畔放大,像毒蛇吐信,带着冰冷的、令人战栗的诱惑。“轰”的一声,
热血猛地冲上头顶。刘家宁的脸颊、耳朵,甚至脖颈,瞬间红透,像煮熟的虾子。
喉结被那微凉的指尖触碰的地方,仿佛被烙铁烫了一下,**辣的,又带着奇异的麻痒感,
电流般窜遍全身。他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那三个字在疯狂回荡:肉偿?肉偿!
身后的西装男人——顾晚舟的助理陈锋,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眼神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无奈,仿佛对自家老板这种惊世骇俗的行径早已习以为常。
天桥上的风似乎也停滞了,远处城市的喧嚣被无形的屏障隔绝。
刘家宁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震耳欲聋。他猛地后退一步,
脊背撞在冰冷的桥栏杆上,才找回一丝逃离那致命气息的喘息空间。
他几乎是狼狈地避开了顾晚舟那极具穿透力的目光,胸腔剧烈起伏,
试图平复那几乎要破膛而出的心跳。“我…我……”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发紧,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拒绝?五千块一小时,是他无法抗拒的数字。答应?
那“肉偿”的威胁,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让他本能地感到恐惧和……一丝隐秘的、连自己都不愿深究的悸动。
顾晚舟看着他这副惊慌失措、面红耳赤的模样,眼底的笑意更深了,
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兴味。她好整以暇地收回手,
仿佛刚才那个惊世骇俗的提议和触碰只是他的一场幻觉。“怕了?”她挑眉,
语气带着一丝挑衅,“还是觉得……姐姐我不值这个价?”她微微侧头,
午后的阳光恰好勾勒出她完美的下颌线和天鹅般优雅的颈项。刘家宁深吸一口气,
冰凉的空气灌入肺腑,强行压下了那份翻江倒海般的混乱。他抬起头,
眼神里还残留着未褪尽的红晕和慌乱,但深处却渐渐凝聚起一种豁出去的倔强。他需要钱。
他没得选。至于那所谓的“肉偿”……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只当是对方恶劣的玩笑。“画!
”他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字,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弯腰,
几乎是粗暴地开始收拾地上散落的炭笔、橡皮,动作带着一种发泄般的用力。
他不敢再看顾晚舟,只是闷头把画板折叠起来,夹在腋下,炭笔盒紧紧攥在另一只手里,
指关节捏得发白。“很好。”顾晚舟满意地点点头,仿佛只是完成了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交易。
她转身,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再次响起,清脆而笃定,
朝着天桥下停着的那辆线条流畅、宛如黑色猎豹的劳斯莱斯幻影走去。陈锋无声地跟上。
刘家宁抱着自己简陋的“家当”,硬着头皮,脚步有些虚浮地跟在后面。
昂贵的真皮座椅触感柔软得不可思议,车内弥漫着与顾晚舟身上如出一辙的冷冽暗香,
只是更加醇厚浓郁。他紧贴着车门坐着,尽可能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目光投向窗外飞逝的街景,心却像被丢进了滚筒洗衣机,疯狂地旋转、撞击。
车子最终驶入一个被高大乔木和森严安保环绕的高档别墅区。穿过雕花的黑色铁艺大门,
停在一栋线条简洁现代、通体玻璃幕墙的三层别墅前。
巨大的落地窗映着天空的流云和庭院里精心修剪的绿植,冰冷,奢华,
与他那个连窗户都吱呀作响的简陋工作室天壤之别。顾晚舟率先下车,径直走向大门。
智能门锁无声滑开。刘家宁抱着画板,像个误入巨人国的孩子,迟疑地跟了进去。
玄关宽敞明亮,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水晶吊灯璀璨的光影。
空气里只有恒温空调系统运转的细微声响,空旷得令人心慌。“二楼,画室。
”顾晚舟头也没回,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面上,发出空旷的回音。刘家宁循着声音,
踏上旋转楼梯。二楼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实木门虚掩着。他推开门。巨大的空间豁然开朗。
整面墙的落地玻璃将庭院景色尽收眼底。光线极好,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松节油和颜料的气味。
画材的架子、随意摆放但价值不菲的雕塑……一切都彰显着主人对艺术的投入和不菲的身家。
这像一个专业画家的圣地,而不是他想象中“富婆”附庸风雅的地方。
顾晚舟已经姿态闲适地坐在了房间中央一张宽大的、铺着深灰色绒布的欧式复古单人沙发里。
她踢掉了那双价值不菲的高跟鞋,赤足踩在柔软的地毯上。然后,在刘家宁惊愕的目光中,
她极其自然地抬起一条腿,优雅地搭在了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动作间,
黑色阔腿裤柔顺的布料微微滑落,露出一截光滑细腻的小腿。更让刘家宁瞳孔骤缩的是,
那细腻的肌肤之上,覆盖着一层薄如蝉翼、泛着细腻哑光的浅灰色**。
那**的质感高级至极,完美地包裹着优美的腿部线条,从圆润的脚踝,到纤细的小腿肚,
一路延伸,隐没在垂坠的裤管深处。光线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落,
在那层薄纱般的**上流动,仿佛为那双腿镀上了一层朦胧而诱惑的光晕。
她甚至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那被**包裹的足弓绷出一个更加诱人的弧度,
深酒红色的脚趾甲在浅灰的**下若隐若现。“开始吧,小画家。”顾晚舟单手支颐,
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沙发扶手上,指尖在绒布上轻轻点着。她看向已经完全僵住的刘家宁,
红唇勾起一抹摄人心魄的弧度,眼神慵懒,却又带着洞穿一切的玩味。“时间,可是很贵的。
”那目光,那姿态,那双腿……像一张无形的、由欲望和金钱编织的网,
瞬间将刘家宁牢牢罩住。他抱着冰冷的画板,指尖却像被那浅灰色**上的微光灼伤般滚烫。
喉结不受控制地再次剧烈滚动了一下,额角的汗珠重新渗出。
他几乎是同手同脚地走到画架前,机械地撑开架子,夹上画纸。手指颤抖得厉害,
试了几次才勉强把炭笔夹稳。画笔落向纸面,每一次线条的勾勒都异常艰难。
顾晚舟的存在感太强了。她慵懒地斜倚在沙发里,像一株在暗夜中盛放的、带着剧毒的花。
那被浅灰色**包裹的双腿,如同最精密的仪器,准确无误地干扰着他的视线和神经末梢。
他强迫自己聚焦于她的面部轮廓——那明艳的五官,带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
眼角淡淡的细纹非但不显老态,反而平添了难以言喻的风情。
她的眼神始终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直勾勾地落在他身上,
仿佛在欣赏他每一次因紧张而导致的细微失误。画室里异常安静,
只有炭笔摩擦画纸的沙沙声,以及他自己越来越响、越来越乱的心跳声。汗水顺着额角滑下,
痒痒的,他却不敢抬手去擦。空气里松节油的气味混合着她身上那股冷冽的暗香,
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奇异的氛围。时间从未如此漫长而煎熬。不知过了多久,
仿佛一个世纪。刘家宁终于停下了笔。画纸上,顾晚舟的神韵被捕捉到了六七分。
成**性的风韵与眼底那份掌控一切的慵懒野**织在一起,背景被他虚化处理,
更突显人物本身强大的气场。特别是那双腿的线条,流畅而充满张力,
浅灰色**的质感被他用炭笔的深浅和细腻的排线艰难地表现了出来,
带着一种含蓄又惊心动魄的诱惑力。这几乎是他超水平发挥的作品。他放下炭笔,
手心全是汗,后背的T恤也湿了一片。他垂着眼,不敢看沙发上的女人,
声音带着完成巨大任务后的虚脱感:“画…画好了。”顾晚舟这才慢悠悠地起身,
赤足踩在厚实的地毯上,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她停在画架前,目光落在画纸上,
久久没有移开。画室里安静得只剩下两人细微的呼吸声。刘家宁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好?
还是不好?那“肉偿”的威胁像阴云再次笼罩下来。终于,顾晚舟伸出手指,不是指向画作,
而是轻轻拂过画纸上她腿部线条被**包裹的部分。
指尖在炭笔留下的细腻阴影上停留了片刻。她抬眼,看向刘家宁,眼神深邃难辨,
红唇微启:“很好。”刘家宁紧绷的神经猛地一松,几乎要瘫软下去。然而,
这口气还没完全呼出,就见顾晚舟优雅地从随身的手包里拿出一个鳄鱼皮支票夹,
抽出一张空白支票。她拿起画架旁边一支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钢笔,
龙飞凤舞地签下名字和金额——正是承诺的五千块。
就在刘家宁的目光被那张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支票吸引时,
顾晚舟做了一个让他大脑再次宕机的动作。她双手捏住那张薄薄的支票,指尖用力。
“嘶啦——”清脆的裂帛声在寂静的画室里格外刺耳。
那张承载着刘家宁急需的五千块的支票,在她纤细有力的手指间,瞬间被撕成了两半,
然后又被随意地叠在一起,再次撕裂。碎片像雪片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光洁的地板上。
刘家宁的瞳孔骤然收缩,震惊、不解、愤怒和被戏耍的屈辱感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你!
”他猛地抬头,声音因为极度的情绪而变调,双眼死死瞪着眼前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
顾晚舟却对他的愤怒视若无睹。她甚至向前逼近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呼吸可闻。
那股强大的、带着侵略性的冷香再次将刘家宁包裹。她微微仰头,
看着这个因为愤怒而胸膛起伏、眼睛发红的年轻男人,红唇边绽开一个近乎妖异的笑容。
那笑容里,带着猎人捕获心仪猎物后的绝对掌控和志在必得。“钱?”她嗤笑一声,
尾音带着轻蔑的钩子。涂着深豆沙色的指甲,轻轻点在了刘家宁剧烈起伏的胸口。
指尖下的肌肉瞬间绷紧,如同岩石。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
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敲打在刘家宁的耳膜上,也狠狠撞击着他摇摇欲坠的世界观:“跟我结婚。
”顾晚舟的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目光锐利如刀,穿透他所有的防备和伪装。“我的钱,
”她顿了顿,红唇勾起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就都是你的。
”云城顶尖的“云端”旋转餐厅顶层,巨大的落地玻璃墙外,是璀璨如星河倾泻的城市夜景。
悠扬的小提琴声在空气中流淌,水晶吊灯折射出迷离的光晕。侍者穿着笔挺的制服,
无声地穿梭于铺着洁白桌布、点缀着新鲜玫瑰的餐桌之间。然而,这极致奢华浪漫的布景,
却掩盖不住空气中弥漫的异样气氛。一道道目光,或明或暗,
带着毫不掩饰的探究、鄙夷、嘲弄,像细密的针,从四面八方刺向靠窗那张位置绝佳的餐桌。
刘家宁坐在柔软的丝绒座椅上,背脊挺得笔直,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身上穿着顾晚舟为他准备的昂贵手工西装,剪裁完美,衬得他肩宽腰窄,
年轻的俊朗被勾勒得淋漓尽致。可这身行头非但没带来安全感,
反而像一件沉重的、不合身的戏服,勒得他喘不过气。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目光的灼烫——那些来自云城上流圈子、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的目光。
他们窃窃私语,嘴角挂着心照不宣的讥诮弧度,眼神在他和身旁的女人之间来回扫视,
传递着同一个无声的讯息:看,那就是顾晚舟新得手的“小玩意儿”。“啧,
顾总真是好兴致,这‘小画家’看着是挺养眼,就是不知道画技值不值这个价码?
一个穿着亮片晚礼服、妆容精致的女人用不大不小、恰好能让周围人听清的音量“感慨”着,
尾音拖得长长的,满是轻佻。旁边立刻有人低笑附和:“画技?
我看是‘睡服’的功夫值钱吧?顾总这‘慧眼识珠’的本事,咱们是学不来喽!
”“听说连工作室都是顾总给盘下来的?啧啧,软饭硬吃到这份上,也是个人才。
”“可不是嘛,攀上顾总这棵大树,少奋斗几百年啊!就是不知道骨头还剩几两重?
”那些低语如同毒蛇,嘶嘶地钻进刘家宁的耳朵。他握着冰凉的高脚杯杯脚,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杯中的红酒微微晃动,映着他紧绷的下颌线条和眼底压抑的怒火。
屈辱感如同冰冷的潮水,一波波冲击着他的神经末梢。他真想站起来,
把杯中酒泼向那些刻薄的嘴脸,或者干脆掀了桌子,让这虚伪的盛宴见鬼去!就在这时,
一只微凉的手轻轻覆盖在他紧握杯脚的手背上。那触感细腻柔滑,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
瞬间像一道微弱的电流,击散了他胸中翻腾的戾气。刘家宁猛地侧头。顾晚舟正含笑看着他。
她今晚穿了一条酒红色丝绒长裙,深V领口恰到好处地展露着成**性优美的锁骨线条。
灯光下,她明艳的五官愈发显得光彩照人,眼角那几道细纹在笑意中舒展开,
带着阅尽千帆的从容和一种近乎霸道的温柔。她仿佛完全没听见那些恶意的议论,或者说,
她听见了,却根本不屑一顾。“别理那些苍蝇,家宁。”她的声音不高,
带着惯有的慵懒沙哑,却清晰地盖过了周围的杂音。
她的手指在他手背上安抚性地轻轻拍了拍,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掌控感。“尝尝这个鹅肝,
刚从法国空运来的,配这里的松露酱,味道很特别。”她说着,
姿态优雅地用银匙舀起一小块点缀着黑松露的鹅肝,动作自然地将勺子递到了刘家宁的唇边。
那姿态,亲昵得近乎宣告**。带着诱哄,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