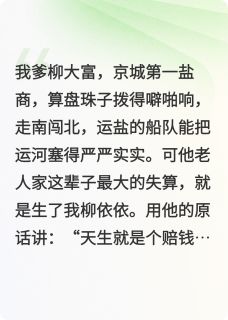我爹柳大富,京城第一盐商,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走南闯北,
运盐的船队能把运河塞得严严实实。可他老人家这辈子最大的失算,就是生了我柳依依。
用他的原话讲:“天生就是个赔钱货!”琴棋书画?样样都摸过,先生教《女诫》,
我在底下偷偷描花样子;抚琴拨弦,弦没断,
倒是隔壁家黄狗被我的“宫商角徵羽”嚎得直挠墙。账册算盘?更别提了,
家里金山银山堆着,我爹想让我学学看账,我对着那密密麻麻的数字,眼皮子直打架,
最后在账册空白处画了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我娘拿着我的大作叹气:“闺女,咱长得好看,
这就是顶顶大的福分。”我爹气得胡子直翘,把算盘拨得震天响:“好看?好看能当盐吃?
能换银子?”可您猜怎么着?我这张脸,还真就值了大钱——国公府托人上门提亲来了!
提起这国公府,听着是顶顶风光的门第,祖上跟着太祖爷打过江山,
挣下这份世袭罔替的爵位。可到了如今,里子早就空了,就是个徒有其表的空壳子,
全靠着祖上攒下的那点薄田和几间半死不活的铺子勉强支撑着门面。更要命的是,
他们要嫁过来的这位小公爷顾言蹊,那是京城里出了名的“散财童子”,头号纨绔!
斗鸡走狗、掷骰子押宝、喝花酒听小曲儿……除了正事,那是样样精通,样样舍得往里砸钱。
媒人把庚帖递到我爹手里时,他正为一批压仓的盐发愁。展开一看,
“顾言蹊”三个字赫然在目。我爹那双精明的眼睛瞬间亮了,猛地一拍大腿,
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哈哈哈!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啊!
这可不就是‘赔钱货’配‘赔钱货’,绝配!这门亲事,应了!应了!”我娘在一旁,
眼泪珠子断线似的往下掉:“我的依依啊!你这是要跳火坑啊!
那顾小公爷的名声……我的儿啊……”她抱着我,哭得肝肠寸断,
仿佛我明日就要去赴那龙潭虎穴。我倒是看得开,一边给我娘擦眼泪,
一边慢悠悠地剥着碟子里新炒的松子:“娘,您哭什么呀?嫁谁不是嫁?再说了,我打听过,
那顾言蹊……”我顿了顿,把一粒饱满的松仁丢进嘴里,嚼得嘎嘣脆,“长得可好看了!
您想啊,好看不能当盐吃,可对着那张脸,吃饭是不是也能多吃两碗?下饭!”成亲那日,
国公府排场不小,八抬大轿,吹吹打打,
把我从柳家抬进了那朱漆大门、石狮子把守的深宅大院。拜天地时,
旁边那高挑身影带着一股浓重的酒气,脚步虚浮,拜下去时差点一头栽倒,
惹得观礼的宾客一阵低笑。熬到入了洞房,头上的红盖头压得脖子酸。我端坐在喜床上,
听着那踉踉跄跄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带着更浓的酒气扑了进来。眼前骤然一亮,
盖头被猛地掀开。我抬眼,正对上一张脸——剑眉斜飞入鬓,鼻梁挺直,
唇色因为醉酒显得格外殷红,一双桃花眼此刻迷迷瞪瞪,水光潋滟,
果然担得起“好看”二字。只是他一张嘴,那股子纨绔劲儿就藏不住了。顾言蹊晃了晃脑袋,
努力聚焦看清我,大着舌头就嚷开了:“娘、娘子!嘿嘿…听说…听说你会唱小曲儿?来!
给、给夫君来一段助助兴!”说着就要往我身边凑,酒气熏人。我心底冷笑一声,
面上却堆起一个极其温顺的笑容,捏着嗓子,用能掐出水来的娇滴滴声音开了腔:“一呀摸,
摸到姐姐的头发边……”唱的是坊间最俗艳露骨的《十八摸》,词儿一句比一句露骨,
调子一句比一句缠绵婉转,直往人骨头缝里钻。
顾言蹊那醉醺醺、色眯眯的表情瞬间僵在了脸上,桃花眼瞪得溜圆,
酒意“嗖”地一下散了大半,脸皮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指着我,
舌头都打了结:“你…你你你……你这小娘子!
怎、怎么唱得比……比怡红院的头牌还、还油滑?你……你……”我再也憋不住,
“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前仰后合,头上的珠翠乱颤:“哈哈哈……夫君莫怕!
咱们这不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么?油?咱们这是‘同类’相吸!
”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看着他目瞪口呆、活像见了鬼的表情,
心里那点初入陌生之地的忐忑竟奇异地消散了大半。顾言蹊张着嘴,半晌才缓过神,
自己也跟着“嘿嘿”傻笑起来,一**坐到我旁边,挠了挠头:“同类?嗯…娘子说得对!
同类!有趣!真有趣!”新婚的“下马威”就这么混了过去。第二天清早,
按规矩要去给公婆敬茶。国公夫人,我那新上任的婆婆,穿着绛紫色团花褙子,
端坐在正厅上首的太师椅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整套的翡翠头面,
端着十足的贵妇架子。她接过我奉上的茶,浅浅抿了一口,眼皮都没怎么抬,
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言蹊这孩子,自幼被我们娇惯坏了,性子是跳脱了些,
如今成了家,你身为媳妇,正室夫人,要多规劝,引他走正道,这才是为妻的本分。明白吗?
”我低眉顺眼,双手规规矩矩叠放在身前,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是,儿媳谨记母亲教诲,
定当尽心规劝夫君。”敬完茶出来,在回我们院子的抄手游廊上,正好碰见顾言蹊。
他大概刚起,头发还有点乱,手里正拿着个大肉包子啃得香。
我立刻换上那副温婉贤淑的面孔,把婆婆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学给他听:“夫君,
母亲大人方才说了,你年幼跳脱,让我这做娘子的,要多多规劝于你,引你走正道。
”我眨巴着眼睛,一脸无辜,“你可要听母亲的话呀。”顾言蹊正嚼着包子,闻言差点噎住,
赶紧咽下去,抹了抹嘴,想也没想就含含糊糊地大声回道:“听!当然听!我听娘子的话!
娘子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声音洪亮,顺着风就飘回了正厅。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正厅门口侍立的一个小丫头“哧”地一声赶紧捂住了嘴。
我憋笑憋得肚子一阵阵抽痛,还得强装镇定。顾言蹊浑然不觉,还在那儿傻乐,
把剩下的半个包子一股脑塞进嘴里。后来听小丫头们嚼舌根,
说婆婆当时在厅里气得手直哆嗦,手里的茶盏盖子磕得叮当响。新媳妇进门,
照理说该晨昏定省,立规矩,伺候公婆丈夫。我不。我反其道而行之——陪他玩!放风筝嘛,
得先让它飞起来,线才能慢慢收。顾言蹊爱斗鸡,那是京城纨绔圈子里一顶一的发烧友。
他常去城南的“斗金坊”,每次去都带他那几只精心饲养的宝贝疙瘩,输多赢少,
银子哗啦啦往外流。这日他又要去,我眼睛一亮:“夫君要去斗鸡?带上我!我还没见过呢!
”他有些意外,随即乐了:“娘子也有兴趣?好!同去同去!”到了斗金坊,乌烟瘴气,
人声鼎沸。顾言蹊带的那只“金将军”刚上场就被对手啄得抱头鼠窜,败下阵来,
他气得直跺脚。我摇着团扇,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等他输了银子,垂头丧气时,
我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子,指着场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夫君,你看那只黑羽的,眼神多凶,
爪子多利!我看它准行!”顾言蹊顺着看去,是只毛色油亮、体型健硕的黑羽大公鸡,
眼神确实凶狠。他狐疑:“那‘黑炭头’?看着是凶,可没战绩啊。”“没战绩才好,便宜!
”我笑得眉眼弯弯,“夫君信我一次嘛!”顾言蹊拗不过我,也心疼输掉的银子,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花了五十两把那“黑炭头”买下了。我还不满意,
转头就吩咐跟着的小厮:“去,给我找最好的金箔来,再要一盒上好的胭脂!
”在顾言蹊和周围赌徒们惊愕的目光中,我指挥小厮,
亲手把那黑羽鸡的两只翅膀用薄如蝉翼的金箔细细贴满,鸡冠子用鲜艳的胭脂涂得通红。
原本其貌不扬的“黑炭头”,瞬间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头顶红云的“黑旋风”,
一出场就闪瞎了全场人的眼!“黑旋风”不负其名,果然凶狠异常,
上场就把对手啄得毫无还手之力。顾言蹊看得热血沸腾,拍着大腿叫好。连赢三场,
他正得意忘形,突然,那“黑旋风”一个猛子扎下斗场,直冲旁边观战席!好巧不巧,
我那位平日里不苟言笑、最爱养些名贵鸟雀的公公——最心爱的一只五彩斑斓的大公鸡腿上!
“哎哟我的‘锦凤凰’!”公公心疼得大叫一声,脸都白了。“黑旋风”得胜归来,
昂首挺胸,顾言蹊却傻了眼。国公爷气得胡子一翘一翘,指着顾言蹊就要发作。
我赶紧上前一步,福了福身子:“父亲大人息怒!是儿媳不懂事,见那鸡勇猛,
一时兴起才……儿媳回头定寻一只更好的‘锦凤凰’赔给您!”顾言蹊看看我,
又看看气得发抖的老爹,再看看那只还在得意踱步的“黑旋风”,
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继而拍着巴掌大声叫好:“好!啄得好!娘子!
你这‘黑旋风’,威武!太威武了!”他笑得前仰后合,全然不顾老爹那锅底一般黑的脸色。
斗鸡风波刚平息没几天,顾言蹊那帮狐朋狗友又撺掇着去“醉仙楼”喝花酒。
吾吾地跟我说:“娘子…那个…王兄他们约我…去…去谈点事儿……”我放下手里的话本子,
抬眼看他,了然一笑:“哦?谈事?醉仙楼谈事,想必是风雅之事?夫君稍等。
”我转身进了里间,片刻后出来,已是一身月白锦袍,玉带束腰,
头发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起,活脱脱一个俊俏风流的少年郎。
顾言蹊看得眼睛都直了:“娘子…你…你这是?”“走啊,”我摇开一柄折扇,
潇洒地扇了两下,“夫君去谈风雅事,为妻自然要随行保护,顺便也开开眼界。
”我冲他眨眨眼,嘴角噙着一丝促狭的笑。顾言蹊拗不过我,
只得带着我这个“俊俏小兄弟”一同前往醉仙楼。那老鸨一见我,眼睛都看直了,
扭着腰就迎了上来,手里的香帕子直往我脸上拂:“哎哟喂!这是哪家的俊俏小公子哥儿?
眼生得很呐!快请进快请进!”她那双精明的眼睛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满是惊艳。
我“啪”地一声甩开折扇,挡开她的手,另一只手从袖中掏出一锭足有十两的雪花银,
“当啷”一声丢在老鸨手里,下巴微扬,学着纨绔子弟的腔调,
声音故意压得低沉:“少废话!把你们这儿最红、曲子唱得最好的姑娘,给我这位兄长叫来!
好生伺候着!唱好了,爷重重有赏!”我指了指旁边一脸尴尬、手足无措的顾言蹊。
老鸨捧着银子,乐得见牙不见眼:“哎哟!公子您真真是大方!放心放心!红袖!红袖姑娘!
快出来伺候贵客!”那位叫红袖的头牌果然袅袅娜娜地来了,抱着琵琶,嗓音婉转。
顾言蹊被朋友们簇拥着,又被红袖姑娘殷勤劝酒,几杯黄汤下肚,很快又找不着北了。
他喝得东倒西歪,满脸通红,最后竟抱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肩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委屈的孩子:“娘子…娘子…你对我…太好了…呜呜…比亲娘对我都好……”我强忍着笑意,
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一样,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夫君开心就好。来,再喝一杯?”这场面,把顾言蹊那帮朋友看得目瞪口呆,想笑又不敢笑。
这事儿不出半天,就传到了婆婆耳朵里。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请”到了祠堂。
祠堂里阴森肃穆,列祖列宗的牌位在烛光下森然排列。婆婆端坐在太师椅上,脸色铁青,
手里的佛珠捻得飞快,几乎要擦出火星子来。“柳氏!”她声音尖利,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你身为国公府嫡媳,正室夫人!看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事?!纵容夫君流连花街柳巷!
还跟着女扮男装胡闹!成何体统!国公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
你这是要把言蹊彻底带进沟里吗?!”我垂着头,盯着自己绣鞋上的缠枝莲纹,
等她咆哮完了,才怯生生地抬起眼,长长的睫毛扑闪着,
眼神清澈无辜得像小鹿:“母亲息怒。儿媳…儿媳只是想着,夫君他心里苦闷,
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儿媳跟着,也是怕他喝多了没人照料……再说,”我声音放得更轻,
带着点恰到好处的天真,“夫君私下里常跟儿媳说,母亲您年轻那会儿,
可是最爱看皮影戏的,还偷偷打赏过那演‘小生’的俊俏男戏子呢,
说那嗓子清亮得……”“住口!”婆婆猛地一拍椅子扶手,霍然站起,
保养得宜的老脸瞬间涨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脖子根,指着我的手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
“你…你…你胡说什么!放肆!简直放肆!给我跪下!抄《女诫》!抄不完十遍,不准起来!
好好反省你的妇德!”我老老实实跪下,丫鬟搬来小几,铺开纸笔。
祠堂里静得只剩下我磨墨的声音。我提起笔,
装模作样地开始抄写:“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抄了没两行,
眼皮就开始打架。昨夜陪着顾言蹊闹腾,本就没睡好,祠堂里又安静,烛光又暖,不一会儿,
我就握着笔,头一点一点地打起瞌睡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身上的薄毯滑落在地。揉揉眼睛,往案上一看,愣住了。那抄了一半的《女诫》纸上,
后半部分竟然已经写满了字!只是那字迹……歪歪扭扭,横不平竖不直,
像是一群喝醉了酒的蚂蚁在纸上爬出来的痕迹,比我的狗爬字还要惨不忍睹。我愕然抬头,
只见祠堂门口探进半个脑袋,正是顾言蹊。他见我看他,赶紧缩回去,片刻后又探出来,
冲我挤眉弄眼,压低声音:“娘子…快抄完了吗?我…我帮你抄了点……字是丑了点,
心意到了就行!母亲那边…我替你说好话去!”说完,像只偷了腥的猫,一溜烟跑了。
看着纸上那“蚂蚁搬家”似的字迹,再看看门口消失的身影,
我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心里某个角落,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软软的。
这纨绔,倒也不是全无心肝。日子就在我陪着顾言蹊“胡闹”中,像指缝里的流沙,
不知不觉滑过了三个月。京城里的风言风语又换了新词儿:“听说了吗?小公爷娶了媳妇,
非但没收敛,反倒疯得更厉害了!”“可不是!他那媳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夫唱妇随,
绝配!”连我爹都坐不住了,托人悄悄给我带话:“闺女,要是实在过不下去,就回娘家!
爹养你一辈子!咱不受那窝囊气!”我提笔回信,只有寥寥数字:“爹,安心。您不懂,
女儿这是在放风筝呢。”没错,风筝。
顾言蹊就是那只不安分、总想往高处蹿、往远处飞的风筝。线嘛,自然得攥在我手里,
但不能攥死了,得让他飞,飞得高高的,才能看清方向,才能……收得回来。
这放风筝的日子看着热闹,底下的暗流却从未停歇。国公府这个空架子,
靠着祖产和一点微薄的俸禄,哪里经得起顾言蹊以前那样流水似的花销?
婆婆明里暗里克扣我的用度,连份例里的胭脂水粉都换成了次品。顾言蹊的月例银子,
更是早就不够他塞牙缝了。他那些狐朋狗友,惯会捧高踩低,见他手头紧,就变着法儿激他。
这日,他又被那群人拉去赌坊“翻本”。结果可想而知,不仅带去的银子输得精光,
还被人哄着,在酒劲上头时,迷迷糊糊签下了一张五百两的欠条,鲜红的手印按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债主就带着打手,大摇大摆地找上了国公府的门。彼时,我正歪在院里的美人榻上,
悠闲地嗑着瓜子,翻着一本新出的话本子。丫鬟秋月急匆匆跑进来,小脸煞白:“少奶奶!
不好了!外面来了几个凶神恶煞的人,说是…说是少爷欠了他们五百两银子!拿着欠条呢!
夫人气得晕过去了,老爷在正厅发火呢!”我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地又嗑开一颗瓜子,
“咔哒”一声脆响,瓜子仁丢进嘴里,细嚼慢咽。等秋月急得快哭出来了,
我才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屑,懒洋洋地起身:“慌什么?五百两银子而已,小意思。
”我径直走回卧房,指着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樟木箱子,“秋月,抬出来。
”那箱子是我的嫁妆之一,沉甸甸的。秋月和小厮合力把它抬到正厅门口。厅里,
国公爷气得脸色发青,婆婆刚被掐醒,靠在椅背上直喘气。顾言蹊垂着头跪在地上,
面如死灰。几个一脸横肉的汉子,正抖着那张欠条叫嚣。我示意小厮打开箱子锁。盖子掀开,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不是寻常的金银细软,
而是一刀刀崭新的、盖着大通钱庄朱红大印的银票!我伸手进去,随意地抓起一大把,
看也不看,朝着那几个债主的方向,“哗啦”一声,就那么轻飘飘地撒了出去。
雪片般的银票纷纷扬扬,落了一地。满厅死寂。那几个凶神恶煞的债主,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贪婪地盯着满地银票,呼吸都粗重起来。国公爷和婆婆也惊呆了,
张着嘴,看着这“银票雨”,说不出话。我拍拍手,仿佛只是掸掉一点灰尘,
声音平淡无波:“点点,五百两,只多不少。拿了钱,滚。再敢踏入国公府一步,
我柳家盐行的护院,可不是吃素的。”柳家盐行护院的剽悍,京城里无人不晓。
债主们如梦初醒,手忙脚乱地趴在地上捡银票,嘴里连声应着:“是是是!谢少奶奶!
谢少奶奶!”捡完钱,夹着尾巴,跑得比兔子还快。厅里只剩下国公府自家人。
顾言蹊依旧跪在那里,头垂得更低了,脖子根都红透了。他没看我,也没看那一地的狼藉,
肩膀微微发抖。那天晚上,顾言蹊破天荒地没出门。我让厨房做了几样清爽小菜,
他食不知味,胡乱扒拉了几口就撂了筷子。我独自在灯下看了会儿账本,起身去院里透透气,
发现他正蹲在院墙角落那片开得正盛的桂花树下,背影缩成一团,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走近,听到细微的啜泣声。他手里正一片一片地揪着落在地上的桂花,
金黄的细碎花瓣沾了他一手。“娘子……”他听到脚步声,没回头,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闷闷地传来,“我…我是不是特别废物?特别…没用?”月光清冷,照着他单薄的背影。
我沉默了一下,没说什么大道理,转身回屋,
片刻后端出一小罐我埋在桂花树下、新启封的桂花酿。我走到他身边,也学着他的样子,
撩起裙摆,不太雅观地蹲了下来,把小小的酒罐递到他面前。“喏,”我声音放得很轻,
“知道是废物就好。喝一口吧,甜的。桂花酿的,喝完睡一觉。明天……”我顿了顿,
看着他沾着泪痕的侧脸,“明天争取变宝贝。”他猛地抬起头,脸上泪痕未干,
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浮木。他接过酒罐,仰头就灌了一大口,
甜润的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混着眼泪。他胡乱抹了一把脸,声音带着豁出去的狠劲:“好!
我喝!我变宝贝!”第二天午后,阳光正好。
我“恰巧”要去城南的铺子看看新到的绸缎料子,“随口”问顾言蹊:“夫君在家也是闲着,
不如陪我去逛逛?听说铺子里新来了一批江南的软烟罗,给母亲做身新衣裳倒是不错。
”顾言蹊眼下还带着点宿醉的青黑,但眼神清亮了许多,点点头:“好。
”国公府在城南有间不大不小的绸缎庄,名为“锦云轩”。地段尚可,但生意一直半死不活。
掌柜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姓李,见我和顾言蹊来了,连忙迎出来,
脸上却堆满了愁苦:“少奶奶,小公爷,您二位来了……唉,愁死人了!”“怎么了李掌柜?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唉!”李掌柜重重叹了口气,把我们引到后头库房,
指着堆积如山的布匹,“您瞧瞧!去年进的这批苏杭细绸,整整三千匹!压在库里快一年了!
花色是去年时兴的,今年没人要了!天气眼看要转凉,再卖不出去,
这库房租金、伙计工钱……小的真是……真是要喝西北风了!”他急得直搓手。
顾言蹊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绸缎,眉头拧成了疙瘩,下意识地挠头:“这…这么多?
这可怎么办?我…我又不会算账,
也不懂卖东西……”他脸上又浮现出那种熟悉的茫然和无措。我看着他犯难的样子,
心里那根弦轻轻拨动了一下。我摊开手,语气轻松,甚至带着点懒洋洋的笑意:“算账?
卖东西?我会啊。”顾言蹊猛地看向我,眼神里带着希冀。我话锋一转,
故意叹了口气:“可我这个人吧,最不耐烦管这些琐碎事,麻烦!算盘珠子拨来拨去,
看得人眼花。夫君,你……”我歪着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点挑衅,
又藏着点不易察觉的鼓励,“想不想学?”顾言蹊愣住了。他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绸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