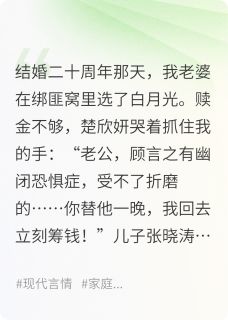结婚二十周年那天,我老婆在绑匪窝里选了白月光。赎金不够,
楚欣妍哭着抓住我的手:“老公,顾言之有幽闭恐惧症,受不了折磨的……你替他一晚,
我回去立刻筹钱!”儿子张晓涛缩在她身后不敢看我,小声补刀:“爸,
顾叔叔教过我钢琴的。”我点头踏进黑暗,以为忍三天就能回家。
再睁眼已是三年后——别墅客厅里摆着顾言之的生日蛋糕,
儿子亲昵地挂在他脖子上:“顾叔叔,许愿你能当我爸爸!
”楚欣妍含笑的目光撞上我满身伤疤,手中红酒杯“啪”地碎裂。后来我放他们自由,
她却疯了般撕碎离婚协议:“张程!那年绑架案真相你不想知道了吗?
”1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的风,带着海城特有的咸腥和一丝若有似无的铁锈味,
钻进废弃教堂破碎的彩绘玻璃窗。我怀里紧紧抱着半人高的沉重旅行袋,
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袋子里装着五百万美金,是我二十年来打拼的江山,
也是我妻儿活命的筹码。几小时前,家里餐桌上还摆着我亲手煎的牛排和醒好的红酒,
桌心放着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是一对定制腕表,表盘内侧刻着“C&Y20yrs”。
楚欣妍当时心不在焉地划着手机,嘴角噙着一抹我看不懂的笑,
只匆匆瞥了一眼盒子:“谢谢老公,放那儿吧。”她甚至没打开。
晓涛则一直摆弄着顾言之送他的最新款游戏机。手机突然响起陌生号码的尖叫,
撕裂了那点勉强维持的温馨假象。此刻,教堂中央的景象像一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视网膜上。楚欣妍昂贵的真丝长裙下摆浸在浑浊的泥水里,
精心打理的卷发凌乱地贴在满是泪痕的脸上。她正张开双臂,
死死护住身后那个西装皱巴巴、脸色苍白的男人——顾言之。我的儿子晓涛,
像一只被吓破胆的小兽,蜷缩在角落的阴影里,双手死死抓着顾言之的裤腿,
小小的身体抖个不停,浅色裤子上甚至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五百万美金,一分不少!
”我把旅行袋用力甩在绑匪头目脚边,沉重的撞击让拉链崩开,
绿油油的钞票瀑布般倾泻出来,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堆成一座小山,“放了我家人!
”头目是个脸上带疤的壮汉,他嗤笑一声,用匕首尖随意地挑起几捆钞票,
对着从破窗射进来的光看了看水印,又捻了捻纸张,眼神陡然变得凶狠。“张总,
”他拖着长音,匕首猛地指向顾言之的咽喉,“你这袋子里,
掺了至少三分之一糊弄鬼的玩意儿啊!看来,
得先切点纪念品给你老婆儿子带回去了……”“不要——!”楚欣妍爆发出凄厉的尖叫,
几乎是扑爬着扑过去,死死抱住绑匪的腿,
精心修剪的指甲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指尖瞬间渗出血珠,“别动他的手!
他的手比他的命还重要!他是钢琴家啊!”她猛地扭头看向我,那双曾经盛满柔情的杏眼里,
此刻只剩下翻涌的绝望和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老公!你信我!假钞…假钞是我换的!
言之…言之他最近投资亏了一大笔,被**逼得快跳楼了!
我…我偷偷拿了一部分赎金帮他填窟窿……我不知道绑匪今天就会动手啊!
我以为还有时间周转的!”一阵裹挟着尘土的风猛地灌进来,卷起几沓散落的假钞,
“啪”地拍在我的脸上。纸张粗糙的触感和那股劣质油墨的味道,混合着楚欣妍刺耳的辩解,
像无数根针扎进我的太阳穴。角落里的晓涛似乎被母亲的情绪感染,
附和:“妈妈…妈妈说要帮顾叔叔渡过难关的…顾叔叔好可怜……”就在这混乱的哭喊声中,
被刀尖抵着咽喉的顾言之,艰难地仰起了他那张让楚欣妍痴迷了二十年的俊脸。
他手腕上那抹冰冷的铂金光泽,
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眼底——那是我去年送给楚欣妍的二十周年礼物,百达翡丽的**款!
此刻,它正牢牢地戴在另一个男人的手腕上!
绑匪头目的狞笑、楚欣妍带着血丝的哭求、晓涛怯懦的附和,还有顾言之腕上那刺眼的反光,
所有声音和画面扭曲成巨大的漩涡,将我拖向窒息的深渊。“张程!
”楚欣妍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冰凉湿滑的手指猛地攥紧我的手腕,
那触感如同毒蛇缠上濒死的猎物,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你…你替言之当一晚人质!
就一晚!好不好?他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被关在这种地方会死的!他真的会死的!
”她的眼泪大颗大颗砸在我的手背上,“我回去!我回去立刻把珠宝、房子都卖了,明天!
明天太阳升起之前,我一定带着真钞来接你回家!我发誓!”她的瞳孔里,
映出的全是顾言之惊恐的脸,没有半分我的影子。晓涛终于从顾言之身后怯怯地抬起一点头,
目光躲闪,不敢与我对视,声音细若蚊呐,
“爸…顾叔叔…顾叔叔他教过我弹《月光》的…他不能有事…”教堂穹顶投下的彩玻璃光影,
在地上流淌,斑驳陆离,像一滩凝固的、肮脏的血。死寂笼罩了所有人。
我看着楚欣妍眼中只对顾言之的担忧,看着晓涛对那个“顾叔叔”的依赖,
看着顾言之在刀锋下那不易察觉的、微微勾起的嘴角。时间仿佛被拉长、凝固。
我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弯下腰,近乎麻木地,将散落在地上的假钞一沓一沓捡起来,
塞回那个巨大的旅行袋里。金属拉链齿咬合的声音,
在空旷死寂的教堂里显得格外刺耳、冰冷。然后,
我听见一个干涩、陌生、仿佛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滚了出来,
砸在冰冷的地面上:“好。”2沉重的铁门带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在我身后轰然合拢。
最后一丝从门缝透进来的、属于外面世界的光线,被彻底吞噬。巨大的声响震落了簌簌灰尘,
扑头盖脸地落下来,呛得我一阵咳嗽。就在那光线彻底消失前的最后一瞬,
我看到的是:顾言之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几乎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楚欣妍和晓涛身上,
被他们半拖半架着往外走。他艰难地回头,目光穿过渐渐闭合的门缝,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在门扉投下的浓重阴影里,他的嘴角,
极其清晰地向上弯起一个微小的、充满胜利和嘲弄的弧度。紧接着,是绝对的黑暗,
和令人窒息的死寂。地窖比一口棺材大不了多少。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尘土味,
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仿佛什么东西腐烂了的甜腥气。墙壁冰冷潮湿,手指摸上去,
是滑腻的苔藓和凹凸不平的霉斑,像一张张扭曲的地图。脚下是坑洼不平的泥地,
渗着冰凉的湿气。唯一的光源,是头顶斜上方一个巴掌大的通风口。每天只有正午时分,
会有一道惨白的光柱,像探照灯一样刺破黑暗,悬浮的灰尘在其中疯狂地舞动,
如同无数濒死的幽灵。
变卖首饰需要时间…处理房产最快也要三天…加上筹现金…”**着冰冷滑腻的墙壁坐下,
用指甲在靠近地面的墙根处,用力刻下第一道深深的划痕。尖锐的疼痛从指尖传来,
带着一丝奇异的清醒。我强迫自己冷静计算着,“最多五天。五天,我就能出去。
”指甲在坚硬的墙壁上一次次划过,留下带着血丝的印记。一天,两天,三天…第七天正午,
当那道光柱再次刺入时,通风口上方传来绑匪戏谑的嗤笑:“哟,张总,还数日子呢?
”半块硬得像石头、爬着霉绿绒毛的面包被粗暴地塞了进来,掉在泥地上,“别数啦!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那情深义重的老婆,报警了!”他的声音充满恶意,
“警察动作挺快嘛,昨天端了我们三个点!啧啧,可惜啊——”“可惜什么?!
”我猛地扑到通风口下方,嘶吼着追问,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可惜啊,
”绑匪拖长了调子,像在欣赏我的绝望,“警察动静太大,惊了蛇!老大发话了,
这票买卖黄了!至于你嘛…嘿嘿,就看你老婆报警的速度快,
还是哥几个送你去见阎王的速度快了!”脚步声渐渐远去,
留下恶毒的笑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我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冰冷的地上。
那半块发霉的面包塞进嘴里,粗糙的碎屑刮着喉咙,带来一阵剧烈的呛咳。
血液疯狂地冲上太阳穴,发出沉闷的轰鸣。报警?楚欣妍报警了?
她难道不知道绑匪最忌讳的就是报警吗?
她是为了逼绑匪放人…还是…为了彻底摆脱我这个累赘?顾言之那张得意的脸在我眼前晃动,
胃里翻江倒海,我趴在冰冷的地上,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第二百天。
通风口再次被堵住,一张揉得皱巴巴、沾着不明污渍的报纸被塞了进来。我颤抖着手,
借着微弱的光线展开。社会版的头条标题像烧红的烙铁烫进我的眼睛——《走出阴霾,
传递大爱:知名企业家楚欣妍女士携子投身公益》。照片上,楚欣妍穿着华贵的晚礼服,
站在慈善晚宴璀璨的聚光灯下,笑容得体,容光焕发。她雪白的脖颈上,
正戴着那串价值连城、本该送去典当行换取赎我的蓝宝石项链!照片的角落,
穿着合身小西装的张晓涛,踮着脚尖,正将一杯香槟递给旁边西装革履、笑容温和的顾言之!
“啊——!”压抑了二百天的绝望、愤怒和被彻底背叛的剧痛,
如同火山般在我胸腔里爆发。我发疯似的撕扯着报纸,用头狠狠撞击着冰冷潮湿的墙壁!
指甲在粗粝的墙面上崩裂,钻心的疼痛传来,温热的血珠顺着指尖流下,一滴一滴,
渗进墙根那些密密麻麻、记录着我无尽等待的刻痕里。黑暗吞噬了我野兽般的嘶吼。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饥饿是永恒的刑罚,胃袋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反复揉捏、灼烧。
为了活命,我学会了舔舐墙壁上渗出的冰冷水珠,捕捉偶尔从通风口掉落的可怜飞虫,
甚至强忍着恶心,吞下爬过脚背的老鼠和面包里蠕动的蛆虫。寒冷像无数根钢针,
日夜不停地刺入骨髓。我用尽一切方法保持清醒和体力:在方寸之地做深蹲和俯卧撑,
搐;强迫自己背诵复杂的商业数据、财务报表;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晓涛刚出生时柔软的小手,
他第一次叫“爸爸”时含糊的声音…这些记忆是支撑我不坠入彻底疯狂的唯一浮木。
第六百个午夜(我早已不再精确计数,但身体对黑暗的恐惧刻入了骨髓)。地窖沉重的铁门,
毫无预兆地发出一声刺耳的、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竟缓缓地被从外面拉开了!
久违的光线,即使是微弱的月光,也像无数根烧红的钢针猛地刺入我的双眼!
剧痛让我瞬间失明,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
一个高大的、穿着黑色紧身衣、蒙着面的身影堵在门口,像一尊来自地狱的杀神。“张程?
”一个冰冷、毫无感情、带着明显电子处理杂音的声音响起。一支乌黑的手枪,
带着死亡的气息,精准地抵上了我的眉心。“有人花钱,买你永远闭嘴。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在对方扣动扳机的电光火石之间,我用尽全身力气向侧面猛扑,
同时狠狠一脚踹向对方下盘!枪口火光一闪,灼热的气流擦着我的耳际呼啸而过,
留下**辣的痛感。“找死!”杀手闷哼一声,显然没料到在如此虚弱状态下我还能反击。
他稳住身形,再次举枪。我抓起地上能抓到的一切——一把混合着泥土和霉斑的砂石,
狠狠砸向他的脸!趁他视线受阻的瞬间,我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猛地撞开他,向着洞开的门外那片未知的、暴雨如注的黑暗荒野,亡命狂奔!
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我单薄的衣物,刺骨的寒意直透骨髓。
身后传来杀手愤怒的咆哮和紧追不舍的脚步声!泥泞的地面让我每一步都深陷其中,
步履维艰。子弹带着尖锐的破空声,不断在我身边和前方的泥地里炸开!
每一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突然,“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身后传来!
我下意识回头,只见地窖方向腾起一团巨大的、橘红色的火球,瞬间撕裂了沉沉的夜幕!
灼热的气浪夹杂着泥土碎石扑面而来!巨大的冲击波将我狠狠掀飞出去,重重摔在泥水里!
是爆炸!那个杀手竟然引爆了地窖?!刺耳的警笛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飘渺的幻觉。
我趴在冰冷的泥泞里,浑身剧痛,耳朵嗡嗡作响,眼前金星乱冒。不知道是警方的突袭,
还是杀手自己的灭迹行为。冰冷的雨水冲刷着我的脸,意识在剧痛和寒冷中迅速模糊。
在彻底陷入黑暗之前,我只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从雨幕中向**近,是敌是友?未知的深渊,
似乎比这地窖更加黑暗。3三年后的初秋,海城的空气里带着一丝清爽的凉意,
却吹不散心头的阴霾。我站在一栋被精心打理的花园环绕的别墅外。
曾经熟悉的白色栅栏被换成了冰冷的黑色铁艺,簇新的门牌上,
两个烫金的字在夕阳下刺眼——顾宅。隔着宽阔的庭院和巨大的落地玻璃窗,
客厅里灯火通明,一派温馨景象。
一个抽高了不少、穿着名牌运动服的少年身影正兴奋地蹦跳着,挥舞着手臂。是晓涛。三年,
足以让一个怯懦的男孩长成眉宇间带着几分张扬的少年,只是那轮廓里,
再也找不到一丝属于我的怯懦和依恋。“顾叔叔!快许愿!吹蜡烛!
”晓涛清亮快活的声音穿透厚厚的玻璃,清晰地传出来。巨大的生日蛋糕上插满蜡烛,
暖黄的光映照着围在蛋糕旁的人。被几个半大孩子簇拥在中间的顾言之,
脸上挂着温和宠溺的笑容,深吸一口气,吹灭了所有蜡烛。掌声和欢呼声响起。
站在他身边的楚欣妍,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米色羊绒长裙,脸上是恬淡满足的微笑,
递上一个包装精美的天鹅绒礼盒。顾言之含笑打开,
铂金袖扣在灯光下折射出冰冷而熟悉的光芒——那是我父亲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他一直叮嘱我要传给晓涛!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无法呼吸。就在这时,
晓涛突然像只活泼的猴子,猛地跳起来,双手搂住顾言之的脖子,整个人亲昵地挂在他身上,
声音清脆响亮,带着毫无保留的亲昵:“顾叔叔!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你能当我的爸爸!
”客厅里瞬间爆发出更大的哄笑声和掌声。一片热闹的祝福声中,
楚欣妍含笑的目光不经意地转向落地窗外。当她的视线撞上我站在阴影里的身影,
撞上我脸上那道从眉骨斜划至下颌、在暮色中更显狰狞的蜿蜒疤痕时——“啪嚓!
”她手中那只盛着殷红酒液的高脚杯,从指间滑落,在她脚边摔得粉碎!
鲜红的酒液如同粘稠的血液,在她光洁的白色大理石地面上,
溅开一朵巨大而刺目的血色烟花。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
客厅里的欢声笑语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张…张程?!”楚欣妍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
她踉跄着冲过来,猛地拉开了沉重的别墅大门。
温暖带着食物香气的空气和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甜香扑面而来,却让我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恶心。
她的手僵硬地悬在半空,指尖微微颤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的伤疤,
仿佛那是什么极其恐怖的怪物,迟迟不敢触碰。
场找到了…有疑似你DNA的…人体残骸…他们说你…你早就……”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恐。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灯光下,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顾言之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被一种极度的震惊和阴鸷取代。而晓涛,几乎是条件反射般,
猛地从顾言之身上跳下来,像受惊的小鹿,迅速躲到了顾言之宽阔的身后,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眼神里充满了惊惧、陌生,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
和三年前在教堂角落里躲避我的眼神,何其相似!“张程?真的是你?
”顾言之最先反应过来,他迅速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将楚欣妍挡在身后,
脸上挤出一个极其勉强的、带着巨大震惊和警惕的笑容。他抬起手,
似乎想拍拍我的肩膀以示“欢迎”,手腕上那枚百达翡丽在客厅璀璨的水晶灯下,
反射出冰冷刺目的光芒。“这…这真是天大的惊喜!欣妍和晓涛…我们都以为…唉,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语速很快,带着一种刻意的热情和不容置疑的掌控感,
“公司那边你放心,这三年一直是欣妍在辛苦代管,虽然有些艰难,但总算撑过来了。
有些…有些必要的法律文件,还需要你补签一下字,股份变更什么的,
都是流程……”他的话语像苍蝇的嗡嗡声,令人烦躁。我没有看他,
也没有看脸色惨白、摇摇欲坠的楚欣妍,
更没有看躲在顾言之身后、用陌生眼神打量我的儿子。
我的目光扫过这间装修风格已经完全陌生的客厅,然后径直走向通往二楼的旋转楼梯。
主卧的门虚掩着。我推开。曾经属于我和楚欣妍的巨大衣帽间里,
挂满了当季最新款的男士服装。我打开衣柜,所有衬衫、西裤的尺寸,
都明显比我的身材大了一号。曾经摆放着我们结婚相册、记录着二十年点点滴滴的那个位置,
如今放着一个精致的银质相框。照片里,
楚欣妍、顾言之、张晓涛三个人站在一片紫色的薰衣草花田中,笑容灿烂。
晓涛怀里抱着一大束薰衣草,对着镜头笑得没心没肺,仿佛那场绑架和失去父亲的痛苦,
从未在他生命中出现过。普罗旺斯。楚欣妍曾说过,那是她和顾言之年轻时最向往的地方。
“张程……”楚欣妍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疲惫。
她不知何时跟了上来,手里拿着一套崭新的男士真丝睡衣。“你…你的房间,在二楼的客房。
已经收拾好了。”她将睡衣递过来,手指白皙光洁,保养得宜,指甲上涂着柔和的蔻丹,
仿佛从未在教堂冰冷泥泞的地面上,为了另一个男人抓挠出血痕。“晓涛他…”她顿了顿,
避开我的目光,声音低了下去,“他好不容易才从当年的阴影里走出来,
心理医生说需要稳定的环境…你…你暂时先别**他,好吗?让他慢慢适应。
”她的语气带着一丝恳求,更多的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安排。我没有接那套睡衣。
目光越过她,投向窗外。楼下花园的阴影里,顾言之正背对着别墅,
拿着手机在低声快速地说着什么。清冷的月光照亮了他半边侧脸,
那不再是客厅里温和的模样,嘴角紧绷,眼神阴鸷,充满了算计和狠厉。
尽管隔着距离听不清,但那口型,我曾在无数个商战对手脸上见过,
此刻看得分明:“再安排一次意外。这次,必须彻底干净。
”4晓涛的厌学情绪爆发得毫无征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我不去!
我就是不去学校!”他将那个价格不菲的名牌书包狠狠砸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上,
震得碗碟叮当作响。一碗刚盛好的奶油蘑菇汤被打翻,滚烫粘稠的汤汁溅了我一身,
昂贵的衬衫前襟瞬间染上大块污渍。“新转来的那几个**!他们…他们天天嘲笑我!
说我是绑匪的儿子!说我爸是策划绑架的同伙!活该被炸得尸骨无存!
”晓涛的脸因为愤怒和屈辱涨得通红,胸膛剧烈起伏。楚欣妍慌忙站起来,
抽出纸巾想要擦拭我身上的污渍,声音带着惯有的安抚:“涛涛别这样!
妈妈明天就去学校找校长谈谈……”“找校长有什么用!”晓涛猛地打断她,
情绪更加激动,他伸出手指,直直地指向我的鼻子,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和迁怒,“除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