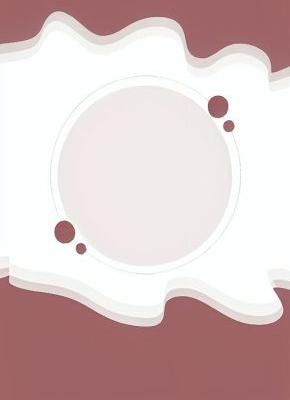我曾以为他是世上最完美的未婚夫。直到我在他书房暗格里,
发现一枚带血的猫铃铛——那是我“意外死亡”的猫去年戴的项圈。当晚,
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轻笑:“解决了,她父母的车祸赔偿金下周到位。
”我摸着抽屉里的妊娠报告,悄悄把他的胰岛素换成了生理盐水。客厅里,
那盏他特意为我挑的、据说是某位北欧设计师**款的水晶吊灯,
洒下过分明亮却毫无温度的光。光晕落在光可鉴人的黑胡桃木地板上,冰冷地反射着,
衬得偌大的空间有种样板间似的精致与空旷。
空气里弥漫着他惯用的那款雪松尾调的须后水气味,一丝不苟,和他的人一样。
墙上的挂钟指针,不紧不慢地走向晚上九点。沈牧通常在这个时间结束健身房的活动回家。
还有半小时。我蜷在宽大得过分的真皮沙发一角,身上裹着条米白色的羊绒薄毯,
指尖无意识地捻着柔软的毯边。电视机屏幕无声地闪烁着,光影在我脸上明明灭灭。
演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这屋子太静了,静得能听到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
还有胃里那一点点尚未被消化殆尽的、他晚餐时夹给我的清蒸鲈鱼的味道——他说对孕妇好,
蛋白质丰富,脂肪又低。孕妇。这个词像一根细小的冰针,猝不及防地刺了我一下。
我搁在毯子下的另一只手,轻轻覆上小腹。那里依旧平坦,什么也感觉不到,
除了因为晚餐吃得略多而微微的饱胀。可里面确实有了一个东西,
一个被那薄薄一张纸、几个冷冰冰的激素数值所确认的,正在悄然生长的生命。我和沈牧的。
我曾以为这是上帝,或者说,是命运对我前二十几年所有平淡乃至有些灰暗人生的盛大补偿。
赐予我沈牧,一个英俊、多金、温柔、自律,几乎挑不出错处的男人,
一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然后,再慷慨地附赠一个爱情的结晶,在我们婚礼前夕。
完美得像一则俗套却令人心安的都市童话。现在,童话书的封皮还在,烫金的标题依旧闪耀,
可我指尖触摸到的内页,却开始渗出粘腻的、铁锈般的寒意。
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客厅另一侧,那扇紧闭的橡木门。那是他的书房。家里的“禁区”,
倒不是他明令禁止,而是他总笑着说里面乱,都是他工作相关的文件和私人收藏,
怕我看了无聊,也怕我弄乱。他需要绝对的安静和秩序来思考。我向来尊重,
甚至欣赏他这份专业和专注。直到今天下午。他去了公司处理一个“紧急事务”,
出门前照例吻了我的额头,叮嘱我好好休息,眼神温柔得能溺死人。保姆张姐请了假回老家。
偌大的房子只剩下我。一种奇异的冲动,混合着孕期也许特有的某种无聊与探寻欲,
驱使我推开了那扇从未主动进入的门。书房很大,延续了客厅的性冷淡风格,
一整面墙的书柜,塞满了精装的大部头,分门别类,一丝不苟。巨大的实木书桌纤尘不染,
除了电脑、笔筒和一个造型简洁的金属相框——里面是我们上个月在北海道滑雪时的合影,
我笑得见牙不见眼,他搂着我,下巴搁在我头顶,同样笑意满满。一切都很“沈牧”。
我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书柜,扫过桌上整齐的文件,扫过角落那盆据说能防辐射的仙人掌。
最后,落在书桌侧面,一个与墙体同色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凹陷上。
那是一个隐藏式抽屉的拉手,设计得极为巧妙,
若不是午后阳光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斜射过来,在上面投下一道浅浅的阴影,
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心跳漏了一拍。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指,抵住那个凹陷,轻轻一拉。
抽屉无声地滑出。不大,里面东西不多。几本看上去有些年头的护照,
一叠用橡皮筋捆好的外币,还有几个丝绒盒子,大概是些不常戴的腕表或饰品。
我的目光掠过这些,定格在最里面,一个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标识的深蓝色天鹅绒小袋子上。
手指有些发僵。我捏住袋子,入手很轻。拉开抽绳,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叮铃。
一声极其轻微、几乎不可闻的脆响。在过分安静的书房里,却像一声惊雷,炸在我耳膜上。
一枚小小的、黄铜制成的猫铃铛。上面沾染着几处深褐色的、早已干涸的污渍。
铃铛连接着一截断裂的、边缘有些磨损的红色尼龙绳。我的呼吸骤然停止。
血液似乎在这一瞬间冻住了,然后疯狂地倒流,冲撞着太阳穴,突突地跳。四肢冰冷,
指尖却像被那黄铜烫到一样,猛地一颤。不可能认错。这是我给绵绵买的项圈上的铃铛。
绵绵,我养了七年,从大学宿舍偷偷抱回来的小橘猫。去年春天,一个同样阳光很好的下午,
它从这栋高层公寓未完全关闭的阳台窗户“失足”掉了下去。十七楼。我找到它时,
它小小的身体蜷在绿化带的灌木丛里,身下是一滩已经发黑的血迹,项圈断开,
铃铛不知所踪。沈牧陪着我,一遍遍安慰哭到几乎休克的我说,是意外,绵绵太调皮了,
也许是想抓窗外的蝴蝶。他温柔地处理了后续,亲手埋了绵绵,在那之后的一个月,
对我呵护备至,绝口不提再养宠物的事,说怕我触景生情。我以为那铃铛早就和绵绵一起,
永远留在了那个悲伤的春天。可现在,它在这里。在他书房的暗格里。
带着可疑的、铁锈色的污渍。那些污渍……是血吗?绵绵的血?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拿走这个?一个意外死亡的宠物项圈上的铃铛,有什么珍藏的必要?
除非……那不是意外。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我意识的最深处,幽幽地浮上来。胃里一阵翻滚。
晚上吃下去的鲈鱼,混合着沈牧温柔的劝食声,变成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油腻感,堵在喉咙口。
我猛地捂住嘴,强压下那阵剧烈的恶心。手指收紧,铃铛坚硬的边缘硌着掌心,生疼。
我把铃铛塞回袋子,原样放好,推回抽屉。动作僵硬,但奇迹般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做完这一切,我退出了书房,轻轻带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
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细微地颤抖,冷汗浸湿了贴身的真丝衬衫。回到客厅,
我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坐到夜幕降临,坐到华灯初上,坐到时针指向九点。毯子下的身体,
一阵冷,一阵热。脑子里是乱的,
的满足模样;它摔下去后血肉模糊的小身体;沈牧沉静地擦拭我眼泪的手指;他向我求婚时,
在铺满玫瑰花瓣的餐厅里,那双盛满星光的眼睛;还有下午,
暗格里那枚沉默的、带着陈年血渍的铃铛。哪一个才是真的?
玄关处传来电子锁开启的、清脆的“嘀”声。然后是熟悉的脚步声,沉稳,规律,由远及近。
我猛地闭了一下眼,再睁开时,迅速垂下眼睫,调整了一下呼吸,
手指在毯子下紧紧攥住那张对折起来的、藏在睡衣口袋里的妊娠报告单,
冰凉的纸张边缘刺着皮肤。沈牧走了进来。他刚刚洗过澡,发梢还带着湿气,
换上了一套深灰色的家居服,衬得他肩宽腿长。看到我,
他脸上立刻漾开那种我熟悉至极的、令人安心的笑容,走过来,很自然地俯身,
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带着清爽的沐浴露和须后水的味道。“怎么不开电视声音?
一个人发呆?”他的声音低沉悦耳,手指拂开我颊边一缕不听话的头发,动作轻柔。
“有点累,懒得看。”我抬起头,努力扯出一个笑容,希望看起来只是孕期常见的倦怠,
“今天公司的事处理好了?”“嗯,一点小麻烦,解决了。”他轻描淡写,在我身边坐下,
手臂环过我的肩膀,将我往怀里带了带。他的体温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过来,
曾经让我觉得无比温暖和安全,此刻却像一种无形的桎梏。“宝宝今天乖不乖?有没有闹你?
”他的手很自然地覆上我的小腹,掌心温热。我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瞬,随即放松下来,
靠在他怀里。“还好,就是有点没精神。”“怀孕辛苦,我的暖暖受累了。”他叹息般说着,
下巴蹭了蹭我的发顶,“等婚礼结束,我们去你一直想去的那个海岛度假,好好放松一下。
”暖暖。他给我起的小名。他说我像个小太阳,能融化他所有冰封的情绪。多讽刺。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只是静静靠着他,听着他平稳有力的心跳。一下,
又一下,规律得像精密的仪器。这个男人,这个我打算托付一生、共同孕育生命的男人,
他的胸腔里,跳动的究竟是一颗怎样的心?接下来的时间,像被拉长又压缩的胶片。
我们像往常一样,闲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他督促我喝了半杯温牛奶,
然后起身说要去书房处理一点收尾的工作。“别太晚。”我轻声说,
目光追随着他走向书房的背影。“很快,你先睡,不用等我。”他回头,
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笑,然后关上了书房的门。那扇橡木门,再次将我们隔开。门内,
是带着绵绵血迹铃铛的暗格,是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门外,是我,
和一个刚刚确认存在、却已蒙上浓重阴影的小生命。我没有听话地去卧室。我躺在沙发上,
毯子拉过头顶,在绝对的黑暗和寂静里,睁大眼睛。感官被无限放大。
我听见远处街道隐约传来的车流声,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潺潺的微响,
听见自己压抑的、有些过快的心跳。然后,我听见了。隔着门板,模糊,但足够清晰。
是沈牧的声音。他在打电话。语气不再是平日对着我时的温柔耐心,
而是带着一种……松弛的,甚至有点轻佻的凉意。“……嗯,放心,
都打点好了……比预想的顺利。”短暂的停顿,对方似乎在说什么。他低低地笑了一声。
那笑声,像毒蛇滑过冰面,钻进我的耳朵,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解决了,
她父母的车祸赔偿金,下周就能到位。”时间,空间,一切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碎裂。
我父母的……车祸赔偿金?一周前,我远在老家的父母,在一次夜间自驾途中,
因为“刹车突然失灵”,冲下了山路护栏。妈妈当场身亡,爸爸重伤昏迷,至今未醒。
警方初步调查说是车辆老旧,意外事故。沈牧当时立刻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陪我赶回去,
处理一切,联系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安抚几近崩溃的我,他的悲痛和担当看起来那么真实。
他甚至红着眼睛对我说:“暖暖,以后我就是你的依靠,爸妈不在了,我还在。”可现在,
他在电话那头,用谈论天气般的口吻,说“解决了”,说“赔偿金下周到位”。解决了什么?
怎么解决的?刹车失灵……是“解决”的一部分吗?胃里翻江倒海,
那股恶心感再也压制不住。我死死咬住毯子的一角,将干呕的声音闷在喉咙里,
浑身抖得像个筛子。冰冷的泪毫无征兆地涌出,瞬间爬了满脸,流进耳朵,流进嘴角,
咸涩冰冷。绵绵的死,不是意外。我父母的车祸,也不是意外。那是什么?是为了什么?钱?
我父母只是普通的中学教师,能有什么钱?赔偿金?那笔钱,会是给我的吗?然后呢?
沈牧是我唯一合法的丈夫,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如果我也不在了呢?
一个清晰的、完整的链条,带着地狱般的寒意,在我脑中轰然成型。从绵绵开始,或许更早?
到我父母,然后……到我。扫清一切障碍,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手一切。我家的老房子,
可能有的微薄存款,还有……保险?我父母有保险吗?我有吗?沈牧似乎提过,
要给我买一份高额的健康保险,说是“保障”……恐惧,灭顶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
但比恐惧更先冲上顶梁的,是冰锥般尖锐、淬毒的恨意。那恨意如此汹涌,
几乎要冲破我的天灵盖。我死死瞪着书房门的方向,眼睛酸涩胀痛,却没有再流一滴泪。
哭没有用。悲伤没有用。我要活着。我必须活着。为了我惨死的绵绵,
为了我生死未卜的父母,也为了我肚子里这个尚未成型、却已被他父亲列为清除目标的孩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书房门开了。沈牧走出来,看到沙发上的我,有些意外:“怎么还没睡?
”我从毯子里探出头,头发凌乱,眼睛可能有点红。我哑着嗓子,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只是困倦和低落:“睡不着,想爸爸妈妈了……”他走过来,坐在沙发边,
摸了摸我的脸,指尖温暖。“别想了,暖暖,还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
”他的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无比真诚,充满怜惜,“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为了宝宝,
也为了我,嗯?”我看着他,看着这张曾让我觉得是全世界最英俊、最值得信赖的脸。现在,
每一处线条,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让我感到一种毛骨悚然的虚假。“嗯。”我低下头,
躲开他的触碰,将脸埋进毯子,“我这就去睡。”“我抱你。”他不由分说,
将我连人带毯子打横抱起来,走向卧室。他的手臂有力,怀抱温暖,
曾经让我觉得是天底下最安稳的所在。此刻,我只觉得每一寸与他接触的皮肤,
都像被毒蛇的鳞片刮过。他将我放在柔软的大床上,细心盖好被子,又俯身吻了吻我的额头。
“晚安,我的暖暖。”“晚安。”我闭上眼睛。他关了灯,带上门出去。黑暗中,我睁着眼,
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去了客卧——自从我查出怀孕,他说怕自己睡相不好碰到我,
主动搬去了客卧。很好。我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大约半小时后,
整个屋子彻底陷入了沉睡般的寂静。我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
悄无声息地溜出卧室,像个幽灵。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城市永不彻底熄灭的黯淡天光,
摸向厨房旁边的储物间。沈牧有轻微的胰岛素依赖症,
据说是早年工作过于拼命、饮食不规律落下的毛病,并不严重,
但需要每天睡前注射一次短效胰岛素。他的药,还有专用的注射笔、针头、消毒棉片,
都放在储物间一个带锁的小医药冷藏箱里。钥匙,他有一把,我也有一把——是他主动给的,
说“家里一切对你没有秘密”,为了方便我“照顾他”。我拿出我的那把钥匙,
手指稳得可怕,没有一丝颤抖。打开冷藏箱,冷气扑面。里面整齐码放着几支胰岛素笔芯,
还有几小瓶未拆封的备用胰岛素。我取出一支他今晚用过的同型号笔芯,
又取出一支未拆封的。然后,我从旁边的家庭常备药箱里,
找到了一小瓶未开封的、医院常用的那种0.9%氯化钠注射液,也就是生理盐水。
我的动作很慢,很轻,但异常稳定。我用消毒棉片处理好生理盐水瓶的橡胶塞,
用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抽吸了足量的盐水。然后,
我找到胰岛素笔芯尾部那个不起眼的、用来补充药液的橡胶塞,将针头小心地刺入。
我没有抽出里面的胰岛素——那会有气泡,容易被他察觉。我只是将注射器里的生理盐水,
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推了进去。直到笔芯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只是稍微沉重了一点点,饱满了一点点。做完这一切,我将这支被动过手脚的笔芯,
放回他今晚本该使用的那支原来的位置。而原来那支,被我藏在了储物架最深处,
一堆过期杂物的后面。关上冷藏箱,锁好。我把用过的注射器、针头、棉片,仔细地包好,
塞进明天一早要扔的垃圾袋最底层。回到床上,我重新躺下。
身体因为紧张和冰冷的寒意而微微发抖,但心脏却像被扔进了绝对零度的冰窖,
一片死寂的冷硬。我知道胰岛素的作用。它是降低血糖的。一个依赖胰岛素的人,
注射了生理盐水,意味着他的血糖将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持续升高。短期,
也许只是口渴、多尿、乏力。但时间稍长,高血糖会引发酮症酸中毒。嗜睡,意识模糊,
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昏迷,甚至死亡。沈牧很在意自己的身体,
他每天都会用血糖仪检测。但血糖的升高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是在我每天精心准备的、看似营养均衡的饮食掩护下——我可以悄悄在菜肴里多加一点糖,
或者淀粉。他会察觉不适,但可能首先会归咎于工作压力,
或者我这段时间情绪低落影响了他。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可能已经晚了。这需要时间,
也需要运气。我不能让他立刻倒下,那太明显了。我要的,
是一个缓慢的、看起来“自然”的恶化过程。在他“生病”期间,我需要做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