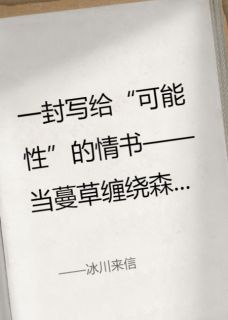雨水,是江蔓来到这座北方城市后,天空给予她最频繁的问候。不同于江南细雨的缠绵悱恻,这里的雨,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砸在水泥地上,溅起浑浊的水花,空气里弥漫着尘土被打湿后特有的、略带腥气的凉意。就像她此刻的心情——一种被连根拔起、强行移植后的无措与微凉。
她叫江蔓。
“江”,是故乡蜿蜒清澈的河流,是流动的,也是滋养的根脉;而“蔓”,是藤蔓,是野草,是看似柔弱却能在石缝砖隙里顽强攀爬、缠绕生长的生命。父亲说,希望她像江边的蔓草,无论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都能找到扎根的力量,坚韧地活着。可此刻,抱着几乎要遮挡全部视线、摇摇欲坠的新课本,走在陌生而喧闹的走廊里,江蔓只觉得自己像一株被暴雨打折了茎叶的野草,狼狈地匍匐在湿滑的地面上,连“活着”都显得笨拙而吃力。那些厚重的书本,是新的知识,也是新的枷锁,压得她喘不过气,视线艰难地越过书堆顶端,也只能看到前方同学模糊晃动的背影和湿漉漉、泛着惨白灯光的地砖。
讨厌这种失控感,就像讨厌这场突如其来的转学——从温润的江南水乡小城,一头扎进这座以升学率闻名的北方重点高中的冰冷喧嚣里。雨水顺着她微湿的刘海滑落,滴在睫毛上,痒痒的,带着北方的生硬。
他叫林渡。
“林”,是葱郁的森林,是沉稳的绿意,是包容也是遮蔽;而“渡”,是渡口,是摆渡,是经过,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短暂停留。这个名字仿佛预示着他生命的轨迹——像一棵树,根植于某处,枝叶却向往着更广阔的天空,又像一艘船,注定要在不同的渡口停泊,载人一程,然后驶向未知的远方。沉静温和是他的表象,那深藏眼底的、对远方的渴求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游离感,才是他名字里“渡”字的真正注脚。他或许能成为他人生命里温暖的驿站,却很难成为谁永恒的港湾。
就在江蔓小心翼翼地侧身,试图避让一个抱着篮球风风火火跑过的男生时,脚下沾了雨水的帆布鞋猛地一滑!
“啊——”
惊呼声卡在喉咙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怀里的课本像是突然获得了生命,挣脱了她的束缚,哗啦啦——如同受惊的白鸽群,争先恐后地散落一地。崭新的书页狼狈地拍打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瞬间被脏污的水渍晕染开深色的痕迹。更糟的是,几本最厚重的习题集借着惯性滑出去老远。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周遭嘈杂的人声似乎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书本坠落和拍打水面的刺耳声响。巨大的狼狈和窘迫感如同滚烫的岩浆,瞬间从脚底直冲头顶,烧得她耳根通红,脸颊发烫,恨不得立刻原地消失。
预想中冰冷的撞击和彻底的狼狈并没有到来。
一只骨节分明、肤色偏白的手,比她更快地出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稳稳地按住了即将滑入人群脚下的一本厚厚数学竞赛书。那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
江蔓惊魂未定地抬起头,视线顺着那只救急的手向上移,猝不及防地撞进一双眼睛里。
是林渡。
他就半蹲在她面前不远的地方。洗得有些发白的蓝白校服衬衫,袖子被他随意地挽到了手肘,露出的手腕线条清晰,看着有些瘦削,却意外地蕴藏着刚才那一下展现出的力量感。他正利落地帮她捡拾散落在周围的课本,动作安静而迅捷,没有多余的言语,也没有刻意的关切表情。走廊顶灯的光线有些昏暗,混杂着窗外阴雨天灰蒙蒙的光,斜斜地打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清晰利落的下颌线,和微微抿着的、显得有些专注的薄唇。
他的神情并非拒人千里的冰冷疏离,反而带着一种在高中生里少见的沉静温和。像初春午后晒暖的湖水,平静无波,让人下意识地想要靠近汲取一丝暖意。然而,当江蔓的视线与他低垂的眼睫下抬起的目光短暂相接时,她心头莫名地微微一悸。那湖水的深处,似乎漾着一种难以触及的遥远。那并非针对她的冷漠,更像是一种……心在别处的游离感。
“谢…谢谢你…”江蔓的声音细若蚊呐,带着显而易见的慌乱和尚未平息的窘迫。她手忙脚乱地想伸手去接他刚刚整理好、叠放在最上面的几本书。
“拿稳。”他的声音不高,质地清冽,带着北方口音特有的爽利感。但这清冽之中,似乎又奇异地揉进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像山间溪水流过被阳光晒得微暖的鹅卵石,短暂地驱散了一点她心头的冰凉。他把那摞书稳稳地递还到她手中,目光似乎不经意地在她沾满了泥点和水渍的白色帆布鞋上停留了极其短暂的一瞬——那目光里没有嘲笑,更像是一种快速的、近乎本能的观察。随即,那目光便极快地移开了,没有任何评价,也没有任何停留的意思。
他甚至没有再看她一眼,也没有等她再说些什么,便直起身,像完成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转身,步履从容地汇入了下课铃响后汹涌喧闹的人流。那抹蓝白的背影,在攒动的人头中很快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消失不见,仿佛一滴水融入了奔腾的河流。
江蔓抱着重新摞好、却已不复崭新的课本,站在原地,像一座突然被遗落在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的孤岛。走廊里重新灌满了学生们的笑闹声、脚步声、议论声,这些喧嚣却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隔膜挡在了外面,变得遥远而模糊。
鼻尖,似乎还固执地残留着他刚才靠近时,带起的那股独特气息——干净的消毒皂的清冽味道,混合着一种旧纸张特有的、带着点微尘和时光沉淀感的淡淡墨香。这气息很淡,却异常清晰地烙印在她的感官里。
她下意识地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泥泞、狼狈不堪的帆布鞋。刚才那巨大的窘迫感正缓缓褪去,像潮水退下沙滩,留下一种空落落的、却又被另一种陌生情绪悄然填满的感觉。是尴尬褪去后的余悸?是绝处逢生般的感激?还是……对那双温和沉静、眼底却仿佛藏着遥远星辰大海的眼睛,所产生的、无法抑制的、如同蔓草悄然攀附般的好奇?
她忍不住又抬眼,望向林渡消失的方向。那个蓝白的背影早已不见,但刚才那一幕却在脑海里反复回放:他半蹲着帮她捡书时,微垂的眼睫下专注的侧脸;他递过书本时,骨节分明的手指与自己慌乱指尖那极其短暂的、微凉的触碰;还有那句清冽中带着一丝奇异暖意的“拿稳”。周围的男生还在嬉笑打闹,撞掉了别人的东西也只会哄笑着跑开。
可林渡……他那么安静,动作那么利落,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窘迫的样子。这种带着距离感的、不掺杂任何戏谑或怜悯的善意,让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律地跳动着,一种莫名的、带着细微电流感的情绪,正顺着被雨水打湿的发梢,沿着被书本勒红的手指,悄悄地、无声地蔓延开,缠绕住她初来乍到、尚且惶惑不安的心。
这北方城市冰冷湿漉的走廊里,一个叫江蔓的女孩,第一次遇见了一个叫林渡的男孩。像一株渴望扎根的蔓草,遇见了一缕注定要穿林而过的风。温暖短暂停留,留下的是被拂动的痕迹,和风过之后,更深沉的寂静,以及对那不可知远方的、懵懂而悸动的凝望。
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伴随着散落的书本、滑倒的狼狈、一只伸出的手、一个短暂交汇的眼神、一句清冽的“拿稳”,以及那迅速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缓缓地、带着宿命的回响,开始了转动。蔓草与渡者的故事,在初秋的这场冷雨中,悄然埋下了它充满希望与怅惘的第一笔。而那本沾了水渍的数学竞赛书封底,一个用铅笔写下的、力透纸背的名字——“林渡”,正静静地躺在江蔓怀抱的书堆里,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漾开的涟漪,无声地扩散向未来。